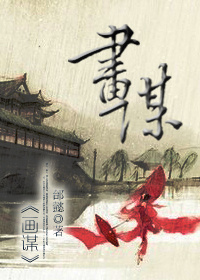丞相谋-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嗯,三年前的约定还做不做数。”
对酒而歌,不醉不归。
我点头:“作数,待会我就去告诉九皇兄。”
他笑笑,转身要进殿,却被我拦住:“你二弟……是不是叫杜璟?”
他点头,复又奇怪看我一眼,“你见过?”
我咳了声,道:“见过的,可有婚配?”
他一个踉跄,险些跌下台阶:“他年前便成亲了,十三你该不会……看上他了?”复又摸摸下巴,忽而笑道:“十三,以你的资质,做个且还是过得去的。”
我瞪他一眼,却见一人从殿内出来,青衫墨发,却是白棠。
白棠在我二人身前停住,对杜白笉笑道:“三月未见,不想再见竟是在此见得杜兄。”
我惊异道:“你们认识?”
杜白笉拿食指拂了拂剑鞘,点头道:“前些日子凉州水患,我与白相见过一面。”
是了,凉州与壁连关虽不为同境,真真说上也只隔了几个小镇,二人见过,不足为奇,我点头,却见杜白笉蓦地沉了声:“现下冬日刚过,雪水刚化,周边小镇却依旧无人管辖,水荒刚过,却是民不聊生。”
白棠拿扇敲敲手心,半眯着桃花眼说了句:“无妨。”复又转头对杜白笉道:“皇上正问起杜将军。”引得他风风火火的进了殿,这才悠哉悠哉与我道:“公主好兴致,彻夜未归,竟与杜府大公子在一路。”
昨夜酒力还未退,又被他这笑狠狠的晕了一番,又想今晚与杜白笉约着的不醉不归,又是一晕,龇牙咧嘴。
白棠挑眉笑道:“喝酒了。”
我摆摆手,说了声:“小意思。”便鬼迷心窍的邀他去御花园挖那埋了三载的酒。
酒是在杜白笉去壁连关的第二天我与九皇兄一起埋的,我深怕倒时找不到,便拿了根红绸子在隐蔽的树根下系了个结,我白棠将酒放在亭里坐下,默了默,撩起绣摆靠在云柱边坐下,白棠挑了挑眉坐在我身边,我转头道:“你不是故意杜白笉进殿么,怎么现下又不说话?”
他笑笑,眸若深潭,声音清润沉静:“你莫不是害怕与我独处?”
我的老脸很没骨气的红了一红,复又想到他用这桃花样儿不知够了多少千金少女的心,我这反应也忒没骨气了点,只得咬牙看他,水火不容的样子。
白棠摇了摇头,甚有无奈:“你不必如此,我支走他,却是为他好。”见我依旧嘶哑咧嘴,只与我道了半盏茶的工夫,却让才将昨日卫和那没头脑的说辞想了个通透。(文-人-书-屋-W-R-S-H-U)
原来这凉州与壁连关间一小镇,名为余。
余镇虽不算富裕,却也能自给自足,哪料一个水患却是坏了庄稼良田,以至有些人将主意打到了军粮上面。
锦镇南为斐国,北邻曰国,却不属两地,无人管辖,加上军粮一事,杜老将军借着这个机会上了道奏折,请吾皇将杜白笉给招回来,杜白笉虽封号少将军,入关三载,确实未回金陵,此番请求,自不为过,便将他给找了回来,平定了将军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却又因水患未解头疼不已,遂让安卿帝一起琢磨个法子。
安卿帝一来,白棠这丞相势必凑个热闹,本来安卿帝字里行间说道丞相忧国忧民,此次水患,必会相助云云,后我想了想,却是团子想要支走白棠,为自己所剩不多的自由谋些福利,却被一人打断了这黄粱美梦,深觉郁闷,此番正在行宫里面壁思过。
我被勾起了好奇,忙凑上前,望着他道:“当今竟有如此爱国良臣,若有良机,我一定要去看看,哈哈。”
不料白棠顿住了话头,默着看亭下水面不语,直到我心肝被折磨得几欲垂死,才听他低笑一声,道:“那人你认得的,户部侍郎,卫和。”
卫和果真是去殉国的。
余镇接连壁连关,小战不断,却也深受其害,此番他一个文臣请缨去治水患,却和那送半条命进去差不了多远。
退一步说,若是他未能治好水患,回了金陵,罪论欺君,更是连剩下的半条命也没了,也不知这卫和放着好好的侍郎不做折腾个什么劲,临走还把这卫淮给我折腾,卫和,你这事做什么孽哟,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我……
我点头,从他手里抽过扇子,扇面冰凉如水,玉色如月,点了点他的肩,他看我动作,却是不语,我笑道:“要是此番杜白笉要知道他是再出不了金陵,指不定要恼得什么样子,此番……嗯,谢谢。”
他愣了愣,转而笑了,复站起身子,颀长身影挡住了日头,袖边金线云纹却是落在我眼边,墨发几缕落在肩上,绝世之姿,遗世独立。
我盯着他看了大半光景,回过神来,却对上溢满笑意的眉眼,只觉脸上红了红,却望天叹道:“也不知你这忒桃花的样子,哪家姑娘会安心嫁与你。”
第十四章
天际青白,层云慰人。
白棠青衫而立,乌发如墨,一如遥花宴上隔花初见之时温雅清毓,片刻过后,却见那人望着我笑得英邪:“公主如此关心我的终身大事,倒让我受宠若惊。”
我白他一眼,只觉这声音听得经络俱灭脸上也似火烧了一样,只好讪笑两声,低头去看拿扇子。
扇身画了枝桃花,褐枝映水,花瓣如春,摇曳生风,煞是好看。
我清醒不少,站在白棠身侧,弯腰拾起一粒石子投入水中,将将冒出水面的锦鲤顿作鸟兽状散去,我望着光秃秃的湖面,忽而拿扇子碰了碰白棠的肩,待他微微侧脸看我,又嘿嘿笑道:“你与团……安卿帝此番来曰国为的是什么事,你与我说说。”
他随我样子也拿了粒石子在指尖,却迟迟未投:“你说的是私事还是公事?”
我愕然道,复又面露好奇,忙凑上身去:“都有都有。”
鼻尖传来一股淡淡的清毓的味道,白棠却未注意到我挨他极近,目光幽幽落在远方:“斐国曰国一向交好,却免不了疏漏纷繁之处,至于公事。”他顿顿,也不知何时拿过了折扇却以半开半合,挑眉笑道:“非皇亲国戚不说。”
我怒道:“我也是皇亲国戚!”话闭觉着此话颇有些强词夺理,便又默然。
他却笑得春风得意:“若你实在想知道,不如嫁……”
“白棠!”我气急吼了一声,却有些慌乱,心下觉着本是没什么的事情被我这么一叫就变成了有什么,真是拿起石头崴了自己的脚,只怔怔望着他发懵。
他盯了我半响,忽然轻叹一声:“真是个经不住逗弄的性子。”
我哼一声,随即别过眼去,心觉今日三番两次被他惹得七窍生烟委实不该,随定定神,目光又转向他:“私事呢?”
他望向我,有些发楞,遂跳了扇子道:“我来找媳妇儿。”
天际一层薄云浅金如锦,池边清风露水,天莹如玉。
身后枯枝垂露,我却想到,再过不久,待到春日,必会花团锦簇,草长莺飞,又是一番大好光景。
杜白笉果真被气得不行,此番月明星疏,树影摇曳,我与九皇兄早早坐在亭中,只看他一人脸色铁青,平素清俊的面容也有些煞人。
我看了半晌,终是忍不住道:“诶,你要是真觉着憋屈。”我吞吞口水,指了指放在桌上的长剑,道:“发泄发泄,也让我看看,你这些年倒有没有长进。”
九皇兄穿着一身紫衣锦袍,凤眸半眯却不知在想什么,直到杜白笉应了声好,作势要拿剑,他蓦地起身道了句:“得此良机,不如比试一番。”便兀自站在了亭外空地上,月光稀疏,投下忽明忽暗的身姿,竟是我从未见过的。
平素也就在街市里见过几次杂耍,倒也没见过真刀真枪,此番我却是赚了个眼福,双眼便直愣愣的盯着二人。
杜白笉身影挺拔,剑出鞘,寒光乍现,九皇兄身形一闪却抽出腰上软剑迎了上去,只觉眼前一黑一紫两道身影格外清肃,树影婆娑,清风摇曳,一个恍神,二人招过大半,却畅快淋漓,须臾,杜白笉退后一步,手中长剑却有些发颤,九皇兄一个闪身便回了桌前,兀自倒了杯酒饮了下去。
我与杜白笉对视一眼,他上前收了剑,目光却涣出神采,想必是比试一番的缘故,我不好打扰,便倒了杯酒递与他:“莫负美景,当酣饮畅怀。”
今夜星辰,莫负美景,当酣饮畅怀,不醉不归。
今日却也算圆满了一回,我望了望手中的酒,估摸着这一喝又要去掉半条命,遂顿了顿,杜白笉被九皇兄此番不顾形象的牛饮有些傻眼,扯了扯我的袖子,道:“你九哥受什么刺激了,太不正常。”
我心下叹叹,对着他做了个唇语,他愣了愣,再望向九皇兄却呆了呆,复又啧啧两声,感慨道:“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我点头,道:“女官这身份特别一些,九哥你再接再厉,再接再厉,嘿嘿。”
酒过三盏,杜白笉就有点坐不住,我用手戳了戳他的脸,心下觉着他果真还要去历练历练,怎的在军营里呆了几年,就这点酒量?
九皇兄情况比他好不了多少,凤目一片迷茫,唇色越发樱红,黑发缭乱搭在颈间,却让我想起白棠在雪地之中青衣缱绻,清毓温润的样子,叹道这人果真表里不一,将碗放下,招了小金子来送杜白笉出宫,自己却扶着九皇兄坐在云柱下。
我默了默,道:“九哥,你与那女官是不是出问题了?你与我说说,兴许我能想想法子。”
九皇兄抬手,却抚上我的发,轻轻摩挲,神色迷离,半响道:“果真到最后,还是你与我一起。”
我愕然道:“真出事儿了?”
九皇兄不语,却低了低声音,目光幽幽落向水面:“我第一次在护国寺见到她的时候,也是这般光景,那时她也是这般坐在亭里,却是在看书。”
九皇兄笑出声,有些苦涩,手一扬,指向亭中一角,方才继续道:“我当时在想,护国寺怎么会有女子出现,还是个脑子里都是结果我走过去,她却像没看见我一样。”
说到这,他顿了顿,我撑着下巴看他:“然后,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办法将她作为女官进了朝,天天与她作对,成日找她麻烦,只盼能有一日她面上表情会生动些。
“有一日我将她府上的书房烧了,她气得眼睛都红了,却还是一声不吭,我当时在想,若是她有半分示弱,我便是将整个金陵都搬空,也要将那些书找回来。”
可是容挽至始至终也没有再说一句话,九皇兄在众位皇子里相貌最好,却是最恣意高傲的,却在一旁一声不响的呆了半日,彼时,月如玉,万树碧影亦酒醇,九皇兄与我娓娓讲了许多事,却始终不离一人,九皇兄此番覆水难收,我听后只觉时光荏苒,要趁着现下的光景,与身边之人踏遍锦绣山河,且吟且行,一同享遍喜乐,历尽劫数,方为圆满,
我吞了吞唾沫星子,踟蹰道:“九哥,你这是单相思……”望了望他渐渐发青的脸,又连忙改口道:“嗯,九哥,你不必担忧,你看,我这也不是对易昭单相思来着,易昭说他没有欢喜的人,那我还是有机会的,嗯,容挽现下也未有欢喜的人,九哥却是这些日子与她交往最深的人,想必……想必你还是有些机会的。”
“我觉着吧,就算她有了欢喜的人要嫁人了也没关系,大不了,大不了到时候我把她给你抢回来,你看成么?”
一番话下来,口舌干燥,又饮了大半碗酒,头疼愈深。
我觉着,我活了十八载,唯有今日一言是用尽了真心,也算掏心掏肺,却引来他一声轻笑:“嗯,十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