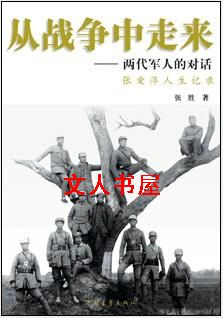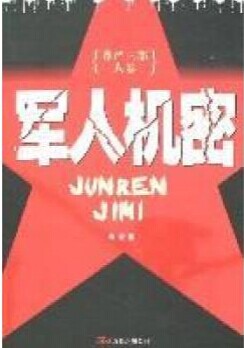军人机密-第7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石榴:“看看小碾子去。”
贺紫达赞同地点点头:“你带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叫小碾子别把他贺叔叔看得那么复杂。过两天,我也去看他。”
谢石榴边走边说:“前半句,不管带!”
招待所,小碾子将单人床板扣在地上,脸盆里装着揉好的泥。他坐在地上,专心致志地做沙盘。沙盘像模像样,基本完成。
门上的锁被拧了两下,闯入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和两个战士。
“查房,查……”妇女一怔,“你,你这是干什么?满屋子和泥玩!”
小碾子继续摆弄着:“走时,我会打扫干净的。”
“那也不成!”妇女极凶,“这是招待所,知道不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
妇女翻看手里的登记簿:“噢,还是个营长……”她一下注意到小碾子头上的绷带,也注意到小碾子正狠巴巴地把一团泥在手里倒来倒去。妇女飞快地软下来,“哦……你弄吧,弄吧。”
出了门,妇女拍抚着自己的胸口:“喔哟哟,战场上刚下来的,一个个都是眼珠子直直的,红红的……”
小碾子接着埋头他的沙盘。门又被敲了两下,又有人走进来。小碾子盯在沙盘处,吼道:“房里又没女人,干什么狗头狗脑的!”
有老人清嗓子的声音。小碾子抬头,马上爬起来:“老号长……我以为……天天半夜查房,比我在部队查岗查铺都勤。”
谢石榴:“招待所里捉奸,恐怕也算咱们这个军队的老传统了。”
小碾子笑。
谢石榴围着沙盘走了一圈,十分欣赏:“像模像样,很是地道。”
小碾子:“挖泥巴出身,弄这个,专业。”
“这就是一○九二?”
“嗯。”
谢石榴看看小碾子:“不服气?”
{}小碾子:“嗯。”
{。人。}谢石榴:“真的?”
{。书。}小碾子想想:“服。但,冤!”
{。屋。}谢石榴拧开军用水壶:“来,喝一口,把白天的补上。”谢把壶举到小碾子嘴边,小碾子揸着两手泥,“咕咚”,喝了一大口。
谢石榴搬张椅子坐在小碾子身边:“你干你的。”小碾子抓起一团泥,继续。
“三二年,在宁岗开辟根据地时,打过一个姓焦的老财的土围子。那时候打仗笨,就是光着膀子朝上冲,一排倒下了,二排上;二排倒下了,三排上。或者是三个排一窝蜂地一块儿上。那回,一连冲了两天一夜,越打不来,越急眼;越急眼,越不要命,围墙跟儿下的尸体都摞出了好大一个斜坡!”
谢石榴朝小碾子嘴里又灌了一口酒:“后来,还是刚参军的你老子想了个主意,他拉着贺伢子弄了一口棺材,把石匠开山用的土炸药装了个满满登登,然后放在一架板车上,再蒙上几床湿被子,趁天夜,悄悄推到墙围子底下……”
小碾子:“然后划着火柴,点燃捻子……”
谢石榴又朝小碾子嘴里灌一口:“哪有那么复杂,两个小兔崽子转身就跑回来,一颗手榴弹撇过去,‘轰’的一家伙,糯米汤和泥巴垒起来的墙,一下被炸开两丈多宽的口子,部队一声吼,就冲了进去。再看那两个小东西,人不但震得昏了过去,而且耳朵孔,鼻子眼儿,全是血,我以为他们死球了,抱着他们俩,哭得那个惨!哈哈哈……”
又灌一口。小碾子被呛得咳嗽:“就……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但是打完了仗,一问,崽子和伢子使炸药那会儿,墙头上也就剩下了七个又老又伤的家丁!要不然那口棺材怎么会那么轻巧地推过去呢。”
小碾子想想,产生共鸣:“……也就是说,用不着爸爸他们忙活,部队再冲一次,也就拿下来了!”
谢石榴用脚踢了踢沙盘:“贺伢子说,这个一○九二是叫你捏软了的柿子,后来让鹿儿捡了个便宜。”小碾子睁大眼睛:“他真的这么说的?”
“你贺叔叔说,过两天他来看你。”谢石榴边说,边察看小碾子的伤,“伤在脑门上,还是后脑勺上,没破相吧?”
小碾子笑答:“脑门上,但头发盖得住。”
谢石榴又灌过去一口:“我这个故事可不是给你提供吵架、骂娘的材料的。要知道,那七个家丁虽然经不住再一次冲锋,但凭借高墙,这最后一冲的路上,少说又要铺上十几条性命。你能说两个小毛孩子的功劳不大?这一仗,就叫崽子和伢子干上了排长,十三岁,当兵还不满五天哪!但没有一个人不服。当官的能打,会打,对于当兵的讲,就是积了大德!”
谢石榴又灌过去一口:“小碾子,自古以来,军功是最抢眼,又是最伤心的,一百个人冲锋,子弹没钻在你身上,是因为钻在别人身上了。军功章最后挂在你胸上,但那原本很可能是该挂在别的哪个人胸上的。当兵的,只要上过一回战场,即使活着下来,也算是死一回了。别人替你死了!你再活就该是替别人活!军功,不是秤称出来的!谁要是没有这个肚量,就他妈别当兵!”
小碾子愣愣地仰着脸,望着谢石榴。
谢石榴:“听懂了吗?孩子?”
小碾子庄严地点点头。谢石榴又为小碾子灌了一大口。
一直趴在钥匙眼儿偷看的妇女,感叹不已:“喔哟哟,就跟老母牛喂奶似的。”
谢石榴又踢了踢沙盘:“不过,这个一○九二,该弄清楚还是得弄清楚,鹿儿是捡了便宜,还是真有一套,也要说清楚。战场上下来,开开会,盘盘泥巴,多打明白仗,少打糊涂仗,才是这个军队真正的老传统。你把这沙盘再弄弄,我去叫人,把该来的都叫来。”走到门口,谢石榴回过头,“小碾子,把你脸上的泥点子擦掉。”
小碾子问:“哪边?”
谢石榴:“左边。”
其实小碾子的脸上什么也没有。小碾子一擦,反将手上的泥蹭上一片。谢石榴“哈哈”大笑着出门,在门外扔回一句:“过去,你的老子们经常这样干。”
大海,辽阔无垠,博大雄浑。
路上,贺紫达、姜佑生、楚风屏、周天品、鹿儿、大碾子跟在谢石榴的身后。
谢石榴:“楚风屏,你就别去了,去看看丁丁。把这个拿去叫她也喝一口。喝了,她还是自家的孩子。”谢石榴将水壶递给楚风屏。他叹了一口气,瞪着姜佑生说:“这件事,你姜崽子和贺伢子都有错误,大错误。”说完,谢石榴大步直走。
姜佑生退几步,对楚风屏轻声说:“找到丁丁,叫她还是回家住。”楚风屏点点头。
周天品对鹿儿说:“你姑被中午的事吓坏了,本来她想请所有的人晚饭时到她那儿去,尝尝台湾风味的烤肉。”贺紫达听见,感叹了一句:“根儿,是菩萨转世。”鹿儿忙道:“我去。多晚,也去。”
小街深处,大杂院内,有一间极普通的小耳房。昏暗的灯光下,一头卷发的丁丁,在对着镜子涂口红。镜子边上是吴文宽的相框。
丁丁内心剧痛,自轻自贱地把口红越涂越不像话,先弄了个“血盆大口”,又点了一个眉心,画了两个红脸蛋,最后画了两撇胡子。她对着镜子出着各种各样的鬼脸。接着,又用唇膏在吴文宽的脸上画着红嘴唇、红脸蛋、冲天辫、胡子、眼镜……
招待所。贺紫达、谢石榴、姜佑生、小碾子、大碾子、鹿儿、周天品,从左至右,围着沙盘在地上坐了一圈。
贺紫达边用手指示,边讲:“一○九二位于边界骑线点,敌方坡缓,有公路相接,支援、供给便利,而我方完全相反……”
钥匙眼上,挤满了脑袋。七八个住所的军人在挤:“叫我看看。”“看什么呢?”“高级军事会议。”“嘘一小声点儿。”
房内。姜佑生:“鹿儿,你那个打法,部队那么分散,怎么指挥?”
小碾子:“当时我也是这么问的。”
鹿儿:“还是用号。长音代表十位数,短音代表个位数。”
谢石榴来了兴趣:“那你指挥第五十九小组冲锋,莫不是要吹五长九短,那多麻烦。”
鹿儿:“个位超过五的,短音在前,长音在后。”
谢石榴笑笑,十分欣赏。
鹿儿:“其实战法讲清,战士们会主动协同动作,指挥员只须个别点到即可。”
谢石榴:“大碾子,你是旁观者清,你说说。”
大碾子盯着沙盘,半天才冒出一句:“真他妈的痛苦!”
马路。路灯下,马路牙子上,杜九霄与金达莱守着一个冰棍箱吃着,聊着。面前已吃出一大堆纸、棍。马路上空无一人。
杜九霄:“不是我打的吴文宽那一枪,他怎么会倒在半路上?不是吴文宽被军工抬到你们医院,又怎么会碰上丁丁?我这一枪,真够积德的,也真够缺德的。”
身后小食店的窗户,伸出一个老太太的头:“吃完了,把箱子给我放在门口,我要睡了。这俩解放军,铁打的肚子铁打的兵。”
金达莱:“想起丁丁,我就想哭,你说她……你说她……吃!”
小屋内,吴丁把领章一针一线地又钉在军装上……
楚风屏找到丁丁的小屋前,她敲了敲门。开门的人吓了楚风屏一大跳——丁丁一脸的怪样!
走进屋后,楚风屏痛楚地叫了一声:“丁丁……”
丁丁冷冷地:“你等等。”她在脸盆里倒了一些热水,洗着脸。
楚风屏看见画得乱七八糟的吴文宽的相框。丁丁马上扑过去,把相框扣在桌上。
楚风屏:“天下还真有这样的事,你贺叔叔不让你找,只让你等,还真就让你等上了。”
丁丁洗脸不语。
楚风屏:“给他治伤时,你把别人都支走了,就你们两个,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哗哗”的水声……
楚风屏:“我相信你,总不会把这边的什么秘密告诉他。”
水声……
楚风屏怜惜地叫道:“丁丁……我的小丁丁!”
丁丁一下扭过脸来,满脸的不知是水,是泪。她扑到楚风屏怀里,哭叫道:“妈妈——妈妈——我还能叫你妈妈吗?”
楚风屏抚摸着丁丁的头发:“孩子,看你外表风风火火的,这肚子里的痴情还真有些像你的亲生母亲。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有人说你父亲是国民党特务,把他关了起来,多少人劝你母亲,反正没结婚,算了吧。可你母亲就是一言不发,她也不说你父亲坏,也不说你父亲好,就是一个‘等’字。一直等到问题弄清楚,你父亲放回来的当天,她就找组织申请结婚。可是丁丁,你呀,等到国外去啦。”
丁丁:“吴文宽是敌人。但他也是好人。”
“什么话,冲这种思想,开除你的军籍,就一点儿不冤。”
丁丁慢慢离开楚风屏的怀抱,拿起军装,欲拽掉刚钉上去的领章,但她又停下手,缓缓将军装叠好,用头巾包了起来。
楚风屏默默注视着。
丁丁将军装平平整整地放进了箱子。
楚风屏拿起军用水壶:“这是老号长带给你的,要你喝一口。”
丁丁接过去:“酒吗?”
“酒。”
“庆功酒?”
“庆功酒。”
丁丁未喝,捧在手里看着。
楚风屏:“老号长说,喝了,还是自家的孩子。”
丁丁站起身,把水壶挂在墙上。她最终未喝。
楚风屏复又痛楚地看着已然极其陌生的丁丁。
夜,鼻笛如箫。
周家阳台,鹿儿用鼻息吹着那种特殊乐器。其声微弱,反而尤感其韧。
根儿走上阳台,听了一会儿,轻声道:“鹿娃,肉烤好了。”鹿儿缓缓停下吹奏,说道:“姑,我想看看那三个铜瓶。”根儿看


![[机甲]重生军人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48/4846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