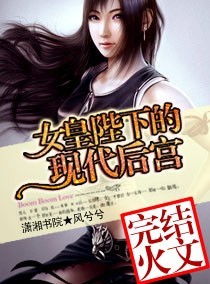陛下,认命吧(更新至完结)-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宣帝便丢下手中奏折,叫了个侍立在门外的宫女磨墨,自己站起身来自背后欣赏着这副红袖添香的美景。在那宫女回身向他示意之前,他就迅速转过了脸,直到人退下之后才又走到桌旁,重又展开那道奏折批阅。
这道折子,是参相州知府贪墨朝廷救济银两,闭门不纳流民的。
如今宣府一带开战也有月余,西北流民渐多,各省皆奉旨安顿。就连京畿也由京兆尹设了临时住所,按时放粥。
因时值二三月间,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国库银两还要支援前线,难以拨出太多。左右宫中无人,内库也不是没花过,宣帝便将前几朝积存的银两拨向各州府,叫府县安顿流民、开仓救济。
而这个相州知府,贪的正是宣帝特地叫人调出去的私库银子。
这些事宣帝原也见得多了,若贪的只是国库银子,还不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可这本是宣帝打算纳妃选美的钱——当皇帝的都肯为了百姓打光棍了,一个小小知府竟敢把黑手伸向这银子上,若不拿出来狠狠治一回,宣帝自己都亏心的慌。
尽管宣帝没能成上亲其实和这银子无关,但相州知府的名字已落到了他心上,而淳于嘉正是他心中做这事最好的人选。
——多见见贪官的下场,尤其是亲手整治几个贪官,总也能叫淳于嘉警醒些,不至于外物迷了眼,分不出自家性命与权势财货哪个更要紧。
发下旨之后,淳于嘉当天下午就进了宫辞行。
宣帝推己及人,体谅他不愿远路奔波的心情,亲自把他从地上扶起,拍着他的肩头劝道:“相州距京师不过四百余里,快马两三日便得来回,路上朕派御林军护送,幼道不必担心路上安危。”
淳于嘉受宠若惊,低头答道:“臣岂敢爱身而忘公。今日嘉入宫是来辞别圣上,也请皇上多多保重龙体。如今方交仲春,正是寒温不定之时,皇上朝务繁忙,更要注意添减衣物,以免受寒。”
宣帝心中熨帖不已,也温言抚慰道:“幼道放心,宫中自有良医在,朕哪会就病了?倒是你在外奔波,要更小心……哪怕路上慢些也不怕,务必以安全为第一要务。”
他面色和悦,说出的话更是字字声声透着关切,听得人如坐春风。淳于嘉抬起头道谢,正见宣帝满面关切之色看着自己,心头一热,不期然想到王右军那句: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真神仙中人。
这话放到人君头上,却有些过于亲昵了。淳于嘉心头一跳,有许多话就想说出口。却不知怎地舌根发直,心底无数可说或不可说的话,明明都到了嘴边,竟一句也说不出来。
挨到最后,他还是带着一队御林军和满腹遗憾出了金水门,直奔相州去查那件贪腐案。
不只眼下的贪腐案,相州知府的后台他也要一揪到底。淳于嘉私心盘算着,总要揪出几个朝中与他勾结的大鱼,再叫他们吐出几百万银子,才不负宣帝将这般重任交到自己肩上。
淳于嘉怀着凌霄之志走了,宣帝在宫中却仍只是逐日忙于政务,上朝时偶尔被何丞相骈四骊六地夸一回不好女色、勤政爱民,听得几乎心如死灰。
然而这朝中毕竟还是有晓事的官员。譬如礼部尚书,也就是原来劝他立妃的宗正寺卿贺徵,就又一次奏上了深合上意的谏疏——已进了三月,宫中该挑日子主持耕藉礼和先蚕礼了。
耕藉礼且不提,先蚕礼却是要皇后主持的!
宣帝简直要扬眉吐气了,然而在朝上议起此事时,他还是板起了脸,带着淡淡忧郁无奈问何玄:“朕后宫空虚,莫说皇后,连低品级的妃子也不曾纳。先蚕礼竟无人能主持,这可如何是好?”
何丞相捻着白玉笏板,不紧不慢地走到列中,低头奏道:“圣上何必忧心,宫中自有太妃太嫔在,不若择其一主持此事。反正百姓看的不过是朝廷爱民之心,何必太过在乎人选。”
宣帝还想说什么,太尉岳雩也随他出列,附和道:“何尚书所言极是。陛下如今正对西北用兵,其他事务不得不一切从简。先蚕礼在前朝亦非年年举行,岂宜为此一礼而牵扯更多事端?”
三公之中出来两个反对的,贺徵位份又不足与这两人相抗,而他最宠信的能臣淳于嘉偏偏又出了京……宣帝便也不再期待群臣,自己打落牙齿和血吞,默默地再度承受住不能纳妃的痛苦,依着礼部安排去演耕。
这项祭礼他前世已做过数回,熟得不能再熟,对推那耕犁也没什么太大兴趣,演礼之时便丢下犁不管,只拉着那两个老农的手,细问他们生计如何。
那两个农民也是京兆尹千选万选出来的,面对皇帝也敢说几句话,都憨憨笑着,不停地夸耀当今是如何盛世,人人衣食丰足,把宣帝赞得堪比三皇五帝。
只是他们面上虽带笑容,眼底却有几分隐忧之意。
朝中奉承宣帝之人何止百千,就连淳于嘉那样的人精都不能全然哄过他,何况两个农夫?宣帝只随意套问几句,便从那老农口中得出真相——京西一带,流民杂居之处,竟有几个人高热不退,似乎身上身上还生了斑疹。
这是——春瘟!
宣帝霍然起身,把演礼之事全数丢下,乘龙辇从后苑直回到垂拱殿,路上已紧急吩咐人召何丞相等朝中重臣及太医院提点、院判等人觐见。
何丞相与岳太尉入宫最早,听得宣帝说了此事,也都大惊失色。京中若流行起瘟疫,定是一桩大祸不提,更要紧的是,那瘟疫到底是从何处生发的?若真是从西北而来,宣府的几十万大军是否也会受到波及?
本就是战况胶着之时,军中万一再发了时疫,只怕顷刻就要不战而败,叫西戎人长驱直入,侵州占府了。
何丞相连羽扇都不摇了,面上却还很沉静,安抚宣帝道:“京中天气远比西北炎热,流民居住一处,或因水土不服而发病也数寻常。军中奏报一日一至,都无异样,咱们倒不必思虑太过。只是有些事还是要预先准备……还是调些良医和药材送往西北和京城吧。”
三人先在殿中计定大局,待京兆尹与太医院人等到了,便由丞相与太傅二人安排细务,并听取诸人意见。
太医院提点当即受命,派人去京郊查看具体病况,宣帝便又拨了些私库银子,晓谕各部安排人手,购入药材,预备应对疫情。
应对疫情,说起来只是一句话,落到实处又有千头万绪。要钱要人,哪里不伤筋动骨?若真是朝中有的是得用之人,也不至于连皇帝要选个妃都拖着不办了。
直商议到晚上,留几位大臣在宫中用罢了晚膳,宣帝才得回宫休息。他也无心睡眠,批罢奏章就叫王义拿了些医书来。翻着翻着,便不由得想起了上辈子。
他记着元初这两年该是风调雨顺,既无西戎侵边,更没有时疫的,怎么如今他才一登位,就闹出这么多不祥之事?
莫非是神仙不满他杀了成帝自立……这神仙真垂青他么?怎么成帝强占他时这神仙从无一丝相救之意,他推翻暴君之后,倒是处处不顺?
宣帝想得心头火起,也看不下医书,随手扔到案上,推开窗透气,便闻到一股细细甜香。展眼看去,院中正有几株桃花罩在雨雾中,映着满月灯火,泛起淡淡光华。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他连室家都没有,还看的什么桃花!宣帝烦躁地将目光转落到灯火上,只觉着身上燥热,便在窗口吹了阵风。
王义进来送茶,见他吹着夜风,便连忙把他拉开,口中念叨着:“我的圣人啊,这才刚三月,夜风还凉着呢,要是吹病了怎么办?”
宣帝随意敷衍两句,端起杯盏一饮而尽,便把人打发出去。自己一夜辗转反侧,尽想着怪力乱神之事。
连疫情的进展也不叫他满意。派出去的几个太医有说是热在营分之疾,有说是热盛动血之相,病人越来越多,却也未拿出个管用的方子。
唯有一点值得宣帝高兴的,就是军中暂且未见病情。
随着朝务日渐繁重,宣帝心中越来越烦急,身上也燥热得穿不住衣服。偏偏到了耕藉礼那日,他还要换上正式礼服,先行过一个十二分繁复的祭礼。
待行过礼,宣帝只觉头脑昏沉,口鼻都要冒出火来。好容易换过礼服,到了谡田当中,才觉有一丝凉风自东方吹来。
然而这风竟也不能提神。宣帝扶着犁还未迈步,忽然觉着鼻中涌出一股热流,眼前一黑,身子便直挺挺向后倒去。
19、侍疾·上
宣帝这一病倒真是来势汹汹,人一倒下去,就再没能起来。
开始御医只当他这些日子政务繁杂,心中本就有火,夜里又贪凉着了风寒,有些发热而已。孰料一剂桂枝汤下去,这病竟一发不可收拾起来——宣帝当晚便又鼻衄出血,神智也有些不清楚了。太医院诸人又重新探脉,试着开了小青龙汤,又用凉水为宣帝擦身降温,法子使尽,竟也不见好。
宣帝被折腾得也睡不沉实,歇过一觉,略略明白了几分,忽然叫王义:“你去告诉何丞相:朕白日发病之事,万不可传到西北,以免军心动摇。”
王义带着几分哭腔应了喏,又苦苦劝他:“圣上如今可安心养病吧。若不是前些日子贪凉,睡得又晚,今天怎么会病得这么厉害呢?”
宣帝也叹了一声,只觉着身上燥热难当,偏又发不出汗来,便随手将寝衣扯开了几分。眼角余光不经意扫过领口间,却叫他当场愣住——那一片早已恢复洁净的胸口上,竟多了几点或淡或浓的红斑。
莫不是成帝作祟……还是那个神仙降罚于他了?
宣帝实在不敢多看,自己合拢衣襟,紧紧咬住齿关,心底似泼了一盆冰水,当即寒彻入骨。他怔怔坐了一阵,脑中仿佛都空了,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低低叫了王义一声:“替朕拿笔墨来。”
王义劝道:“圣上病体沉重,不可劳心费神……”
宣帝不耐烦地说道:“叫你拿就拿来,朕纵要死也不差这一时!”
王义拗不过他,委委屈屈地奉了纸笔过来。宣帝提起笔来,却见手已有些发抖,便叫王义斜托着纸,自己拿左手握着右腕,凝神定气数息,终于稳稳落了下去:
“大将军如晤。前日奏疏中事,朕已尽付六部处置,必不使卿在军中受人掣肘……”
只写了短短几句话,宣帝便觉眼前有些发花,也就扔下笔,吩咐王义:“朕以后怕不能再写信了,这封你先收好,明日着人送至军中,安抚住大将军……”
他放下手时,腕间一点红色半隐半露,正落在王义眼中。
王义急得连信都扔了,卷开他的袖子看了两眼,忽然厉声叫道:“癍疹……圣上,您这怕是着了……时疫了!”
他一声喊罢,便跌跌撞撞地跑出去叫太医。宣帝便将袖子卷了又卷,干脆把上衣脱了,看过胸腹两臂。果然各处都浮了些斑痕出来,有深有浅,形状也不大规整,就连四周皮肤都有些发红。
原来是染了时疫……宣帝心头竟有些喜意。虽说他一向也不大信鬼神之事,但重生以来,许多事都透着蹊跷,逼得他也不由得疑心生暗鬼。此时知道了是瘟疫,倒比成帝来向他索命……至少说起来也不那么丢人了。
宣帝因便轻松了几分,重新将衣袖套上,又捡起那封书信——他既得了疫症,这信却也万不可送到军中了。只愿在朱煊发现不妥之前,他这病已能好起来了吧。
宣帝苦笑着将方才写的那封信撕碎,叫宫人拿去火上烧了。不一时太医便鱼贯而入,这回面上却比从前更惶惶,重新把脉观舌,看了宣帝手上红斑,又问了王义饮食情况,五个人就开出七八个方子来,总以清泻疏导为主。
可几剂方子下来,也未见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