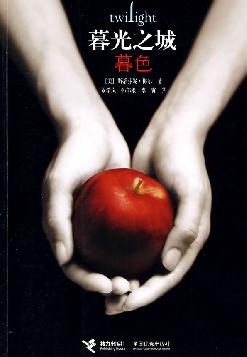焚心之城-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一直闲散。后来被介绍在一家运动俱乐部里做跆拳道教练,每天五场,每场三节,每节30分钟,间歇10分钟,总共做10个小时,一天下来累得要瘫软下去,最后常常感到不是汗水从身体里流淌到衣服上,而是衣服上的汗水被身体吸收掉。
“你不要命了?又不缺钱花,何苦这样拼?”蕊儿一边为她洗澡一边埋怨。只有卢米自己知道为何如此,为了忘记。
酒吧只在周末休息时有机会来,看到被刺伤那个女孩子肚子上的白绷带脏不拉几地缠在那里,没有任何遮掩,提示每个看到的人底下有个不致命的伤口存在,好像是值得炫耀的资本,让卢米觉得恶心。
“应该刺在心脏上??”卢米曾恶狠狠地小声对蕊儿说。
蕊儿吃一惊,瞪着空洞的大眼睛看卢米,眼神里是不理解的询问。卢米不解释,只嗤嗤地笑个不停,让蕊儿以为她喝醉了,在说着疯话。
“他追求我呢。”有一天蕊儿回家后捧着满怀的红玫瑰喜滋滋地说,像捧着一团正燃烧得凶猛的火。火焰舔着她白嫩的脸庞,看起来美艳非常,让卢米都惊住。
“你??能行吗?”
“不知道??也许他不要这个。”蕊儿轻轻地叹息,因为知道自己说的不是真的。
“管他,享受一时是一时,之后如何,我怎顾得了?”蕊儿又叹息。
第二天卢米特意从运动俱乐部请假到蕊儿所在的内衣公司接蕊儿下班,看到追求蕊儿的那名年轻的内衣设计师,白白净净的戴眼镜的男孩子。但卢米从他看蕊儿的目光里看出快要溢出的欲望正波涛汹涌,让卢米感觉有说不出的绝望,对蕊儿,也对自己。所以两个人很早就来到酒吧买醉,用酒精麻痹被现实刺痛的神经。
“放开吧??不会有结果??又何苦挣扎?”卢米劝蕊儿。蕊儿倔犟地咬着嘴唇,一副坚持到底的模样。
“大不了是个死,我不怕??”蕊儿说出最骇人的誓言。卢米却透过这一句看到停放在未来路上那个凄惨的结局,被惊吓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死亡是人生尽头的唯一结局,但不应该是人生道路上的唯一选择。”卢米想对蕊儿说这个,但觉得和蕊儿一直以来忍受的痛苦相比这句话轻飘得像个不该被放出来的屁,所以忍住。
很久没有喝过这样多,卢米难受得想将脑袋拧下来不要。
走出酒吧,让夜风凶猛地吹,逗引出胃里的酒,吐在酒吧前的花坛里正盛开的叫不上来名字的花朵上。心里想:自己蹂躏掉现实中的花儿,真是作孽,就像命运蹂躏掉想象中的蕊儿一样卑鄙可耻。同时在心里悲哀自己是不是命运将要蹂躏的下一个对象?或者正在被蹂躏的过程中也未可知。
然后抬头看见一个人影正在自己的前面不远处对着一辆红色的车发呆。
光线幽暗,卢米看不清他的侧影。但凭着女人特有的本能,卢米立刻认定他是君。因着心中“我不要被命运蹂躏”的叫喊和挣扎,卢米疾走几步,差一点张臂将君抱入怀里。但自小养成的羞怯和矜持及时阻止了她,让她傻乎乎地站在他的对面,看着他大大咧咧地和她瞎聊。
“路多长呵。”卢米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感叹。
其实鞋子早就让她的脚不舒服,不舒服到疼痛的程度。但卢米舍不得停下来,坚持着疼得想要哭出来的坚强和君一步步地向前走,并感觉过去的和未来的生活自己一直都在以这样的心态坚持,坚持这种疼得想要哭出来的坚强??谁来疼惜呢?君显然无知无觉,走得轻松自在。于是卢米想:在现实中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情景呢?就像我和君这样,一个忍着几乎不可忍的疼痛坚持,一个麻木得毫无知觉,一起慢慢地向前走,一天一天地度过,什么也不交错,什么也不分享,什么也不感觉,什么也不纠集,什么也不交流,就像两个没什么关系的路人一样呵。这多可怕,不如一个人。
卢米知道凭着君那粗糙的个性一定发现不了自己此时所忍受的痛苦,所以不怪他,直到坚持不住。
看着君笨拙地为自己的脚包束,卢米忍不住在心里幸福地笑。一再地想要告诉他“我想爱你”,却不敢。也才知道这一句是所有语言中最难以出口的几个字,因为出卖的太多,沉重到失败不起。
但卢米知道她和君需要一个开始才能继续下去,就像电视机需要一个电源开关啪地按下去才能在屏幕上出现图像一样。可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她发现她和君之间没有那个开关在,所以没有电流流过。
敲开门,看着蕊儿哭过的红肿眼睛和被酒精蹂躏得不堪的面容,卢米忽然有说不出的心疼汹涌上来,猛地将蕊儿紧紧地抱入怀里。
蕊儿正委屈得厉害,忽然得到这样的疼惜自然兴奋,和卢米搂着大哭不止。两个人各哭各的伤心,谁也不管谁。
第二十八章 天使与魔鬼
…………………………………………………………………………………………………………………………………………
犹豫了一整天,终于决定第二天去看芬。但早晨起来后发现勇气就像流光的水一样,忽然又消失得一干二净。只得一个人闷在家里看书,等待晚上敏的到来。
敏却提前打来电话,说晚上临时有事,不能来,叫我异常的沮丧。
曾有一刻特别想去酒吧喝个酩酊大醉痛快一下才回来,让要一个人孤独度过的无聊夜晚有所改变。于是我脱光衣服,站在花洒底下用凉水拼命地冲,直到头脑冷静,想去酒吧的念头黯淡下去为止。
刚刚收拾整齐,听到敲门声。打开,看到敏站在外面。
“不是??”不等我说,敏推开我,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随便地走进来,踢掉脚上的鞋子,也不穿拖鞋,光着脚啪叽啪叽地直奔卫生间而去。我有些奇怪,直到闻到残留在空气里的、浓重的酒精味。
敏吐了好一会,但没有什么出来,只是干呕。凭我的经验我知道这样会更难受,所以一直鼓励她。但敏还是放弃了,让我扶着回到卧室里,然后象段失去知觉的木头一样倒在床上。
“喝得不少呵??”我用湿毛巾擦她的脸。她不让,挣扎着将我推开。
“知道我为什么去喝酒吗?”敏的舌头还利索,让我觉得惊讶。我摇摇头。
“因为无聊呵,你不懂吗?”敏抹一把脸,然后我看到她眼睛里的泪水正要流出来。
“你不会懂的,我的无聊,你怎么会懂?”敏哽咽一下。
“其实我也不懂你的,是不是?我们都不懂得对方,却还要假装相爱,假装做爱,假装快乐,多无聊呵??”敏又哽咽起来,慢慢地闭上眼睛。
我不知自己听到的是什么,也不知应该想些什么,只麻木地坐在那里,感觉手脚正慢慢地变得冰凉。血液都不知流往何处,反正不再肯温暖我正寒冷下来的心。
敏以僵硬的姿势睡去,双手举向上方,像要抓住什么似的用力。一条腿因为裙子的局促而无奈地压在另一条腿上,并不时地扭动一下。脚趾偶尔也会抽搐,让我看着奇怪,才知道她其实在睡眠时也和自己挣扎个不停。额头上渗满细密的汗水,一颗颗晶莹地反射着台灯漫无目的的光芒。终于汇成一条小溪般的水流,沿着她的鼻翼向嘴巴淌下去。
我用毛巾擦去她的汗水,帮她脱去小衫和短裙。看着她被抹胸紧紧地束缚着的乳,我犹豫一会,帮她解放出来。敏显然还在酒醉里,身体绵软得出乎我的想象,任凭如何翻转而不做一点抗争。这样的柔弱深深地打动我,就像看到初生的婴儿一般透彻心底那么疼惜。我忍不住将她的裸体紧紧地拥在怀里,让她滚热的体温烫着我冰冷的脸和泪水。
敏忽然有片刻的清醒,睁开眼睛奇怪地看我,嘟囔一句什么,伸手推向我,那么用力地,好像要推开临近的危险。我只好将她放下,为她盖好薄薄的布单。
窗外今夜的黑暗和以前的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好像加深许多。
不知为什么睡得特别地沉,醒来时天已经大亮。看窗外太阳的高度该有九点钟了吧?敏自然早已不在。
起身后看到桌子上有一片纸在那里白晃晃地闪烁,上面似有黑色的字在不停地蹦跳。我抓过来看:‘就这样吧,不要再找我。’没有署名字。
我把这张纸放在眼前看了好一会,突然觉得有说不出的憋闷。我将纸用力地揉成一团扔出窗外。
找敏的睡衣、我洗干净收在衣橱里的她的内衣,还有放在卫生间里的她的牙刷、沐浴露、洗面奶、润肤霜、香水等,结果统统不见。
我发一会呆,突然想起那张放在我衬衫口袋里的她的名片,急忙翻找,才发现也同样被她抄走。上面那个随时可以找到她的电话号码我却无论如何也记不完全,才发现好像早就知道应该忘记似的而从来没有用心记过。
走出君的住处,敏还是站在楼下犹豫一会,然后才似下定决心一般离去。
没有征兆,在早晨起来后突然就决定如此,好像努力爬出要将自己吞没的沼泽地一样急迫。
君还在傻乎乎地睡着,意识不到醒来后将要面对怎样血淋淋的残忍。敏这样想着时倒也有些不忍,但还是冷静地收拾自己的东西,就像收拾此时破烂的心思一般彻底,连君放在上衣口袋里的自己的名片也不放过。
然后仔细地想,发觉没有剩下一丝可寻的痕迹后才罢手,同时对自己暗暗地吃惊,不明白怎能保持这样的冷静和认真,是在其他事情上没有体现过的作风。
昨夜的宿醉也是没有来由的,是自己一个人跑到和君第一次见面的酒吧里孤独地喝个痛快后开始的。
其实不是因为君,敏觉得在心里自己还没有在意他到这个程度。是因为自己,因为一直在纠缠自己而无法逃离的那么深的无助感,是欲望和自我的挣扎到了不堪面对的两败俱伤,谁也不肯退让,最后被打败的是敏自己。
是不是每个人在长大的过程中都要体验这样的挣扎呢?最后有多少人被欲望打败而沦落为麻木不仁地随波逐流的行尸走肉呢?这个蜕变的过程中所要忍受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痛呢?
敏绝望地喝酒,一边慢慢地回想被欲望捆绑的不自由是怎样黯淡的黑夜里的无可奈何,因此更加地绝望。
在路上,敏的心里乱得没有头绪,不明白这一次自己和欲望的对抗会有怎样的结果,是不是还是以自己的一败涂地告终?她甚至有将手里提的装着从君那里收回物品的塑料袋扔入垃圾桶的冲动。
敏说不准自己是不是真的懊悔,也不知是该懊悔当初和君的相识,还是应该懊悔今早和君的分手。分手固然痛快,让她有从泥泞一般龌龊的罪恶感里解脱出来的轻松。但也突然有一种自己拥有的什么从手里失落的空虚感让她觉得万般地不舍。
她先将手中提的东西送回家里,然后乘车来到学校。
学校对敏来说是块独立在尘世之外的净土,她在这里可以心无旁骛地练琴。但也只能练琴,没有别的什么可做。导师是位七十多岁、瘦得走路都没有声音的老人,也懒得说话,只肯半闭着眼睛听。敏今天拉得比平日投入,不觉间被自己感动,忍不住泪水簌簌而下。
中午一个人去一家常去的川菜馆吃饭,还是水煮肉片和水煮鱼这两个菜。肉片和鱼都吃得很少,敏其实只喜欢那种凶狠的辣。老板娘显然是个很热心的女人,对敏存有大量的好感,坐在对面和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让敏失去很多胃口,吃得更加地少。
从菜馆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