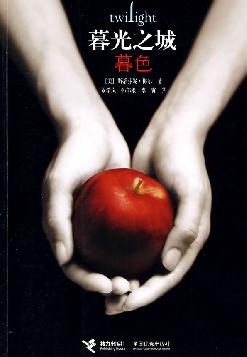焚心之城-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人逛商场,在一对对男女之间穿越,冷眼看着他们旁若无人地走过,心里报以冷笑。买很贵的衣服和鞋子、化妆品和手袋,但美好的感觉只在付款时存在,回到家里就荡然无存,将东西扔在一边不再理会。
一个人看电影,赶夜场的三级片,瑟缩在角落里一边看一边自慰。出来后深切地自责,发誓再也不来,过几天又照旧。心里恼恨,以为自己很失败。
一个人吃烛光晚餐,喝1972年的白兰地。醉掉后急急地往家里赶,冲入卫生间大口地呕吐。然后坐在淋浴下面孤独地哭很长时间,让热水洗去泪水的痕迹。但没什么用,躺倒床上后还要哭一会儿才能睡着。
芬不知自己哪里做错要承受这么沉重的折磨。
但想不明白也要承受呵,就像鱼想不明白为何要活在水里却还要活在水里一样,所以鱼很憋闷。芬这样以为,并能理解。
觉得跑步时不穿内裤,让胀大的下体跟着一起蹦跳这种感觉很有意思,遂决定以后就这样。
已经能在不休息的情况下坚持跑到雷达站的下面,然后慢慢地走回来。也习惯了大量地出汗后那种虚脱一样痛快淋漓的感觉,迎着劲吹的风有说不出的爽快,好像让身体里充满什么似的,简直要爆发出来。
杰、英和权打来很多次电话,我都不接。
我想听到雅芬的声音,但她再没有打过来。我隐约地知道我们完蛋了,连最后那一点可怜的友谊也没有剩下。但我不怨怪她,我知道她必然也很无可奈何,就像我不能打给她一样。
《亨利四世》只有《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这一册,余下的怎么都找不到,让阅读思绪悬在半空的我烦乱不堪。于是我来到图书馆。
丹看到我,微微地笑一下,继续她的忙碌,直到快下班时才向我走过来。
“还好吗?”她在我的对面坐下,手里抓着一个卷在一起的画轴。我点点头。
“跑步很累,读书很累,一个人坚持着孤独也很累,没别的了。”
“再也没有去过酒吧吗?没有喝过酒?”丹好像不肯信。
“没有。”我自嘲地笑一下,其实在心里觉得很得意。
“那很好呵。”丹用画轴打我一下,很亲昵地。
帮我借《亨利四世》余下的两册后,丹送我出来。
“还想着我自慰吗?”丹又一次问起。我摇摇头。
丹笑起来,但目光里有掩饰不住的失望让我看得一清二楚。
终于进入冷战时期,丹和他沉默着面对,望着对方尴尬的模样发呆。
丹犹豫着,心痛到好像要死掉那么难熬,但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分手’这两个字。虽然她知道自己需要这两个字来割裂自己的感情和生活,就像病人需要药片延续生命一般必须。可深藏在灵魂深处的软弱此时却跳出来叫嚣着阻拦,让丹不忍心对自己曾经最执著的付出下手,只能像个被按在案板上的什么似的等待着他挥舞起屠宰的刀。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无奈更让人不可忍受呢?但丹知道自己只能忍受。
好在人的免疫机制里有一项实用的功能,就是逐渐麻木的感觉可以随着疼痛的加剧而更加无所谓。丹就凭借着这样涣散的心态坚持着,就像站在铁道上等着呼啸而至的火车一样等着将自己撞得血肉横飞的现实的到来,并像个疟疾患者似的抖着身体不寒而栗。
生命中有多少曾经美好的要被后来的现实粉碎呵,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这有多么残忍?
更残忍的是好像还从来没有人因此发出过感叹,大概都以为那是必须如此的一种视而不见吧。
如今丹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绘画上,在铁线描和晕染之间寻找能够支撑自己继续平静地生活的勇气,因为她需要。
丹最擅长的是工笔重彩观世音菩萨造像,掩映在缭绕云雾中的那种。看着那张慈眉善目的脸庞在自己的笔下一点点显现,丹常有恍惚的错觉,以为她就能拯救自己的不幸。于是急急地赶,贪黑熬夜地画出来挂在那里。才发现她只是望着自己笑,其中的暧昧虽然不是嘲弄,但也并不同情。
丹知道在观世音菩萨的法眼看来世人的一切痛苦都是自找,自己当初不也是决然地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吗?而今不过是路走到尽头。因为没有规定每一段爱情都必须要天长地久那么遥远,不然这世界岂不乏味?
但丹真的不甘心自己的这段爱情只是生命中一个应景的点缀,只为让自己长大,懂得世事无奈才是常态,懂得人生悲苦才是必然。
果真如此吗?即便长久,最后的结局也是乏味的无聊和彼此的厌烦?果真如此吗?丹一遍遍自问,但不敢给肯定的回答,因为怕自己因此丧失活下去的勇气,丧失爱的勇气,甚至丧失自我,成为越来越多抑郁症患者中的一个。
这样坚持了半个月,感觉一切好像都好得没话说,于是我决定打电话给敏。
不知为什么,照着名片拨那串号码时我的心跳得异常猛烈,好像要承受不住似的。只有片刻的嘟音,然后是个沙哑的声音接听,我知道是敏。
“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打给我了呢。”敏压低声音说,显然她的身边还有其他人。
“过来吗?”我问话的声音一定颤抖得厉害,敏“喂”了一声,表示她没有听清楚。
“我说??你过来吗?”
“嗯?”敏犹豫了一下。
“什么时候?现在吗?”不等我回答,她忽然转头向旁边的人说什么,口气很严厉。
“我晚一些过去,你准备好吃的,我要呆一整晚呢。”然后她又向我说,口气有说不出的温柔,让我感觉自己好像要融化掉一样浑身软绵绵地没有力气。
放下电话,我望着窗外有些云彩的天空发了一会呆,在心里回味着刚才那种似乎要把人打倒的巨大的幸福感。
我买回苹果,是最贵的那种。又买回西柚和葡萄,也是最好的。还有开心果、五香杏仁、巧克力和薯片,外加一瓶波尔多干邑和一箱七喜。如此便花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让我对未来吃什么活命有片刻的茫然,但很快被将要见到敏的喜悦冲淡。
敏来得比我期待的晚很多,让等得焦躁不安的我正犹豫着该不该打电话过去询问。
她今天穿一件有圆形领子和短短袖子的素色小衫,下面一条同色的长裙上装饰着波浪形的白色蕾丝,是随意的打扮,看起来很清爽。手里提着两个口袋,一个里是刚刚出炉的海鲜披萨,一个里是她换穿的没有惯常所见镶有蕾丝花边的粉色内衣、青蛙头的怪样子牙刷、瑞士产的梳子、薰衣草味的沐浴露、法国产的洗面奶、蜂蜜润肤霜、很贵的香水和白色上印着米奇图案的睡衣等和美丽香甜的女孩子有关的各种小物件。
敏环视一圈,满意地笑。
“好像换了个地方,我喜欢。”她在餐桌前落坐,将披垂下来的长发挽起成一个髻,用揣在口袋里的白色发卡夹住。
“吃饭好吗?我饿得不行。”
敏只喝一小杯没有兑七喜的干邑,但两颊已经被绯红染透。她摇着头不肯再饮。
“去洗吗?”她用自带的餐巾纸擦净嘴唇,言语直白地问我。
“你想吗?”我收拾着桌子,回转目光看她。
“嗯,去吧。”我说“好”。
敏脱去小衫和裙子,露出里面藕荷色的内衣。
“好看吗?我特意为今天买的。”我才注意到抹胸只是很小的一块布,刚刚盖住乳晕,剩下的都是蕾丝。内裤也只是窄窄的一条,让她茂盛的毛丛从两边支出很多。我笑着点头。
敏在花洒下很羞怯,和雅芬完全不一样。她洗得很仔细,一遍遍地使用沐浴露,让我觉得不耐烦。我忍住不说。
但我还是一败涂地,不比前一次强过多少。我懊恼地趴在床上,将脸埋进被子里。
“没关系的,我不在意。”敏亲昵地拍拍我,起身出去洗浴,擦润肤霜,然后穿着睡衣回来。
关掉灯,夜色也跟着沉寂。我听到她在耳边均匀的呼吸声,很久都没有变化。
“睡不着吗?”我翻个身,将怀抱向着她。
“嗯,换个地方就不行。”敏浅浅地叹息一声,任凭我将她搂入怀里,没有一点抵抗的意思。我低下头嗅她发间的清香,觉得很享受这个味道。
“说点什么?”敏问我。
“什么?想听什么?”我伸手轻轻地抚在她的颊上。
“什么都好。”
“嗯??”
“哎,就说??你以前和别的女孩子如何吧,这个话题我喜欢听。”她调皮地笑起来。
“以前吗?和别的女孩子?如何?你是指??”我倒觉得有些尴尬。
“你明白的。就是和别的女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关系,过程如何,结果如何,如此等等。说说吧??大男人嘛,不必害羞的。”敏鼓动我。
“嗯??好吧。我的第一次是在上初中,十五岁那年。”
“啊?那么小?”敏惊叹。
“是啊,现在想来都觉得很悲惨呢。”我随口胡扯地逗弄她。
“和谁呢?”听得出,敏对这类事确是很有兴趣。
“和邻居家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她个子很高,长得??还算好看。”
“是她勾引你吗?”敏变得越来越热心。
“是啊,很多次呢。”我心里偷偷地笑个不停。
其实确有那个女孩子在,但是我一心想着她,她却从不曾注意过小屁孩一个的我。和她之间唯一的接触是她曾教过我一次游泳,让我有机会隔着泳衣碰触到她的身体,并为她饱胀的乳那么柔软而暗暗兴奋许久,让她成为我意淫的对象。她嫁人那天我很伤心,独自躲在屋子里哭一个下午。现在想来只觉得好笑而已,就像少年懵懂时做下的许多件蠢事一样。
“那你??现在还想着她吗?”敏很小心地问。
“嗯,有时吧。”我在她的额头轻吻一下。不知为什么,好像引起她的不快。她扭动身体,离开我的怀抱,独自一人直挺挺地躺着。我的心里忽然就涌起一股无法形容的委屈,不知该如何是好。
“你的职业是??二胡演奏师?”我咳一声,借以稳定一下情绪,然后问。
“嗯,怎么了?”敏的口气不是很糟,但其中却含着拒我千里的冷淡。
“你是??学二胡的?”
“是呵,学了很多年呢,至少有??十五年。大学也是这个专业,现在在读研究生。”敏喘一口气,很大声,但很舒缓地。
“二胡??好学吗?”我觉得有意思,又问。
“嗯,就是闭着眼睛瞎拉。”敏的口气里透出不耐烦但又不想发泄的隐忍。我知道该闭嘴,只好沉默。敏也不说话,静静地呼吸。
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我心里有想抱住她痛哭的冲动,并在心里一再地问起:我们究竟能如何?但没有答案。我想问敏,终究不敢,只好作罢。让不知是她的肌肤还是睡衣上飘散出来的清香将我淹没。我们就这样躺着,各自在心里揣摩着对方此时的想法,想要接近,却又无能为力。终于慢慢的都疲乏起来,连探究对方的兴趣都没有了,象两个毫不相干的路人似的各自努力睡去。
敏起来得很早,收拾东西的声音将我惊醒。
“还要去上课。”敏正在系抹胸,向我做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我轻轻点头,其实心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想。
“这个??能帮我洗一下吗?”敏将换下来的胸衣和内裤放在床上,然后直起身体看我。
“今天是星期一,我??星期三来,好吗?”我突然有被巨大的喜悦打击后的眩晕感,竟窒息般地喘不上气来。
“哦,对了,今天晚上有我的演出,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