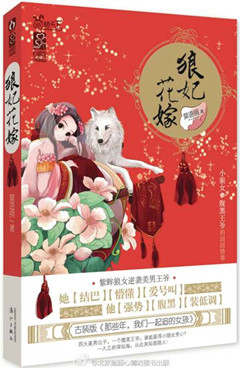��ɽ�ο�Ц�˹�-��1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ǡ���
��ȥ�����ݶ��ٹ���һ��ת�����ϣ���٧Ҳ����ͷ������ֻһ�˿��ߣ�����ֻ������ȥץ���֣�ûץ������٧һ˦����ֻ����������䣬����קס�ǰ�����䣬��٧ͣ�˽ţ���ͷ��������Σ���
��������ƣ���ɫ���ͣ����ݵ�������٧����
��٧������������������IJ��ɣ�һ������������������
����˵��������ȴ��ק�Ų��ţ���٧��ŭ�������������彣����һ�أ�����Ӧ�����ѣ���٧�ѵ����˽������͵ش��������ж���ǰ���������أ���ʱ������ˬ���٣��������������ϵ����������ˣ����������ҡ���
����һ�������ºͣ�������һ��������Ҳŭ�ˣ���ü���۵���
�����в��������������ģ���
������������������С����٧��Щ���죬�������Ŷ���˼������������ָ�������ȥ���������������ˣ��������ˣ��������ˣ�Ҳ��Ƣ���ˣ�����������
���ݵ��������в�����
��٧�����ŭ�ˣ�ץ�������������˻ظ���Ҫ��ѵ������������ͣ�������ǿ�û�����ⳡ�棬������ͷ����٧���������ţ�˨���ţ������Ѿ��������ۣ���٧˵����������������������ȴ�Ǹ����ߴ���۵��������죬������ŭ������ڣ����˶���ָ���������ǿڲ����ԣ���ʹ��������������ȱ���۰���������ģ���֪���۰�����
����������Ҫ���ų�ȥ����٧קס���������������ȥ���Ҷ��ˣ���
����һ�첲���������������ǰ����٧�����Ѿ��ڲ����գ�һ���������ϣ�ֱ�����ߵ��ڵأ�������������Ҫ�ܣ���٧ֱ�˹�ȥ�����ֽŰ�ס�����ݶ����Դ�һײ��ֱײ����٧�Դ����Σ������е���
���������ݣ����Ҵ��˳ɲ��ɣ�����������è���������İ�����
���ݸ���ѹ�ö����ã���������٧�������ҵ����������ô����ѧ���ˣ������Dz���צ�ӣ�һ��û�䣬�����ǹ����ӣ�����ţ������ҾͰ����㣬��������צ��һֻֻ���ˡ���
�������Ǻޣ���٧������ģ��������������ͷ�����������������ҧ����٧��ÿ죬���Ǹ�ҧ�����´�����٧���IJ��У����������Ҳҧ�����´�������һ��Ѫ�������
�����Ų����ҽ��˽�����ʰ�㣿��
���ݾ�ǿ������٧������һ�ѵ���
����ľ���ӣ��Ҳ����㣬�Ҳ����㣬�����ӣ��Ҵ�������ô�ˣ������ҧ�Ұ�����
��٧�Ѿ��۵�û�������곶��������������Ѿ͵��ڵ��ϣ�������������Ҫ�ܣ�Ҳû�����ٹ�����ֻ���˿������������������ҳ�ȥ���Ҷ����ˣ�������������ݾ��ҵ���������˫��˫��������������ԹԸ��Ժ�ȥ����
��٧�ⳡ�۵IJ��ᣬЪ�˺ü��գ�ȴ���ѵ��������ˣ��������ڸ��к��ھ����磬���ڱ���Ļ�Ź�������٧��ų��ţ�ֻ��һ������������һϯ�������������������ٹ�������ǰ���־��ྴҲ����˼��������ͷɥ�����ƺ��š�
���ų��˾�����������ģ����Ц������ˡ֮�����������¡���
ȴһϸ����������Ѫ�裬���ۿ�������������Ҳ��һ��ģ������������ȡЦ����
�������������˶���ԭ����Ϊ�ˡ���
��٧̧ͷ����������ͬ��Ԫ����һ��һ�����Dz��������˶��ǹ�����ڣ�����������赣�ҲһЦ�����ֵ�������ǰ�ⲻ�����ˣ���������ƽ�壬�����������𣿡�
������Ԫ��Ц����Ԫ������˭������ˡ֮����
����ִ�����ֹ�������������£���ԪҲ���Ҳ����£���٧������Ԫ���ֶ����ŵ���
����˵��ô����һ������������������������ң���������ȥ�Ǿ�������
���ŵ�����ˡ֮���������ױ���ʶ����֪�������£�ֻ�Ƿ��½����������ҵȷ���˳�ƶ�Ϊ���ˣ���̫��ִ����
��٧��Ĭ���ԣ����ε�������˵������Ⱦưɡ���
������ü��ת���к����������ݣ�ǰ�������ơ���
��٧������һ�ѣ�Ц�����������ô����ӣ���Ҳ������ʹ���ģ���
�����ѵ�ǰ����������������ƣ�����ϸϸ������Ц�����������˲��˵á���
��˵�����ָ��˸��������䣬���������ϣ����Ǵ�Ѫ�����ᴥ�˴�����ת�����ո������£��������µ�һ��ͷ�����������һֻ�ְ��������㶯�������˵��Ƿ�����˫������������Ŀ����٧һ�ھ�Ǻס�������ѵ�һ���ĺ������������������ͥ���ڵģ������š���
�����ջ��֣�һֻ���ֹ�������٧��������������������æס���ְ��£����ŷ������֣�Ц�����������֣���ͬˡ֮��ʶ��ã��������Ǿ���ʱ�����հѱ��Ի�������ͬ�Σ�����ͬ�ޣ�ˡ֮��ȻҲ��ͬ�Һá���
��Ԫ����Ц�IJ��У�Ҳ�����к����ƣ�˳��ȡЦ���ŵ���
�������˵����У�����Ҳ��ͬ��á���
���ݵ��˾ƣ����������������ߣ�����������վ�ţ�Ҳ���°ɡ���
�����������£�������������������ͬϯ��������߿������������������Ҳ����Щ���ʶ�Ҳ������ϯ��ȴ�Dz���˵�����������ϸ��������˾����������ԣ���һ��̸���Ȼ��������뿴����˵������ʱҲ��Ц����������ȴֻ����һЦ����٧̧�۶�������ͻȻ����ǰ�մ�Ӧ�Ľ����������������ö����øɾ�������
��ƣ��q�����ˣ�ɢϯ������ƣ��qȥ��ɽ�ͷ�Ҷ��˳���ƣ��q��������
�����ͷ��������ǰ�������������㣬����ȥȴ��˵�㲡�ˡ���
��٧ʵ���˯������˯��һ�����ǣ�����������Щ������ֻ�õ������Dz��˼��ա���
�ڡ�12����
ʮ�£����������������أ������������ɽ������¤ɽ��������ʮ�պﺯ��������Dz������ﺯ������ƽ��ӭ��֮��������������
��٧�������У���������ͬ�ٹ����������������£�ʱ����ҹ�����е���ţ�͵ƣ��谵���ٹ���������������������Ƽ�����������٧���ɺ�Щ����
��٧����Ⱦ�˷纮��һ·���о���Ϊ�Ϳ࣬���ڽ��պ���Щ����٧����
�����������ģ�������
�����Ƶ�����������Ϣ����
��٧��������DZȥ��̽��������ͤ�������������²ξ����壬������������ɽ�ϣ���ɽ��ʮ���������Ӫ��ֻ��ǧ�ˣ�����·�������������ء���
�����Ʋ�ͷ�ʵ���������˿�֪��������
������������������Щ���������ڳ�����˵�������������ذ�������
��٧������������Ҳ����һ��
�������ʵ���������ڱ�Ϊ��ɽ��������Ҫ��������ˮ���裬���ն��أ�һ���˳�ꪶ������ɵְ����۱������������������ǿ���ʲô�Ʋߣ���
�����������������£��ƿ����ǡ����������Ƶ���������˵Ц��������ֻ��һ������ֱȡ��ƽ����Ӷ�����
�ٹ�������������˵�IJ����������Ƶ�������������·����ͤ����ɽ���ϰ������ǣ��˶�����Ϊ����ƽ���ʺ�������ֻ�����Ƿ��ؼᱸ����ͭ�Dz��ɹ�����֪�������ؽ���˭����
�����Ƶ��������źϡ���
�ٹ������������ǣ��źϴ����������ܲ�֪��ȴһ���ϵ����ѡ���
�����ƹ���������ź��ǣ���
�ٹ����������ź��������Ѷ��ӣ�͢��֮�£�ˡ֮������������������ػ��ϵá���
������ٷ����������µۣ�����ʱΪ����ʷ����Ȼ�ڳ��ô�����٣�Ϊ���ٵ�ͥ���������ٺ����ᄀ�������ţ��ź�ʱ�������ݣ�Ϊ�������������Ӹ���λ��������լۡ���������ֺš����ҡ��������źϻس���ȴ��֪�����ź�δ�ܡ�
��٧�����˴�Ҳ�������ף�������ȴ���ϵã��źϴ��ˁ�����㡣������丸����ʷ֮��ȣ��ز���������Ϊ�������ң�ֻ�����ܺ�����²�����Ϊ֮�����˿���Ȱ������
������æ����������ˡ֮Ϊ��������һ�ˡ���
�ٹ���������Ȱ���źϣ����ǿ�ֱ��ȡ�����ǹ���ƽ�أ�����ʧ�أ���ͤҲ�������أ�����������˱ض���ҹ����ƽ���ڳ����������س��������Կ��ƹ����������С·��֮���Կ�ȫʤ����������������ֻ�����·��Χ�ϣ����Ա���֮������ͤ�����ǿ��������˲������������£��ض���ս�Խ�����
�������ӵ�����������ȡ��ͤ�����ǻ���һ��Ӳ�̣������ǵ������ǣ�����һ��һ�䣬ֱ����ƽ�ر���̽��ȡ��������ֱ��Ӷ������������������档��
�����Ƶ�����ˡ֮�ɷ�������һ�ߣ���
��٧���������¾�����Ϊ�����������Ƶ�������٧�������̣���
��٧���������ձ�ȥ����
������æ����������������ʿ������������Ӫ�ʣ���٧����ι���������ʸ��¡�
���ݿ����Ҵ�ææ�����ϵ�������������ȥ����
��٧��������������ȥһ�ˡ���
���ݵ�����������ȥ����
��٧�����£���ϵ�´���������ȥ���գ�������Ӫ�С���
���ݵ�������ͬ��һ��ȥ����
��٧Ц��������Ҳû˵ȥ��Ҫ��ô�����ҿ�û��Ȥ���Լ��Դ�����������ģ�ֻ��Ϊ���б䣬��ͬ���ź���Щ�ɽ����������������°����������һʱ���ҽ�����Σ���������С�����˵�������ҿ�����ĺܣ���Ҫ��ȥð���գ��Թ�������һ�������
����������Щִ�Ų�������������٧��Щ��ϲ������������Ц����
����ģ������������������������㣬��������û�գ����һ��������㡣��
˵�ſ첽������ȥ��������ʿǣ�����������˲���ʻ��Ӫ�š�
�������dz��µ������⣬����ʿ�����˳��ţ�ʮ����ӵ������������ͬ�������о�ʿһ�������������ˣ�Ѻ�ű�ȥ���źϣ���٧ƽ����δ�ܹ����ִ��������¿�Ц��
�ź�����ϯǰ�������ھ��ж��꣬����ȥ������ʱһ����������һ���������ף����絶�̸��䣬�����з���֮�ƣ���٧����������Щ�ϲ���������ʿ����������һ��������������ˣ�����ϵã�������������������Ц��������������δ�������������д���ѽ����
�źϷ������������������ҲһЦ��ʾ���ʿ�ɰ���ֱ�����������˵ˡ֮�������������£�û�뵽��Ȼ���棬����ˡ֮��������������Ҫ���������ģ�����
��˵��ֱ�ӣ���٧Ҳֻ��Ц����������˵���������ز��š���
�ź�ҡͷ�������������ţ���ͬˡ֮�оɿ�������֮��ɺ��л�˵����
��٧���ۣ��ź������;�������ϯ��������Ȱ�ƣ���٧�������ź�ͻȻ����
������Ҿ������������������Ҿ�Ϊ�����������ҵ�������Ϊ������νʿ�ڲ����Բ��㣬�����ӳ�������Ҳ�������������������˶����������ǣ�ˡ֮��֪��������ε�������
��٧���˶٣�����ҡͷ��������֪����
�źϵ������������������գ�������Ϊ�����¶��٣������ȵ�ʥ������ʹ�´ʣ��Ծ�����Ǭ����Ź�Ϊ�������գ����������������亡�ǣ���������ȥ�����ݡ���
��٧����˵���������������������ݲ�֪��Ҳ�ܲµó�������������˵����
�źϵ���������Ϊ���ۣ����踺�أ���ϧ���������Ķ��������ټ������������Խᣬ����������������Ϊ��������Ϊ������Ψ�������ɣ�һ�����ǣ������������������壬�罭��֮ˮ��ϴ��������Ȼ����������ղ�Ϊ����Ⱦ����
��٧���ó�Ĭ�����ε���������������˵ʲô����
�źϵ�����ˡ֮��Ϊ�������Ʊ��������ʿ���ҿ��������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