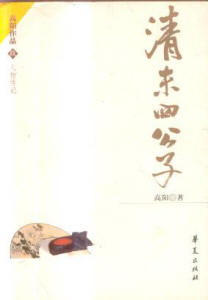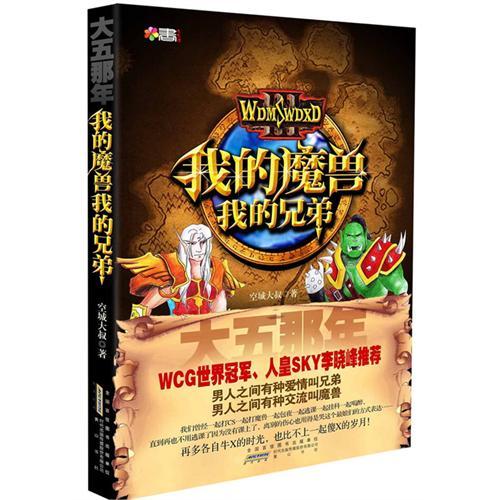清末那几年:一幕未散场的潜伏传奇-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样,时刻关注着朝廷的一举一动。哪个出京的官吏勘核火牌时,我们总是问这问那,拐弯抹角地套些个话儿出来;又怕问多了讨人嫌,左右好是为难。在馆驿当差,身儿要弯,腿儿要软,眉目要谄,步儿要绵,总之,规矩多着呢。还有一大忌讳,就是多舌。这一套功夫,林驿丞最是拿手,照他做就是了。这一日,林驿丞来找我,说是一枝梅下葬,要我陪着到坟头烧纸化币。这一枝梅是通州城数一数二的花娘,柳眉杏眼,玉齿朱唇,馋得那些风流后生镇日里围着她团团转。未想年初她得了一场痨病,才半年,就香消玉殒了。我不似林驿丞,他是风月场上的急先锋,我便推东说西不愿去,偏巧,张目过来凑趣,我就坡下驴道:“你与张大哥一道去岂不更好!”张目闻听是给死人下葬,正想收些死人的泪,就畅快答应了。据说,死人将死之时,都要流泪,将这些泪水集起来,滴在常人的眼里,不仅目明,而且还能看见鬼魂。林驿丞跟张目一同去了,临走,林驿丞点着我的鼻子道:“你呀,你呀——”半天他也没说出一句囫囵话儿,戴上他那顶一把抓的毡帽愤愤离去。张目冲我扮个鬼脸,也相跟着去了。我知道林驿丞不满于我,我也豁出去了,堂堂一个男儿,倘站不稳,富贵在前,威武在后,恐怕只有随波逐流了。回身恰见三娘,她问我:“张目随林驿丞有何公干?”我没好颜色道:“给一个妓女送殡去了。”
四
林驿丞说:
一枝梅死了,送殡者寥寥无几,只有她的几个妓馆的姐妹送路。想当年,她家门口也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两相比照,让我不免唏嘘,世上有情有义的人实在屈指可数。
一枝梅十三岁上破瓜,多少公子哥爱她爱得紧;刚值二九年纪,便呜呼哀哉了;埋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拖到乱葬岗子来。薄木棺材一具,还是我舍的。一枝梅生作万人妻,死是无夫鬼,想这世道着实是不公平。我对着一枝梅的棺木说:“再来投胎,你投个猪马牛羊都行,就是不要再到人间蹚这道浑水。”落葬时,一枝梅妓馆里的那几个姐妹抱成一团,挥泪不止,八成她们的归宿也是一样吧,连带着我也伤心了好一阵子。
张目问我:“驿丞何以如此哀伤,敢不是你与一枝梅有些交情?”我说:“交情倒谈不上,只是天性多愁善感而已。”张目淡然道:“那又何必。”我喟然长叹道:“人生无常,此话不假。”张目寻思我是烦恼自己将来坟前无人拜扫,眼睛有一对,儿女却无一个,故此劝道“儿女总会有的,或许命里来得迟些也未见得。”他哪里知道,我愁的则是另一码子事,听说光绪帝新近招一个南海康圣人在左右闹维新。维新条款中就有一项,要裁撤驿站,开通火车,怕是要不了多久,我等就得扒下这身官衣,擓个荆筐沿街要着吃了。张目他们至今还蒙在鼓里,浑然不知呢。
不过,我又听说西佛爷对光绪帝这么瞎折腾很是冷淡。有一回,光绪帝要把康圣人引荐给西佛爷,西佛爷却说“一个黄脸汉子,见不见的,不当紧”,等于给了光绪帝一个蹬心脚。上边打火镰,下头准火苗子三千丈,打文良老爷一没影儿,我的窗户纸就总有窟窿,糊上,也不管用,一看就是用小拇指头蘸唾沫捅的。我知道在馆驿里,既有西佛爷的人,也有光绪帝的人,也许还有什么亲王贝子的心腹也说不定,哪一个都大有来头。有时候我真想推个车上街卖豆腐去,常言不是说“若要富,牵水磨”吗?只要离开这些个是非就好。
回到驿馆,尚未换衣裳,李耳就一迭声地喊着我的名字追来。怕是又有什么难缠的事,本想推个干净,好清净清净,李耳偏不识趣,揪住我不撒手:“听说了没,光绪帝被老妖婆幽禁起来了!”一句话,像是定海神针,镇得我挪不开步子,赶紧问:“这话怎么说来?”李耳道:“说是谭嗣同鼓动袁项城起兵,围了老妖婆住的颐和园,逼她施行新政……”我嘘了一声,提醒他别一口一个老妖婆,小心隔墙有耳。他接着说:“结果,消息泄露,西佛爷先下手为强了。”我说:“是荣禄跟西佛爷透的信吧,他不是一直反维新吗?”李耳说:“有人猜测说,可能是该死的袁项城告的密。”见李耳急三火四的架势,我心里冷笑道:这些家伙都该杀!李耳痛心疾首道:“现在,康有为跑了,梁启超躲了,谭嗣同又被关了,完了,这下子什么指望都没有了。”我假意道:“静观其变吧,也许还有转机,可别太伤了精神。”李耳这么一来,竟现了原形,露出了形迹,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光绪帝的人。挺伶俐的一个人,却错认了主子,跟随光绪帝这样的窝囊废跑,难成正果也是必然,活该他倒霉。
晚晌,我与祝氏对饮,叫景儿坐在横头,又传杯又递盏。祝氏问我:“有何喜事,令你这般开怀?”我说:“我今儿个揭开一个天大的谜。”祝氏嗔怪道:“一把年纪的人了,还有闲心拆字猜枚,真是个不老成。”我只是笑,不便与她说通。
我想对她说:若是让我将所有的谜团解开,叫我拿一天的大顶我也情愿。看天色晚了,打发景儿进房睡下。祝氏又给我斟了一杯酒,我趁接杯时捏住她十指尖尖的小手,憨脸皮厚地说:“我饮半杯,你饮后半杯,如何?”祝氏偷眼瞟我一瞟,笑道:“美得你。”她这娇嗔模样,最是让我痴。我被迷了一样,一把搂住她,忙来亲嘴。祝氏恐人撞见,抵死不从:“叫景儿看了怎么是好。”我说:“她早在云里雾里了。”祝氏嘴一撅:“那也不行。”说不行,却又做出千般媚人的光景。我知道她最怕的就是咯吱她胳肢窝,一咯吱,她就乐不可支,滚作一团,任什么都肯答应。唯独共进绣花衾一事,即便砍了她的头,也是没用,她刚烈着呢。满通州城都传我与祝氏如何如何了,其实,冤杀我了。我确是意美情浓,盼着与她一处同眠,可祝氏就是不允啊,总说除非明媒正娶。我一个脑瓜子别在裤腰带上的人,真娶了她家去,难不成叫她第二次当寡妇吗?几次想把肺腑实话说知与她,话到嘴边,又都咽了。饮至更深人静,我酒已八九,祝氏安置我睡下,临行再三叮咛:“天凉,起夜一定要穿上棉袄,当心冻着。”祝氏别去,我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
我半生周游四方,算是知道了天高地厚,一辈子只觉得主义和女人是好的,其余不过污泥浊水而已;一帮子国家懒民,民间蛀虫,色中饿鬼,财上罗刹。为那主义和女人丢了性命,我也不屈,只可惜,二者不可兼顾。主义要的是刚强,女人要的是温存,见了,身子就酥了半边。景儿催过我好几回:“你就娶了祝姨吧,多秀气的一个人啊,月儿见了都闭,花儿见了都羞。”我何尝不想,祝氏实实是个知音识趣的娘子,又有十二分的颜色,想起她来心里就热煎煎地发烫。可是,心猿意马时,一瞅见景儿我便凉了半截子。我若一门心思莺恣蝶采,怕是对不住景儿他爹,景儿他爹说过的话时时记在我脑子里,一刻不敢忘。我只有把祝氏当做那橄榄,咂摸咂摸它的滋味……次早,我奔驿馆,头还是昏昏的。
早有信差堵在门外,一照面,信差就申斥我一顿,说等了我半天,要是耽误了公事,即便有十个脑袋也不够我掉的。我赶紧赔着笑脸,求他宽恕我这一遭。信差消了气,才宣读步军统领衙门的密令,责成各个通商口岸和铁路驿站,搜查康梁及其余党。我恭恭敬敬地磕过头,将信差送到客房歇息。转回身来,我叫过李耳:“搜查康梁及其余党的差使就交由你来办。”李耳脸色煞白,要明了他是怎么想的,只有问他自己才知道。王品倒像没长眼眉一样,跑来对我说:“驿丞,这么担沉重的差使,李耳一人怎么担当得了,让我从旁协助吧。”我淡淡地说:“你另有交代,放心,咱们都闲不下来了。”果然,打那天起,西佛爷身边的人一拨一拨地从我们驿馆经过,一色都是顶深盔、披铁铠的健锐营兵,有的还佩了洋枪。我们几个迎来送往,忙得脚后跟都朝前了。造化得很,几天下来,居然没出什么差错。很快就有消息传来,说康圣人的弟弟康广仁被逮了,四川刘光第自首了,还有个叫杨泽秀的小子竟跑到颐和园去责问西佛爷为何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这不是自家送上门去吗,那还有个好?没三五天,我又听说,谭嗣同、康广仁几个都在菜市口问了斩,一场大乱子就这么平息了。这让我很是失望,我恨不得乱得地覆天翻,让大清国彻底完蛋才是称心。更不称心的当是李耳了,他这一程子听戏听得更起劲了,白天晚上都去。我知道他是心烦,就嘱咐王品多陪陪他,我怕指不定哪一天,他便突然消失不见了。以前,这档子事发生多了,常见,也没谁去深究,太深究了反而容易招来麻烦。
累了一个够,我才得空家去,好些日子没跟景儿说说话儿了。院里的秋千踏板坏了,说好要给她修的,也一直没曾着手,她少不了要怪我了。这小妮子若耍起小性来,还是挺厉害的,动不动就不吃饭,闹绝食,也是我平时太娇惯她了,我也只有千赔罪万赔罪。还有祝氏,也是几日未见了,她手里就好似有一根牵着我的绳,引得我要东便东,要西便西。
进得门来,祝氏劈头就问:“哎哟喂,请问这位爷找谁来?”我心下暗笑,知她怪我几天都不着家,口中又不好说出,我只是嘿嘿地笑。祝氏道:“想那朝中如此昏败,而地方上还有你这班人勤勉至此,真是稀奇。”我说:“一个妇道人家,奢谈什么军国大事!”祝氏恼了,拎起我衣领往外便撵:“这些个饭菜,你不必吃了,因也是妇道人家做的。”我只好求她:“我饿急了,央你放放手,我明日买汗巾送你。”祝氏道:“哪个稀罕你的汗巾。”景儿也替我说情:“叫他吃吧,吃了好去给我修秋千呢。”我又喜又恼,喜的是景儿不让我饿肚子,恼的是她让我吃饭的目的却是给她打小工。还是景儿有面子,祝氏这才与我暖起酒来。景儿跟我淘气了一阵子,累了,便睡下了。祝氏跟我扯起闲话来:“听说你们驿站有个顺口溜?”我装傻道:“我怎不知道,你说来。”她说:“张目的眼,三娘的腿,李耳的耳,王品的嘴。”我说:“倒也合辙合理。”祝氏又说:“还有一句我没说。”我说:“你且讲来。”祝氏扭捏片刻,才言道:“羞人答答的,我不说。”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在驿馆,言来语去我清楚着呢;睡觉都睁着一只眼,什么都瞒不过我,那句话无非就是“驿丞的屌”。我非但不为他们背后这么说而火大,反而心中暗喜。我不稀罕什么好名声,好名声当不了饭吃,有这样一个名号反而给我带来些实惠。我逗祝氏:“你想见识见识他们说我的那个东西吗?”祝氏投了一个媚眼:“呸,没个正经。”她虽是个寡妇,却有着一副千金的骨架,素臂,瘦腰,犹如没采摘过的青杏一般。我情难自禁地过去携她的手,一字儿坐在床沿上;她甩开我,退了退身子。唉,她频送秋波可以,我一展身手却不行,哪里说理去?我对她说:“可怜我苦等了这一年多……”祝氏道:“这怨得我吗?”一看她满脸的幽怨,我也不敢再与她争竞,依主宾端坐下来,宽慰她道:“怨我怨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