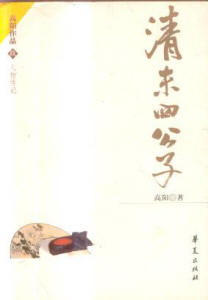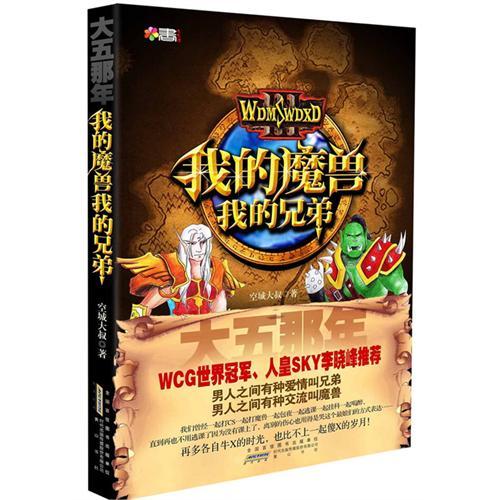清末那几年:一幕未散场的潜伏传奇-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驿丞说:“我就想把旧国家毁了它,戳起一个新共和来。”李耳赶紧说:“这不也正是皇上立志维新的目标所在吗?”林驿丞问他一句:“你那个皇上能赞成共和吗?能脱掉龙袍让人们轮流执政吗?恐怕不能吧!”
一句话,把李耳问得哑口无言。我万不曾想到,林驿丞的脑袋瓜子里边还有这么不老少的干货,我以为他只有一肚子的嫖经呢。从此,我对他多了几分敬重,他再说什么我都留心听,记在心里。三娘虽然嘴上说他“你这是一派胡言”,其实心里也觉得他讲得颇有见地,自然也开始对他另眼看待。“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正经起来,倒还有几分英气。”枕席之上,三娘对我说。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春去秋来,转眼数月过去了,可是,杀静怡的元凶还没有查出来。三娘镇日郁闷,天天闷坐内室,一言不发,我要碰她更是不行。我即便是个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难免寂寞。闲暇时,我便常常上街散闷,以解别扭。也是合该出事,那天,走过一家青楼,有人打二楼的窗上丢一颗枣子下来,偏好砸在我头上,见一美人用纨扇遮着脸儿冲我嘻嘻地笑,我被她的体态风流吸引,竟看呆了。她瞅我痴痴的样儿赶紧闭了窗,躲开了。这么一来,我那嘲风弄月的襟怀、沾花惹草的心性一下子又被撩拨起来,径直上了楼。美人三言两语,稍施狐媚之术,我就将三娘抛在脑后,不免上了圈套。如此连续三天,天天偷着与她宽衣解带。三娘貌似性格粗犷,其实是个心细的娘们儿,见我总上街溜达,脸上又有春风形景,未免有些疑心:“你近日忙碌什么,总见不到你的影儿?”听她一问,我不觉吃了一惊,赶紧满面堆欢,编了些故事骗她。我若是就此罢手,也就好了,偏一颗心只想着美貌佳人,转日又去了。阳台再赴,情不能已,谁料正在得趣,门扇被踹开,三娘闯了进来——青楼砸了不说,还把美貌佳人的嘴巴打了几掌,登时双腮肿起老高,老鸨跟茶壶也不知躲哪里去了。三娘解了气,便揪着我的耳朵回驿馆,一路上人们都围着看,拿我当西洋景了。我求她撒手,她竟揪得更狠了,只好忍了,待回房中再作道理。这时候,美貌佳人湘裙下的金莲,鸳袖内的玉笋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心里想得只是三娘会如何开销我。
进了屋,三娘往椅上一靠,长出一口气:“说吧,你跟那个狐媚子是怎么勾搭上的,勾搭了多久,睡了几回,睡的时候又说了多少败坏我的话,一一道来。”叫她这么一通嗔斥,我早吓得真魂出窍,两条腿没了主胫骨,一软,跌坐在地。我知道三娘不是个脾气好的,真发作起来,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故而一句也不敢申辩,只垂头坐在那里自悲自叹,认倒霉。
忽然窗外有窸窸窣窣的动静,想必是有人听窗根。
“是谁?”三娘问。
“是我们几个。”李耳跟王品嘻嘻笑着走了进来。
我简直羞愧得抬不起头来,赶紧坐起来。三娘见他们来了,口气马上变了,变得心平气和:“你要想讨一房小,不妨直说,我绝不拦你,千不该万不该,你却去偷。偷个书香小姐倒也罢了,偏去偷窑子里的妖狐,真要染上一身的病,你说怎么办?”这一番通情达理的话,叫李耳和王品听得连连点头,都冲着三娘挑大拇哥,敬佩不已。只我了解三娘,暗自叫苦。“张目家的真够贤惠。”李耳说。
“谁要娶了这样的媳妇,那是造化;你小子算是赶上了,还不知个足,你算是积了八辈子阴德了。”王品也一个劲敲边鼓,不知他是真这么想,还是瞧我的笑话。
不管怎样,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便说:“不待你们说,我也知道这件事我错了,还望娘子见谅,就是再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勾三搭四的了。”三娘体贴地说:“还不赶紧叫各位兄弟落座,戳在那里做什么,你们瞅瞅,他哪里像个当家的!”
“嫂夫人,张目兄素来沉稳,这一回准是被那伙子粉头迷惑了,一时昏了头。”李耳和王品再三替我说情。
三娘豁达地说:“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个个都是吃着盆儿,盯着碗儿,真吃醋还吃得过来?”她这一说,李耳俱都放下心,直冲我叽咕眼儿。三娘的深明大义让我无地自容,后悔不已:似三娘这般知冷着热的媳妇,打着灯笼怕是也难找,再把脚往外伸,着实大不该。三娘又张罗着要给李耳和王品排饭,他二人见风已平浪已静,便不再耽搁,哄然散去。我送他们出去,回过身来想跟三娘道个歉,表明心迹,往后一准与她安心过日子。话未出口,想不到她突然色变,一把将我搡倒在地,又踏上一只脚:“你这个混账东西,竟敢背弃了我,我断不可与你善罢甘休!”
此时间,我是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唯有求饶。
“这桩没脸营生,往后再不敢干了。”
“往后是往后,这一回你说该怎么办?”
“你踹我屁股两脚,消消气也就罢了。”
我怕她又掐又抓,把我的脸伤了,出去不雅观。
“要是这么便宜,你将来仍旧没个改性。”三娘一通掐,屁股蛋子、大腿腋子、小腿肚子,凡是见不得人的地界,都让她掐得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我咬着牙强自忍耐,嘴里咕咕哝哝地念叨着。
三娘问我:“你叨咕什么呢?”
我说:“我认错来着。”
“你给我大声念出来。”
没料到她的耳朵跟李耳一样好使,竟听出我念叨的是什么。我不敢不依,只好说:“我念得是‘天皇皇,地皇皇,灵符一道吐霞光,二十八宿齐天降,六丁六甲众大王,快将妖精来擒去……’。”
三娘说:“好啊,你拿我当妖精了。”少不得又是一阵儿掐。这一次,我实在是耐不住了,疼得叫出来。她怕前后左右听了去,背地里骂她雌老虎、醋葫芦,这才罢了手。
叫三娘收拾了一顿,我再也没脸出门了,出去还指不定有多少难听的话往耳朵里头灌呢。我好歹也是个汉子,硬让一个细皮嫩肉、柳腰小脚的娘们儿给辖制了,还怎么出去混事?常言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三娘倒好,不但打了,还罚我一天不让动筷,饿上三顿,上炕也得睡在床脚上,蜷个身子。她翻个身,就顺势踢我一脚。我转天起来,腰酸腿疼脚脖子抽筋,一伸懒腰,骨头节都嘎巴嘎巴响。冷静想一想,真是他娘的不值,鸡巴就舒坦了那么一时,却连累得浑身上下都跟着遭殃,没一处不难受的。自此,我就老实了,断了风流的念头。“三娘没再跟你嚼会子牙吗?”再见我,李耳和王品问。“他敢。”
“想不到三娘貌似强梁,其实也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寻常女流。”他们说。我心想,外强中干的不是她,而是我。不过,我嘴上还是说:“她还操持着要给我讨几房小妾,我没答应;上青楼也就是随便玩玩,当不得真。”屈心不屈心暂不去管它,先说出去捞回一点面子再说。李耳和王品闻之个个羡慕不已,真拿我当掀天拔地、搅海翻江的英雄好汉一般看待了。唯有林驿丞不吭一声,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连头都不抬。想听听他的高见,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了句:“大伯子不当问兄弟媳妇的事。”
“静怡师父那事有头绪了没?”林驿丞问我。
“显见不是我们驿馆里的人所为。”我说。
“那么是谁呢?我要知道的是这个。”
我说:“三娘查了,静怡师父在通州城里没什么仇家,跟妇道们也相交甚好。她们有《“文》点什么事,都让她《“人》给拿主意,比如婚《“书》丧嫁娶,静怡师《“屋》父都推算得阴阳有准,祸福无差,所以均信服她。而且她的庵堂里也没什么贵重财物,图财害命的可能也不太大……”
林驿丞想了一会儿:“照你这么一说,岂不是遇见了一桩无头案,难不成要石沉大海了吗?”我赶紧给他解释:“三娘还不死心,非要追出个水落石出,给静怡师父报仇雪恨不可。”林驿丞和李耳、王品瞅着我,都不言语。“那就拜托你家弟妹了。”林驿丞客气了两句。
我知道,他们仨都急于等着破案的结果,这样一来,该洗刷清白的洗刷了清白,该告慰亡灵的告慰了亡灵。毕竟,他们仨都有嫌疑,不便出头露面。回去跟三娘一学舌,三娘心思又沉重起来,道:“这两日光顾跟你生气着急了,倒把正事忘了。”我赶忙说:“我那些许小事你别总挂在心上。”三娘说要早睡,明日天一亮就去庵堂附近打问打问,想必最近有什么生脸汉子出没,邻居会知道。我们并头躺下,三娘居然没有赶我走。
“你的手怎么这样不老实?”三娘说我。
“咱夫妻有日子没亲近了,不如今夜来个曲尽欢娱吧。”“滚一边儿去,姑奶奶没这个心情,你要找打就言语一声。”我说:“你看你旱了我这么些时日,我再不敢心存二心了,定当与你永结百年之好,你就高高手……”一边说着殷勤话儿,一边动手动脚,撩拨于她。万一她一心软,我得以一夕之欢,就此旧怨也就烟消云散。“你的手别碰我,碰了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问她为什么,料想她是芳心已动,怕是就要绷不住劲儿了。再费些工夫,指定叫她忘掉前嫌,天晴雨收,哪个女人能是铁石心肠?我想得倒是好,谁知三娘却突然翻脸了,将我的手腕一掰,嘎巴一下子,疼得我眼冒金星,冷汗加身。“你那摸过狐媚子的手,脏。别往我身上搁!”三娘说。“知道了。”
“贱骨头,不给你点厉害,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这下子知道了,马王爷的眼左右各一只,天灵盖上还长着一只。”我哪敢再闯事生非,只有唯唯拜受。
这时候,谯楼已敲三鼓,我也只好乖乖钻进被窝,准备安生睡上一觉,心里虽然不免冷落孤凄,却也不敢有所表示。
“去,你给我躺炕脚子去。”
我这一鼓糗,倒鼓糗出毛病来。三娘烦了,坐起来,揪着我的耳朵挪到炕脚。我气得心中火发,口内生烟,怎奈又斗不过她,本事不济,只能甘拜下风,一宵晚景不题。再醒,已是晌午,三娘早已不见了踪影。我走出门来,发现是个阴天,冷风阵阵,细雨蒙蒙地飘将下来。老妈子告诉我,夫人出去也没捎一把伞,非挨淋了不可。我思忖,立功赎罪的机会来了,立马拎起一把油纸伞,就奔尼姑庵而去。老天爷仿佛跟我故意作对,我一出去,蒙蒙细雨立马变得雨骤风狂,树叶子哗哗地都刮下来了。老远就瞧见三娘正立在一家当铺门口背雨,周身上下都打湿了。我赶紧将她拽到伞下,成心让自己淋半截儿,而叫她淋不着一点。我问她:“打问出个结果没?”她说:“家说去。”听她的意思,料是有些成效。快到驿馆,恰巧雨住云开,三娘见我已跟从水里捞的一样,不免见怜,便说:“你真是榆木脑袋,要接我,怎不多带上一把伞?”我要的不正是这个效果吗?便作势说:“怕你淋病了,一急,就顾不得了。”进屋,三娘找出一件月白色紧身小褂,伺候着我换上,我将她推入内室:“娘子先去把湿衣裳脱了,看冻着。”三娘瞅我这等解意,不好推辞,只巧语说了一声:“你暂喝一杯热茶,可不许偷看我换衣裳……”
十一
三娘说:
越不让他偷瞧,他一准非偷瞧不可,男人的天性使然,也是没有办法。换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