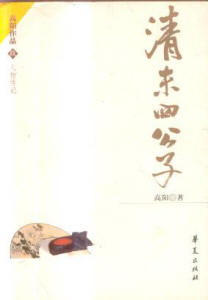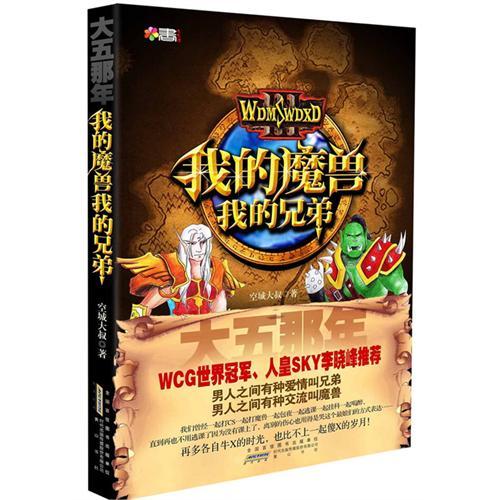清末那几年:一幕未散场的潜伏传奇-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清哪个人是谁的耳目很难,至今我也不知道张目和三娘的来历,可是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他俩的儿子。我给他起名叫做渭仁,三娘没说什么,反倒是张目斟酌再三,迟疑不定。幸好林驿丞也说这个名字使得,张目才勉强同意。他家的小少爷也着实可人,得暇我便抱着孩子不撒手。王品这厮还惦记着拿糖葫芦将孩子勾走,随他玩去;我干脆叫卖糖葫芦的老翁陪伴左右,小少爷什么时候想吃,就奉上一枝。久了,孩子直闹胃酸,却也与我有了依依光景。自此,我更是再疼他不过。与他在一起戏耍,我所有烦愁都一扫而光,说不尽的舒心畅快;说是我哄着他,实则是他哄了我。张目说:“我家的儿子倒让你霸了去,哪有这个道理!要是你喜欢,何不娶上一房妻,自家生上一对两双的,安享天伦?”
我嫌他大煞风景,煞风景的事情本来就够多了,什么花间喝道、果园种菜,还有什么苔上铺席、花下晒裤。现在又添了一项:与孩子玩得正好,偏大人出来捣乱。我们这里正斗嘴,林驿丞赶来,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还闹呢,兵部将驿站的烟酒都掐了,往后再来客官拿什么招呼他们?”原来的烟酒都是专门供给的,酒是山西汾,烟则是上好的朝鲜烟丝;怕来有嗜好的贵客上门,私下里少不了还要备下些川黔烟土。待酒足饭饱,伺候他们抽上两口。现在烟酒断了,就等同于掐上了我们的脖颈儿,难怪林驿丞如此气急败坏。看来潞河驿的大限真的到了,当年镇守京东的天下第一驿,眼下巍巍势焰、赫赫威名早已扫地。到这时候我们才心慌起来,丢了差使,就等于丢了一切。林驿丞说:“我晓得你们都识得几个通天的人物字号,不妨上京疏通疏通,只要事成,必重重奖赏。”没一人应承,这买卖也确实不好应承,谁应承了,去找他的东家求情,岂不是不打自招么?他的仇家还不如同苍蝇见血一般,叮上不放,保不齐连小命也一并丢掉了。林驿丞搓着巴掌说:“都出出主意,甭只顾大眼瞪小眼地相面。若是差使丢了,李耳还可以到戏班提提词唔得,王品也可以拢几个猴崽子教教塾班儿;我呢,怕是到街上打把势卖艺都嫌年纪大了。”他脸红脖子粗,一腔的怒气不知往哪里去撒,偏偏张目不识趣,多了一句嘴:“上下你都给打发了去处,我夫妻俩怎么办?”林驿丞没好气地说:“拉个棍儿讨饭去。”三娘不爱听了,嘟噜着脸子道:“咱也用不着他来安置,种种菜,浇浇园,也养得活一家子。”我们还得两下里解劝,目下,枪口一齐对外方是正理,怎能自家窝里先闹将起来?于是,大伙儿又坐下来,议上一议,自然议也是白议。大局已定,任你再放生戒杀、斋僧布施也是晚了,唯有认命了。我们几个揣着手只等着一纸裁撤驿馆的公文发下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公文没等来,却等来了一桩天大的祸事。
驿馆上下,最为裁撤的事徒自忧伤的自然是林驿丞了。他想解闷,到青楼勾栏泡一阵子,揽镜自照,只见老朽枯槁,一脸的晦气;又见那班俏丽佳人个个杏眼含春,青丝云鬓,真不般配;还怕给人家添堵,只好作罢。找了个犄角旮旯闷头喝了几杯,踉踉跄跄地往家走。谁知半途突然身形一闪,一柄冷剑抵住他的胸口,也仗着他机灵,来个就地十八滚,躲开了剑锋。那杀手却是不依不饶,一剑紧似一剑,都照着他的要害地方下手。他想:这下子,我命休矣。仓皇间问了一句:“你是何人,既要伤我性命,也该要我死个明白。”杀手一言不发,只是将剑挥得虎虎生风。林驿丞匆忙之中只能辗转腾挪,一边退,一边乱念迭起:想我林某,历来都是取别人性命的,今日轮到我了,也是报应。巧的是,紧要关头,几个牢里的禁子刚打完茶围出来,撞了个正着,嚷嚷着“锁了他,锁了他”,就举刀兜了过来。杀手见机不妙,撇下林驿丞,一个纵身,钻进旁边的一条夹股道一溜烟儿逃了。饶是他身轻如燕,健步如飞,还是被一刀戳在腰上,受了伤。几个禁子近前一看,是林驿丞,认得;问了问缘由经过,就都走了。林驿丞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冷汗也溻了后脊梁。不说林驿丞一身的血回家如何疗伤,单说我们几个得了信,匆匆赶来探视。虽然利剑没有落在林驿丞的实处,剑刃却也划破他皮肉多处,鲜血淋漓,请了郎中包扎了,景儿在一边吓得直哭,三娘将她牵到别屋去。没等我们问他详情,他倒先问起我们来了:“你们刚才干什么去了,一直没露面,这会儿倒都结帮搭伙地跑来了。”见他乜视的眼神,便知他是疑了我们,赶紧辩道:“我们本来就结帮搭伙饮酒来着,只你一个单单地溜号了。”林驿丞顿觉无话可说,默然无声了。王品嘴巴来得快:“我们还寻思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呢,也没敢留你。”这话更把林驿丞说得光眨巴眼儿,还不得嘴了。
慰问他一番,我们告辞出来,相跟着回到驿馆,都无困意,又整治酒肴,小酌起来。三娘要奶孩子,先走了。大伙儿心情沉重,谁要杀林驿丞?为什么要杀林驿丞?始终是萦绕于心的天大疑问。可是连林驿丞的根基底细尚不清楚,又怎么能知道更多?我们几个只是胡乱猜疑一回,便各自散去。再遇见林驿丞,他却不愿旧事提起;问起来,他也刻意回避。三娘说:“会不会是林驿丞睡了谁的女人,醋海生波,人家打上门来?”王品却说:“断无这种可能。林驿丞爱女人是真,却不随便爱。他嘴上说得热闹,你又何曾见过他与谁真的睡过?”我琢磨一下,确是如此。担心杀手未曾得手,贼心不死,再重蹈覆辙,我便带上腰刀护送林驿丞。恐他发现骂我,就悄悄尾随其后。半个月都平安无事,我才舒口气儿。一日,林驿丞问我:“你总跟我屁股后边做什么,闲的?”我摇头道:“没有啊。”林驿丞说:“你当我是呆子傻子瞎子吗?”我知瞒他不过,就嘿嘿笑了。林驿丞说:“不光我知道你当我的跟屁虫,我还知道你后边跟着的王品,以及王品后边跟着的张目。你们这群小子,哼!”这倒让我吃惊不小,我怎没发现王品和张目他们两个?还是林驿丞老奸巨猾。转过脸来,我再去责问王品,他矢口否认。我气不过:“你唬我,看我怎治罪于你。”一头说,一头将王品摔倒在地,打作一团。恰好三娘遇见了,三两把将我俩扯开。她当我俩是干仗,俏脸儿赤红,几拳几脚就打得我俩哎哟不断,爬地不起。只知她有一双日行千里的铁腿,却不晓得她的拳脚也是如此了得。张目远远瞅见,不禁倒吸一口冷气,白眼倒翻;他恐怕也料想不到自家娘子竟是这般厉害的角色,往后再遇夫妻不悦,早早鸣金收兵的自然都是他了。三娘临走还说:“若再见你们生事,绝不轻饶。”我懊恼道:“我俩取笑玩耍,你怎不问青红皂白,就来动粗?”张目赶紧跑上前来,连连道歉,三娘也知鲁莽了,却不肯认错,偏说:“活该!”
我与王品招打的事,一时成了驿馆的笑谈,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叫我俩好不狼狈。三娘却被奉为盖世英雄,所到之处,无不前呼后拥着人逢迎,小小的差役都老远就给她赔上笑脸来,就连张目也因妻的缘故沾光不少。王品对我说:“当下的人们就是势利。”我叹息道:“谁说不是。”大概张目看出我俩的心思,也觉得对不起我二人,就摆了一桌酒,算是赔罪。席间,三娘又陪我们喝了两杯,心里才略微平复了些。正吃着喝着说笑着,忽有签押房的差人来报:“林驿丞不知去向了。”我说:“他已回家了,才还打过招呼呢。”差人说:“就是因一个妇人带着他家的景儿小姐来找,方知道林驿丞不见了。”我们这才着了慌,出去劝回了祝氏和景儿,便分散寻找。我领了三五个差人沿东大街而下,凡是店铺,无不打问。路过衙门,衙役告知:“见驿丞跑出城去了。”我一阵惊骇,遂带一行人追下去。恰见林驿丞拐着腿走来,气喘吁吁,通身汗湿。相遇了,不免要问个究竟,林驿丞说:“今日出了驿馆,又见有人尾随,他虽乔装改扮,我还是辨出他便是那天的刺客。幸亏我早有防备,腰间藏了双刀。他终究不是我的对手,三四个回合下来,就处在了下风,只好跑了;我就一径追了去,一直追到了城外。”我问:“后来呢?”林驿丞说:“城外杂草丛生,疯长有一人高,躲进去哪里还找得到。”我忧心忡忡道:“看来,这小子不杀了你怕是不会罢手的,你当小心行事。”林驿丞说:“这显然不是个小子,必是个女子无疑。”我问:“你怎知?”林驿丞笑了:“从身形动作上一看便知,我林某什么时候看女人看错过?”我说:“无论男也好,女也罢,反正是来者不善,你万万不可轻敌才是。”林驿丞说:“知道她是个女人,我只会更在意些,你就尽管放心吧。”说话就回到了驿馆,王品、张目他们都在门口翘首等待,见了,呼啦便围了上来。
叫差人给林驿丞家里捎个信,以免挂念。我说:“就省些麻烦吧,干脆将景儿迁入驿馆,随时照管。”大伙儿也觉得这个法儿可行,遂召唤差人即刻到林驿丞家去接景儿。林驿丞似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王品这厮确实比我心思缜密许多,特别嘱咐一句:“把祝氏也一同请来,不然景儿小姐无暇顾及,林驿丞怕是也放心不下。”这句话,显然是说到林驿丞心坎上了,连声称是,一脸欢然。我咬着王品的耳朵说:“你这个马屁精。”王品还冠冕堂皇地说:“我不过是尽属下之责而已。”这时候,有人将王品叫出门去,嘀咕了几句,王品的脸色即刻沉了下来,匆匆走了。我说:“这小子,不定哪个戏班的相好想他了,着人来唤他。”三娘嫌我没正文,笑道:“嚼舌头的东西,总没个好言好语。”过了好一会儿,王品才回来,两眼直勾勾的若有所思的样子。我问他有什么棘手的事,他倚着门框,回了一句:“不关你的事。”我好心反被当做了驴肝肺,只好躲他远远的。
这当儿,祝氏和景儿拎着包袱来了,大伙儿热闹了一场,就送她们回房歇着去了。林驿丞的眼神儿一直追着祝氏跑,显见是欢喜她;她反倒去挽三娘的手,说些孩子的这个那个。三娘先还有点生分,提起自家的孩子立马就亲近多了,两个眼角也耷拉下来,捏成一道缝。只王品各色,跟霜打了一般,蔫。我想当中必有天机,但又不便再问,问了,他也不会告我。转天,我直睡到日头穿窗才起床,只见院中小渭仁与林驿丞家的景儿玩得正得趣,那祝氏和三娘则在远处观望着。平日里从没见过小渭仁这么喜兴过,看来也是个风流种,瞅见红裤红袄就撒欢。但见王品房内一点动静没有,料想还未醒,未免放不下心来,便去敲他的门。见他穿戴整齐,眼圈却黢黑:“难道你一夜都没睡吗?”王品不胜懊恼道:“你若什么都不问,我便请你进屋;你若问这问那,那就立马走人,我烦。”我归齐还是进了屋,自然又不好问他什么,只随便扯些闲篇儿,就告辞出来。
我其实一点儿都不怪王品,谁的肚里都有一两桩说不出口的恼人的事,作为兄弟,能帮上忙最好,帮不上忙也只好躲一边,别再给他添腌臜。当然,好奇心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