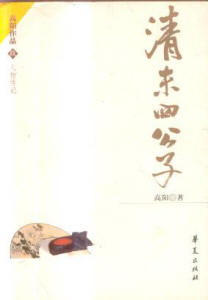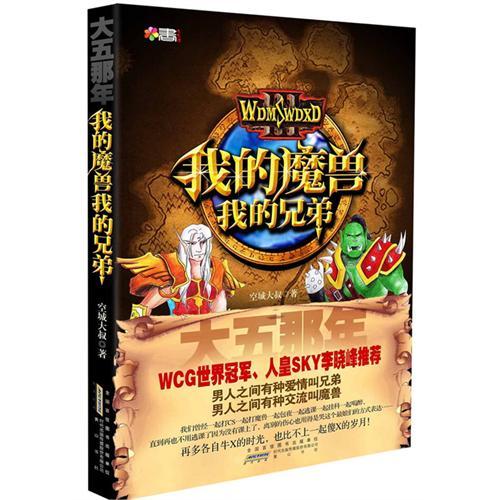清末那几年:一幕未散场的潜伏传奇-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快活煞我了。”他说。
“奴家也是一般。”
“娶你我算是没娶错人。”他又说。
张目还好对付,不好对付的是我家那小少爷,刚会咿咿呀呀,便让我给他说故事讲古。我又不是王品,哪里有那么伶牙俐齿,若不讲,少爷羔子就在我怀里打把势,小嘴撇了又撇,只好随便说点什么哄他:今日说说太平军,明日又讲讲捻军。不想这个小子刚会走,就喜欢舞枪弄棒,屋里家什不知祸害了多少。问他折腾什么,他却说:我要做天王洪秀全第二。张目听了,一个劲儿摇头:“小小年纪,就生就一身的反骨,这可怎么得了。”我几番教导,那少爷羔子也稳当不下来。万般无奈,我只好对张目说:“当家的,改日我再给你生上一个,只一门心思教他读书,一文一武,你老张门下也算是文武双全了。”这么一说,张目才欢喜起来。他倒是急性子,当下就要搂抱在一处,鼓捣那风流情景;拗不过他,只得由他大出大入一番。我现在一副心肠全在孩儿身上,心怀的大志就是将他抚养成人,没病又没灾,哪个是西佛爷,哪个是光绪帝,早忘脖子后边去了。有时候,林驿丞他们总谈这个,谈多了,我就烦:“你们厌不厌,总是这些朝政、朝廷、朝纲,我听得都脑仁疼。”张目喝酒喝到七八分醉时,也会发牢骚:“娘子自打有了这个孩儿,你就变了。”我问他:“是变好了,还是变歹了?”张目说:“说不上好歹,只是你越来越不像你了。”我理一理红软纱裙道:“我给你生儿育女,又守妇道,心无旁骛,难道不是你们老张家的福分么?”张目听了,却还说:“你也只生了一儿,尚未育女,先莫要虚报产量。”
一句话倒让我哭不得笑不得,粉面儿直发烧,只想是张目跟一群没砣的秤杆子混在一处,沉不下来。若是个个都成了家,立了业,又养了自家的孩子,也就心有所属,踏实多了。从此,走东家串西家,着急忙慌地给李耳和王品找媳妇。跑了几家,才知道媒婆子不是那么好当的,不是门不当,就是户不对;门当户对了,八字又不合。费了许多口舌,终算是找了俩合适的;跟李耳、王品一说,他们俩竟然都不买账,脑袋摇得拨浪鼓一般。真真是吃力又不讨好,气得我连连跺脚,发誓再不睬他们。偏他们脸皮儿厚,天天挨至我家门首,一会儿说馋这吃食,求我做给他们;一会儿又要补那褂儿,叫我亮亮手艺。我说:“不应下婚事,我便不管。”怎奈他们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心一软,只好遂了他们的愿,省得他们纠缠不休。再者,我还要奶孩子,他们在跟前,怎么办?
“听说你给李耳、王品两兄弟都说媒来着?”张目回来问我。“别提了,提起来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谁家的小姐,能不能引荐我结识一下?”
“呸,你别也来气我。”
“李耳、王品你都惦记到了,怎忘了林驿丞?”
&文&“他不是有祝氏么。”
&人&张目深深地叹息一声。
&书&我问:“孩儿他爸,你愁个什么?”
&屋&“我愁你太糊涂。”
“这话怎么说?”
“你我俱是因为恩主殁了,没了主心骨,不得不跟寻常百姓一样,做起鱼水夫妻来,人家却与我们不同……”
“他们难道不知道伶仃孤寂吗?”
“他们仍旧身负差使,潜行访察,求的是公侯万代,怎能为儿女之情所误!”
“那你呢?”
“我是个没出息的,被你迷了。”
“你后悔了么?”
“可惜悔之晚矣。”
我起身要走。
“娘子要去哪里?”
“我不想耽误了你。”
“你要走,就耽误了再给我生上一个读书的孩儿了。”
“你且撒手,要我走。”
我挣来挣去,终是没挣脱,不得不并肩上坐。其实我知道张目所言极是,也不再争。
言谈戏谑了一回,方才笑归罗帐。
罗帐欢娱之后,张目披衣坐起,去了一脸的轻佻之容,持重争气地说起朝廷的事。据传,光绪帝病了,忽忽已经数月,怕是将不久人世了。我埋怨他:“你就是抛不掉红尘虚梦,我们当下和和睦睦过脚踏实地的日子,不是很好吗?只怕嫦娥见了,也厌弃她的广寒宫了呢。”张目说:“只是在快活之余,想起恩主当年嘱托,心有不安。”我安慰他道:“恩主生前待我们确实不薄,我们也不曾对他有过二心呀,彼此都扶持。”张目将被儿往上抻了抻,盖住我的腰:“话是这么说,总还是有些忐忑。”此时,风儿吹得窗纸哗啦啦响,我枕在他胸口上,犹豫了犹豫,才说:“我有一事相告,听了,你不兴着恼。”张目笑着说:“瞧你说的,我有那么小气吗?”然而,我还是怕说将出来伤人,故而迟疑不决,半天嘴唇光动弹却发不出声来,倒是张目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有什么话尽管说来,磨蹭什么?”
“相公有所不知,当年你初到驿馆,恩主怕你不老成,曾嘱我不时点化你一二,你的所有举止言谈也都得告知于他。另外,他还特别叮咛我——”“还叮咛什么?”
“……”这让我好生为难。
“你我夫妻难道还有什么信不过的?”
“恩主说,你如有异动……”
“若有异动却将如何,还要把我除去不成?”
“确是这样。”我说道。
“这境遇倒是不曾想到。”
“不愿告你,你知了必然伤心。”
张目仰天长叹一声:“好过的是时光,难过的是劫数。恩主想不到的是他没逃过生死劫,而我却还苟延残喘地活着。”我劝他:“一切尽已过去,切莫再挂在心上了。”张目冷笑道:“我曾将他当父母一般看待,恨不得把他奉上天堂;他则时时算计着将我打入地狱。想想,怎么能不让我毛骨悚然?”我说:“他恐怕也是为大计着想……”张目说:“不过是他们使唤人的一贯伎俩罢了,他也常通过黄老板向我打听你的行踪,一日不漏。你几次独自上山,他们都指派我尾随你,回来报告。”我惊诧道:“他连我都信不过吗?”张目愤愤地说:“依我见,他是谁都信不过的。在他眼里,你我都算不得个人,只是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这下子,轮到我愤然了,怪不得我每次出行,总觉得后面有人盯我的梢,却原来也是恩主的耳目……
九
李耳说:
白天,我跟林驿丞一班人耳闻淫声,目睹邪色,糊糊涂涂凑个趣,镇日嘻嘻哈哈,装作无忧无虑;到晚间,闭上门户,我的弥勒脸即刻化作哭丧脸。最近风闻光绪帝一病不起,老妖婆也不叫御医精心调治;光绪帝身边只有皇后陪着,一个心腹都没有,偏他俩又不是一条心;光绪帝最亲近的珍妃早被老妖婆填井里去了……越想越觉得前景渺茫。假如光绪帝龙驭宾天,我该怎么办?此时间,仿佛周岁孩儿断乳一般教我难受。思来想去,去向无非就两下——要么浪迹天涯,一府一县地信步走去,没个准头;要么就跟张目和三娘一样,一唱一和,相得益彰,总强过独自一人坐在下处倾听窗外风声雨声吧。原以为老妖婆一大把年纪,总不至熬得过时值壮年的光绪帝吧。只要老妖婆一死,随你什么神仙鬼怪皇上都不怕了,谁还敢奈何他?想怎么维新就怎么维新,要如何变革就如何变革。唉,偏偏事不遂愿,归其老妖婆倒命大福大,而光绪帝则少造化。那日,三娘要给我说媒,非是我想在风月场上着脚,也不是不动心,两夫妻在一起暖暖脚也是好的。转念又想,男人立于世上讲究的就是个信义。当初我是起过誓的,要效忠皇上,怎能半途再毁约呢?若那样怎还有脸存活于世上!我李耳平生最看不得的就是背信弃义,今日跟张三战于沙场,明日又去投李四;更恨的是脚踩两只船,左右逢源。听说了,我就咬牙切齿,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一日,我去庙里替皇上烧了一炷香,竟遇见了一张熟面孔。当时烟雾缭绕瞅不清爽,走近了才看出是香铺的房二爷。他家的香堆成了山,却还跑这里来烧香,怪是不怪?更怪的是,房二爷见了我,竟跟不曾相识一般,匆匆离去,连个招呼都不打。也不知他给哪个求神拜佛,疑了一会儿,又猜了一会儿,便把这事忘了;再在铺子门口碰头,也没提起过。房二爷还问我:“老没见了,这一程子够忙?”我亦顺嘴说:“可不,忙得脚丫子都朝前了。”晚上,睡倒在床上,没事做,我不免胡乱猜想。天下像我这样的帝党究竟能有多少?此时此刻,他们又都在做些什么?也像我这般摊手摊脚地躺着无所事事吗?我大概是露出了声色,叫林驿丞看了去,他就常常拉我一道饮酒唱曲;那张目跟王品更是这个晌午邀我下棋,那个晚晌约我听戏。我知道,不过是哄我开心。
他们几个也算得上是我的知己了,却偏不能敞开胸怀,个个藏着掖着,想来都很难受。这两天,驿馆出了一点事,一个雷将东跨院的树劈了,捎带还毁了七八套房;林驿丞报了上去,讨些修缮银子。以往这些许银子根本算不得什么,呈上照准;这一回,催了几次,一拖再拖,总是杳无音信。林驿丞就嘀咕起来,恐怕驿站被裁撤掉,我心思凌乱,也不管顾那些个,只林驿丞一个干着急。他急了就吼我们:“这个驿站要是没了,看你们几个哪里混饭去。”末了,还是他找了十来个泥瓦匠草草将房子搭盖起来。砖头还照旧使过去的那些,工钱也给的少之又少,泥瓦匠都以为被他克扣了,背地里没少骂他。我们去解释,其中一个曾在军中效过力的,说道:“当官的哪有不贪之理,我剿捻军那会儿,我们统领手下只有一千来人,却向朝廷要两千人的饷额,这般景象见得多了。”林驿丞听了,也只有苦笑。见我一耷拉脑袋,林驿丞便说:“别总像科场不中的举子模样,男子汉大丈夫胳膊折了,就该褪在袖中,让人瞅不出来。”我亦觉得在理,就频频点头称是。日后,我便将笑模样粘在脸上,谁见了我都像照了哈哈镜一般,林驿丞却又说我:“你这又忒过了,放自然些就是了。”林驿丞除却喜欢追逐妇人以外,实在可以够得上做我们几个的老大哥。
听说三娘给我们做媒,他举双手赞成,说男大当婚,理当如此;又说娶媳妇就要娶中用的而不能娶中看的,中看的不过就是苗条些、年少些、娇弱些,中用的就妙处多多了。中用的讲究宜肥不宜瘦,宜大不宜小,宜强健不宜娇弱——肥了,生孩子不费劲;大了,提水挑担都来得;强健不至于嫁过来天天抱着药罐子,床上也不怯场。对他的话,我们都只当笑谈,谁娶亲不娶那年轻貌美的?张目娶了三娘,还不是过得挺好?只是驿馆里有两条不成文的规矩,首先的一条就是彼此不随意打探消息,不然我真想问问他们婚后是怎么个快活法儿;另一条规矩则是无论进哪一间房都事先要咳嗽一声,便于通知对方,免得有所不便。我们这一班人原也多少有些个来头,都是哪个王爷、哪个大臣拿帖子送来的,王爷自然是非后党也非帝党的中间派,大臣则俱是清流人物,怕是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只是碍着情面帮个忙。不光我们几个之间相互都挺客气,就是往来的客官也不太为难我们,他们也总得给王爷大臣一点面子。若想弄清哪个人是谁的耳目很难,至今我也不知道张目和三娘的来历,可是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