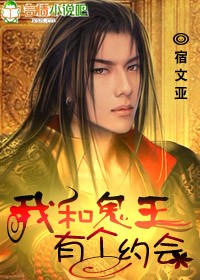我和"卖狗饭的"-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那不久,教皇又约我出去,一见我就咬牙切齿的。我对他说:“你不应该恨我呀,如果不是我阿牧就不会退出,你怎么坐第二把交椅,你现在不是成了名人了吗,见你一面很难呀。”教皇也笑了,说:“辉嫂风采依旧,我这次来只是受梁叔之命来问问你知不知道辉哥的下落?”我很吃惊地问:“难道一辉真的不在梁叔那里?”教皇摇摇头。我说:“会不会是梁叔的障眼法,连你也不知道?”教皇脸色一变,说:“一定不会!”我笑着说:“我想也不会,你忠心耿耿出卖所有朋友去帮他,他应该对你很放心才是。”教皇用恶毒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走了。
在那之后我隔几天就要同梁叔的手下斗智斗力一番,那是因为老秃子总觉得我不老实,感觉被我骗了。我被揍了几顿而已,只留下一点轻微的后遗症,我想老秃子也不会真为难一个穷学生的。
(三十七)思念卖狗饭的
从那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一辉。当一切风波都已平息后,我恢复了自由之身,但我没有再走出校门,我静静在学校里待了半年,看了不计其数的书,以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有时都要问我某某书在什么地方。
我恐惧于一个上街,我极不习惯我的左右少了那个高挑美丽的影子,以前走路我们总不肯规规矩矩地走,我们有时相互依靠有时互相拉扯,我们都很愿意把自己受的地球引力与对方分享,我们不时的迅速跳开闪对方一下……总之所有的可能性被一一示范。而现在,我成了一个走路豪无特点的人,所有人见我走路的样子都会觉得别扭但又说不出为什么。
只有我知道,我抛弃了从前所有的习惯,开始现学走路,所以我走得无比端庄无可挑剔,但是人们一眼就看出我根基不稳,我无可避免地失去了自己的另一半,但我把自己伪装得像正常人一样。
半年中我只到大食堂吃饭,因为只有那里对我们而言是不曾同来过的,我喜欢把自己围在男人堆里,他们吃像千奇百怪,不过总可以让我避免想起那张精致小嘴嚼动食物的样子。
我不敢停足关注新鲜的东西,虽然她不在身边,我却能依照她的语言逻辑事先知道她要说什么话,知道她在说完某句话之后的动作是瞪眼还是撇嘴。没有她的指点我再也找不到美女的身影了,以前只要不按她的指点向左右看去,总能发现美女的,她像一只雷达一样使我提前知道了老奶奶以及丑女们的具体位置,她却那么笨,从来不懂假中混真来一次,还一直自鸣得意……
有时脑袋想事时,腿脚自己会移动,手与肩不自觉摇摆起来,蓦然想起一件趣事,脑袋会突然自己寻找,嘴里说“一辉,你说……”
我有无数次以上的经历,常引路人驻足纳罕。无数次腿脚自己走到以前常去的地方,头脑里便映几幅图来勾引我又去想她。我拿着最扣人心弦的武侠小说去说服身体头脑听我指挥,往往女主人公一出现后它们就起义去想一辉。
看到旧物,我想到以前。
看到新景,我幻想同游。
半年来我看了无数的书想了无数次她,这两件事成了我所有的事情。她在我脑中永远鲜活,无比丰富,凡是我看过的小说,里面都有了她的影子。她时而是女侠时而是女匪时而是都市女郎时而是村姑。看书是为了停止想她,却又是为了想她。
我的书呆子气使我一度消失在了众人里,然后又因为书呆子气而出名,渐成了传奇人物,成了天才与白痴的结合体而被人讨论,略知情的人视我为杨过,深知情的朋友又劝我别再犯傻。
半年之间,我面上就有了刀刻般的沧桑。
我曾上了几回网,唯一的事情就是给她留言,在网上我仿佛是与她面对面坐着,我的言语活泛起来,一堆又一堆的文字组合却一去杳无音信大多成了无人认领的垃圾。
半年中,我也笑,也哭,也快乐,也烦恼,也开玩笑,也发脾气,也知冷热,也觉酸甜,仍有朋友,仍是父母的乖孩子。
但所有的人都说我变了。
过了那最痛的半年,我才恢复了正常。
一辉的身影溶入了我的血液,我不痛了,渐痊愈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再有几个月,我将毕业,一辉将回来,我们将远走高飞。
这个,就是“MGF”计划。
(三十八)失约
大四的时候,我因发表了几篇与年龄不符的所谓成熟文章而小有名气,几家报社答应毕业后录用我。
毕业时一辉仍无音信,我只有等下去。我在这个城市长住下来,焦急地等,每一天醒来似乎都有预感一辉会来找我,但是预感都成为预感而一一过去。
一辉住过的房子已经易主,E薄云天也不知去向。冰河他们彻底从这个城市消失了,所有一切能证明一辉存在过的事物都遗失殆尽,我茫然地四处寻找线索却终是徒劳,我所有的朋友也已忘记了我的过去|Qī|shu|ωang|,有时候连我也在怀疑是否存在过一辉这么一个女孩子。
我修理好了大学时代骑过的单车,顺着一条上坡路蹬去,在这里我和一辉曾重复过《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一个情节,我努力回想当时的情景,一切却似真似幻,我去问当年追求过我的女孩,她却连追过我的事都忘了。我无数次在一辉家楼下徘徊,却看不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人,我冒昧地拜访了新主人,新主人也热情地接待了我,告诉我这里从前只住过一个老人……
我开始真的怀疑一辉的真实性,因为这样一个与我熟识的情人应该留下照片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我手上却一无所有。我开始相信医生关于我的精神分裂的结论。
我开始终日回忆,医生说我得了幻想症,他拒绝一切关于一辉的说法。
这时我终于想到一个可以帮我的人——倪影。
我费尽力气,才曲折地得到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当我胆颤心惊地问她关于一辉的事情后,她爽朗地给了我一个答复:
“你有病呀,连自己女朋友存不存在都不记的了。”
我小心翼翼地承认了自己的确有病后,倪影同情地说:“你的确有一个叫一辉的女朋友,那年过年还在我家里住过几天,高挑个,五官比较精致一身的江湖习气,当时你称她是‘卖狗饭的’。”
我大喜若狂。
倪影又告诉我:“我在本地发现了一个女孩子,长得很像一辉,不过是一头披肩发,动作言谈也很斯文。”
我知道那不是一辉,但我还是很高兴知道了一辉确实存在。
从一开始我根本就不应该怀疑自己,我不是一个脆弱的人。我重树了信心,渐渐回忆了许多我和一辉的往事。
一年时间,我差点被这个女人弄疯!
为什么会那么爱她在我现在看来已成问号,我的神经已经不大肯支持我的逻辑了,但我知道我现在仍然爱她,爱得要命,甚至已经疯了。
我回忆起了“MGF”计划,这是我差点崩溃的关键。这个为期一年的计划已经超时了,那么她为什么没来找我?
她失约了。
(三十九)寻找一辉
我总希望在茫茫人海中会突然发现一辉,我开始用各种有暗示性的笔名发表文章,不久就成了著名的颓废作家,人们说我骨子里有一种颓废加浪漫的气息
我曾在街上几次看到老秃子的林肯呼啸而过,我有一次甚至想去问老秃子一辉的下落,而这个城市所有的人都不记得我了,包括老秃子。
有一次我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一个肮脏不堪的小摊上看见了一个高大的男人,他是阿牧。我坐了下来,阿牧看了我一眼,笑着向我走来,我们握了手,他问我:“你把一辉丢了?”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一见我的样子就知道看出来了。我问他是否知道一辉的下落,他说他根本再没有听到关于她的消息。我们坐了下来,我问他是否还在怀疑是梁叔出卖了他,阿牧告诉我,他一开始就知道梁叔并没有出卖他,在他快出狱的几个月前,警方找过他,让他做警方的内线,他没有答应,而这一消息一定被梁叔知道了,所以他暴露了,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他才退出,而梁叔并没有真的想除去他,所以他平静地活了下来。他还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以他的个性是不会放弃一辉的。他会干掉我,因为他真的可以为了一辉不顾一切。我问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他快结婚了。他临与我分手时给了我一个地址,说一辉很可能在那里。他说那是雅典娜的家。
这时已经又过两年,从表面看去我已经和以前一样了。我学会了平静的等待。我去了雅典娜的家乡,那是一个美丽的水乡,盛出像雅典娜一样清秀的女孩子。
我像猎人一样蹲守了三天才见到了回家的雅典娜,她现在透出一股成熟的女人味,在和一个小老板同居。我们很平静地见了面,她请我喝她的家乡茶,平和地谈了一会过去,她知道我在找一辉,但她与一辉也没有接触过,她冷静地帮我分析了半天一辉的去向,然后我们就互道了再见。
雅典娜说一辉很有可能被梁叔捉了回去,因为在那个城市梁叔要找的人是不可能跑掉的。
我又回来了,等了一年,家里开始关心我的婚姻问题,说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让我回去相亲。我拒绝了。
教皇在一次严打中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去监狱看他,他反而比以前高大壮实了很多,头皮青楞楞的,透过栅栏看见了我扭身就走,他说他不认识我。我叫了他一声,他索性转身回来坐下,他平静地说:“你已经见不到一辉了,她当初在这个城市像迷失了方向的小鹿一样没过三个月就被梁叔捉了回去,逼她嫁给一个得力的手下,一辉大喊大叫骂人,撕扯自己的头发,她被囚禁了起来,没过半年就疯了,然后就趁看守他的人睡熟以后冲了出去,第二天在护城河里捞出了她的尸体。”
我望着教皇,教皇也望着我。教皇对我说:“如果当年你坐我的位子,现在应该是我来看你。梁叔根本不信任我,我为他干了那么多事情以后,被捕后仍无法拿出证据告他。”
我说:“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我又补充说,“我是指一辉。”
教皇说:“一辉临发疯前唯一能相信的人也只有我,她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你。”我说:“信呢?”
教皇说:“早丢了,那时的我怎么可能把你们这种小事情放在心上,不过杜鹃看过信的内容,你可以去问她。”
“杜鹃在哪?”
“她也快死了,要找她就要快点。”教皇眼中闪出一丝恶毒,说,“她现在在蓝天夜总会当小姐,现在不叫杜鹃叫白雪。”
我和教皇同时站起,同时厌倦了对方。临走我对他说:“你现在的发型很酷,保持下去吧。”
在蓝天夜总会,我点名要白雪陪坐。杜鹃一身香浓味道头发打曲,她扭着臀部向我走来,看上去一根指头就可以推倒,她已经不是昔日的散打皇后了。
我开门见山地说:“多年以前,你叫杜鹃的时候,因为同一个叫星矢的男孩分手又移请别恋而被一个叫一辉的女孩一脚踢飞,我是她的男朋友,她留了一封信给我,请你告诉我信的内容。”
杜鹃脸上的媚笑烟消云散,她恢复了正常走路姿势坐在我对面,苦笑着说:“是的,我记得她,那时候也只有她一个人可以把我一脚踢飞,我不恨她,而是佩服她。几年前她死了|奇+_+书*_*网|,留下了一封哀婉欲绝的信,为了纪念她,那封信我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