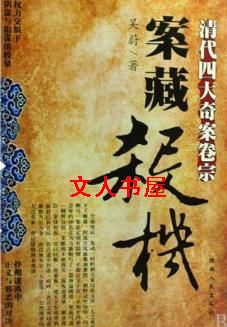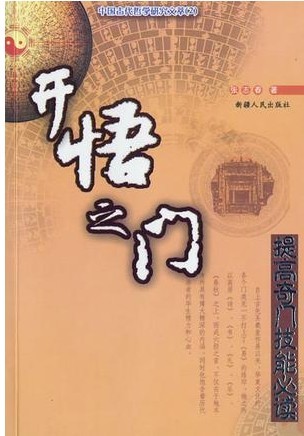案藏玄机-第7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领悟一些带有哲学意味的人生道理。
这是一种兴奋,一种愉悦,一种理性的显现,这是多么大的一股力量呀!他忘了自己是不能动的,他想一跃而起,想再劈出虎虎生风的一掌。但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人的精神更强大的力量,那就是死神的力量。这种无敌力量的先锋就是病魔。它很轻易地就将这个老人撂倒在地,接着就是胸部剧烈地疼痛,死神劈出了一掌,是他过去梦寐以求想学到的一掌,也曾经打出过这样的一掌……
上官杰还是那副无耻的样子,还没等古洛开口,他就矢口否认起来:“我没上车,啥也没干,你们就放了我吧。”
“你没上车?”老张又激动起来。但古洛的问话让他把怒气吞了下去,不过,过了一会儿这怒火就变成了错误。
“我们找到了证人,很漂亮的小姑娘,你很欣赏她,所以她对你印象深刻,还想见见她吗?”
上官杰的脸色又像上次那样变得惨白,汗水又一次流了一脸,还把鼻涕带了出来。他伸出大手擦擦鼻涕,又擦擦汗,一时没有说话。
“说!你是怎么杀害乌伏虎的?”老张大怒,拍着桌子喊道。古洛想制止他,但已经晚了。上官杰抬头看看警察们,眼光中先是惊异,后是困惑,但立刻就亮了一下。这思维轨迹的变化就是在一瞬间完成的。
“我……我凭什么杀他?”他停顿了一下,这是意味深长的停顿,接着又说,“我不认识他。”
“又在说谎。”古洛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说出了这句话。(文*冇*人-冇…书-屋-W-Γ-S-H-U)
“没有。我真不认识他。”
“他并没有要你两只眼睛呀。”古洛说。上官杰低下了头。
“说说你杀他的动机和过程吧。说得要细一些。”古洛从对方的神情中已经窥测到要听到的供词了。
“我没杀他,我杀不了他。他有一身功夫,我打不过,要不也不能丢一只眼睛呀。”
“没有说是用拳脚,你那毒药是做什么的?”老张又发问了。这让古洛很不满。上官杰又沉默了。古洛点上烟,静静地吸着,等着上官杰的抉择。
“可是……”看得出上官杰正在做艰难的挣扎,就连古洛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难下决心,而且下决心的理由让人看到这真是个大千世界,一个无奇不有的人类社会。
“怎么?这么确凿的证据,你也想抵赖?还用告诉你我们的政策吗?”其实,古洛从心里反对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你犯的是死罪,就不会变成活罪,即使你坦白也罢。
“那……”上官杰抬起了头。他的面容改变得是那么剧烈,以致古洛差点儿就认不出他来了。只见他面色灰白,像是从棺材里跳出来的僵尸一般,整个的脸都在抽搐,好像不是他脸一样,眼睛睁得很大,眼白都是混浊的,瞳孔没有焦点,只是形状是向着前方的。
“那……我就说了。你们能对我从宽吗?”
“看你的态度了。”古洛当然不能肯定地答复他。
“好。是我杀了乌伏虎。他是个恶鬼,我的眼睛就是他打瞎的,我能放过他?做梦!我要报仇,你让我残废,我就要你的命……”
“别说废话!说说杀他的经过。”古洛说。
“嗯……”上官杰停顿了一下,“其实,也没啥说的。我出来后,他就一直敲诈我的钱。那天按照约定他又来了,我给了他二百块钱。他说,他想去江城一趟。我看机会来了,就说我正好也要去。他让我给他买票,我就给他买了票……”上官杰看看古洛,突然转了话头,“我想抽烟。”
“给他!”古洛示意胡亮,胡亮就给他一支佳美牌的香烟。上官杰看看烟,说:“云烟,我爱抽。”
他吐出一口青烟,又深深地吸了一口,说:“我留个心眼,给他买了一张十二车的硬座,说没有卧铺了,要不你坐我的吧。这小子倒也不怕苦,说,你坐卧铺吧。就这样我们上了车。我们两个一直在餐车吃饭,都是我花的钱。那天早上,我知道八点来钟就到江城了,就去他的车厢里,和他喝酒,在酒里我掺了药……”
“完了?”古洛问道。
“完了。”
“你知道他死了?”
“肯定死,这药厉害着哩,是慢性的。”
“为什么不早杀他?”
“死在车厢里,我可就危险了。”
“你和他并不坐在一起,他死了和你无关嘛。”
“那一起喝酒要是死了,人一报案,要是再有谁看见我和他一起喝酒,我不就露了。”
“你为什么留下车票?这可是证据呀。”
“我一般都留车票,好记账,过日子的人没有账哪行?再说,我实在没想到你们能找到我。”
“为什么没想到?”
“他一个刑满释放分子,值得啥?死了就像死只苍蝇。”
“嗯,你就是这么看待你们这样的人的?所以说你们是真正的危险分子。好了,你说你留票,可这里面怎么没有回来的票呢?”
“有。你们可能没找到,就在我的屋里,没有错。”
“嗯。我们再去找找。对了,你说你恨乌伏虎,说早就预谋杀他,你都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
上官杰歪着头,用诧异的眼神看看古洛:“你真是个有意思的警察。”
“什么意思?”
“疑心太大。不是我杀了他,我会认吗?”
“倒也是。说说你做了哪些准备吧。”古洛面无表情,但却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
“这个王八蛋!”上官杰愤怒起来,浑身都在打着哆嗦,“我能不杀他吗?我从来也没受过那种气。这小子也是找死,本来出来后,他要是不找我,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可这家伙非来找我,那就是找死。他管我要钱。要钱,钱是什么?是命!是我的命!他要我的命,我就要他死……”
“别说废话!”古洛皱着眉头,打断了上官杰的话。
“是,是。”上官杰谄笑着。这种笑容让古洛不禁疑窦丛生。“这个茅坑里的石头怎么会这么笑?”
“我们说一起去江城,我就把药准备好了。到了车上后,我和他一起吃饭,他妈的,都是老子花的钱,把这家伙弄高兴。最后要下车的那天早上,我特意拿了一瓶杜康酒,跟他喝……”
“说谎!早上谁喝酒?”古洛说。
“没胡说!乌伏虎几乎是一天三顿都喝酒,不过,是好酒他就多喝,坏酒喝得少,奸着哩。一见是杜康,那就没命了。喝完后,我俩一块儿下了车。我说我有我的事,他说分手,不过,以后还要找我。我想,你一个死鬼找我?就这么回事。”
“说完了?”
“完了。”上官杰像是思考的样子,停顿了一会儿才回答说。
“那天挺热吧?”古洛随意问道。
“哪儿呀!下着大雨,可大了。我们俩都没带雨伞,穿上了雨衣……”
“他穿的什么样的雨衣?什么颜色?”
“就是……一般的雨衣,颜色记不住了。”
“他和你一起出了车站吗?”
“没有。一下车,我就赶紧走了,怕他死在我面前。”
“没回头看看?他没跟着你?车站就一个检票口。”
“没有。我们尽量分开走。”
“为什么?”
“不为啥。就是干我们这行人的习惯。”
“你们这行人,哪行人?”古洛盯着上官杰。他知道如果他抓住了要害,上官杰至少会有所反应的。但上官杰很随便地回答道:“就我们这些走黑道的人。也就是蹲过监狱的。”
“这个乌伏虎住在哪里?”
“我……不知道。”上官杰犹豫了一下,说。
“倒新鲜了。干你们这行的,你要杀他,能不知道他住哪儿?你骗谁呀!”
“说!”老张一拍桌子,他又激动了,但这次效果是正面的。上官杰显然害怕了。他抬起头,求援般地看看古洛。
“说!不说对你没好处,说出来对你没坏处。”古洛说。
“这话说得有意思。”上官杰笑了,“他家住在大道街,号数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找到,一个破院子。”
“就他一个人住?”
“不,好像还有一个人。”“如果是同伙,还要小心些呢。”古洛刚一想,胡亮就对老张说:“再找几个人,一起去。”老张还没来得及反应,古洛就说:“没事,咱们三个够了。”
这个街道的名字不知是什么人起的,可以说是古洛见到过的最没道理的名字。这里别说什么大道,就是小道也窄得通过不了一辆比较大的车。公安局的吉普车像个龙钟老人一样,磕磕绊绊、颤颤巍巍地挪动着。司机还把喇叭摁得街道上无人不知来了辆烧汽油的车。
“下去走。”古洛让司机停了车。
“还是坐车舒服。”上官杰说。
“你朋友的家不让呀。”古洛说着,就带头走在前面,这样可以显示出他的英勇无畏。
但五分钟后,他就知道这里根本不需要献出鲜血,更别说生命了。
十三 字中玄机
这是个什么样的房间呀!只有棚户区里才有。房间里只有一张大床和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床上放着一张凉席,这是猜测,因为黑得根本看不清是不是凉席了。桌子上放着没吃完的咸菜和半个馒头,古洛虽然没有仔细看,但可以断定上面长满了绿毛。一个铁炉子,带着一个铁烟囱。屋子里的潮湿和黑暗足以吓跑阳光,就是像佛像前的长明灯一样亮着的日光灯也被房间里的臭气熏得像要昏过去一样。
“臭!”胡亮捂住了鼻口。
“嗯。”古洛指指窗户边或者说炕边的一堆破布。胡亮定睛一看,不由得差点儿叫出来。那是一个人。
一具腐臭的尸体震惊了中原市公安局。不是这里案件少,而是那具没人发现的尸体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在一个大杂院里,几乎没有任何隐私的人类居住地,却没人发现臭气熏天的尸体。而且这具尸体是谁,也无人知晓。他又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就连法医也被难倒了。
中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全面介入了这个案子,他们走访了那个院子和附近的几乎所有居民,但没有人知道那间房子里住的什么人。公安局又找到区房地局,房地局的人说,这里过去是住过人,但后来就不知所踪了。因为这是私人住房,在“文革”中被群众占据,“文革”后,原来的房主人找到政府,要求归还住房,政府就还给了他们。但那个房主是个孤老头子,要回房子只满足了他的精神需求。“我的房子就应该还给我。”他一直这样和我们强调,可真要回房子后,他就驾鹤西归了,房子就空了出来,似乎没人住。
邻居们自然知道这里有人住,但不知道是什么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盲点。乌伏虎和这具尸体就是在这个盲点中生活的,盲点让他们成为人类社会中的影子,直到有一天他们被仇人发现并跟踪。
这时的古洛正在看那半张纸,是在那间房子里发现的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剩下的半张自然还在那个没有找到的笔记本上。这张纸由于在潮湿的空气中生活过,又在老鼠嘴里死里逃生,所以已经破败不堪,被分为两半。古洛将其拼凑起来,上面勉强可以看出有四个竖写的字:良心、工夫。“良心”和“工夫”之间有残缺,“工夫”下面也许还应该有字,但纸已经到了尽头。
“‘良心’、‘工夫’,这是什么意思?”古洛想了想,扔在了桌子上。“也许没什么意思。可是……”没有什么直觉,当时人们还不怎么讲这个词

![[三国]空余青史颂玄机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