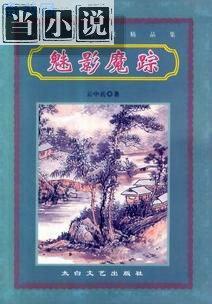萨儿的跟踪-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在害怕。
他害怕是他自作多情,也许她根本不想跟他在一起,更别提共同生活一辈子。
他一向有着数不清的女人,也从来没有得不到的东西,他也一定会得到萨儿。他不允许她拒绝他,他宁愿先下手为强,用强悍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他若有所思,沉默不语,而萨儿也是心事重重。
跟他走?
她走得了吗?
心底有一个声音在说着,她想要抛下“组织”,跟随他到任何地方……
她居然想这么做。
不!她凭什么这么做呢?
到台湾后跟他生活在一起?让他负责照顾她一辈子?
可能吗?
他也许会依承诺捐款,再将此事公诸于世,让她成为媒体宠儿,但当她没有利用价值时,他就会将她抛在一边。她相信他会如此无情,因为他也承认自己是个残忍的人。
她该何去何从呢?她十分肯定的是她并不想离开他,甚至根本离不开他。
两个人都心神不宁、浑浑噩噩地过了一晚。
隔天,依照约定,司机在离开前来叫他们。
奇怪的是,司机与昨天不同,是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
留着络腮胡的司机,结结巴巴道:“昨天那个司机临时有事,无法前来,所以换我来——”他手中拿着金雍宇塞给那个司机的钱,来证明所言不虚。
金雍宇虽觉疑惑,可是因为想赶紧带萨儿回台湾,也只好先上了货柜车再说了。
车子往首都喀布尔开去,起先一切都很顺利,可是,车子渐渐不走大路,专挑偏僻小路走时,萨儿直觉大事不妙。她往窗外望去,大声叫嚷着。“这不是往市区的道路——”
可是为时已晚,车子突然靠边停了下来,车门一打开,萨儿便带着金雍宇准备跳车,不过,在他们还来不及逃离之前,两个凶神恶煞的中东人已将他们团团围住。
由于萨儿对于金雍宇“赞助计划”的不断拖延,所以“组织”再也等不去了。他们决定亲自出面捉拿金雍宇。
而大胡子司机其实就是组织的一分子,已经跟踪他们有一阵子了。当他亲眼目睹到金雍宇和司机私下“交易”时,就把司机打得半死,抢走他的财物,再假扮司机,用金钱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轻易地让计谋得逞。
两个中东人一左一右地抓住了他们,萨儿和金雍宇被迫分了开来。
“萨儿——”金雍宇伸出手来,试图抓住她。
“雍宇……”情急之下,她叫唤着他的名字,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在他即将被套上布袋前,她用中文嘶吼着,告诉他要如何保住性命。“他们只爱英雄,只疼惜英雄,你一定要做英雄……你绝对不能死!”
“萨儿……”恍若生死永隔的一刻。“我……”金雍宇还来不及吐露出爱意,后脑就被狠狠地敲了一记,眼前立刻一片黑暗……
原本以为能返抵国门,谁知那竟是一条不归路。
他被打得惨不忍睹。
既然沦落到这群毫无人性的人手里,只能任他们予取予求了。
金雍宇渐渐知道他们的身份了。
他们是举世闻名,让人闻之丧胆的“恐怖组织”。
他们为什么会找他下手呢?为什么独独挑上他?
他被狠狠地鞭打着。
他没想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中古时代的鞭刑?而且还发生在他身上。
他的衣服残破不堪,沾满血迹。而英俊的脸孔,更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布满伤痕。
那些人对他讲了一堆听不懂的话,由一个脸上有着大刀疤,看来正派的人用流利的英语翻译着。“只要你拿出钱来,就可以有一条生路——”
原来,他们是来要钱的。
他确实是很有钱,可是,他们跟他要钱做什么呢?是要用在哪里的呢?
他们该不会是要发展生化武器,来残害人类吧!这种不好的预感让他顿时变得严肃而冷酷了起来。
他的想法很快就被证实了。
他看到四周有最新的科技设备,显示他们早有发展核武的能力,只是碍于财产被西方国家冻结,所以只好找没有政治情结和宗教因素的有钱人来“赞助”。
他们专挑世界超级大亨,用绑架的方式来要钱,如果不肯乖乖配合,便会死于非命。
他想起被抓来前,萨儿一再交代的话。“一定要做英雄……”喔!亲爱的萨儿,我一定会照着你的话去做,成为一位真正的英雄,让你刮目相看。
他冷峻的表情让人望而生畏,也让那些恐怖分子胆战心惊而退缩了起来。
金雍宇正义凛然道:“最好把我打死,我是绝对不会给你们钱的。我不会拿钱去做不该做的事,那会让我觉得辛苦赚钱是毫无意义的。”
他的话,让这些恐怖份子觉得有意思极了。
中东人的思考模式,和东方人截然不同。他们做事不依常规,也不按牌理出牌,喜欢就是喜欢,厌恶就是厌恶,爱恨十分分明。而他们对金雍宇的勇气显然十分敬佩。
“看样子,他真的不怕死。”金雍宇被打得只剩半条命了,还不肯屈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富豪。在他们的眼里,有钱人大部分都贪生怕死,胆小如鼠,只要几个耳光或几个拳头,就会乖乖地吐出钱来。惟独这个东方人,宁死也不肯屈服。
“看样子,他真的是英雄!”一群人赞美有加,纷纷喝彩着。
或许,他们对东方人比较友善,或许,他们的敌人是美国人。“我们不该要他的命,毕竟他与我们毫无恩怨,而且他也是台湾的大企业家!”他们小声地讨论着。“他抵死不从的精神,让人十分敬佩……让他走吧!”
“金先生,算你好运,我们愿意放你回去——”首脑透过翻译说道。
“那萨儿呢?她在哪里?你们把萨儿藏到哪去了?”金雍宇十分牵挂着萨儿的安危,可是无论他如何用力挣扎,仍挣脱不了重重的绳锁。
首脑仰头大笑。“萨儿的命一点都不值钱,你的命才值钱——”
他全身的血液好像一下被抽干了,冷不防地,他被狠狠地打了一拳,再度昏死过去……
当金雍宇被国际媒体发现时,是躺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天主教医院里,这名之为“垂死之家”的医院,是由德蕾莎修女所创办的。
恐怖分子将他打成重伤,在他昏迷后,用车子载往巴基斯坦,再穿越国界到达印度首都,将他丢弃在贫民区的垃圾堆旁。如果不是被“垂死之家”的义工发现,赶紧将他送到医院救治,奄奄一息的他,可能早就没命了。
他们在他身上找到护照,经由联系后,终于和台湾的金家人联络上了。
接获通知的金家人立即前往印度探望他。金雍宇在国外差点丧命的消息曝光后,媒体也蜂拥而至……
金家人不惜耗费巨资,让还在昏迷中的金雍宇由医护人员陪同专机返台。护送的过程,多家媒体均全程拍摄下来了。
金雍宇是台湾叱咤风云的企业家,怎么会重伤昏迷在落后贫困的加尔各答?这真是疑点重重,令人费解。
许多人急于探知真相……
几天后——
“你终于醒了!”金雍宇一睁开眼睛,便觉得刺眼,原来是护士小姐正揭开窗帘,想让温暖的阳光洒入病房。
“我……”一股消毒药水的味道,令人哈鼻。
他遍体鳞伤,高烧不退,一直在昏迷中,几近死亡。幸好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后,又醒了过来,捡回了一条小命。
“我立即去找金律师来。”护士小姐急着走出去报告这个好消息。
没一会儿,金飙深、李贞德、金炎骏,及新婚妻子辛含灵都跑了进来。
金雍宇面容枯槁,眼神呆滞。
能够再度看到家人,他毕生最大的福气。“爸!妈!哥哥……”泪水不听使唤地掉了下来。
一向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金雍宇,此刻竟脆弱得不堪一击。
“雍宇……”大家都激动不已。
金炎骏抢着说道:“你永远都是我的弟弟,是金家的一分子!”
“儿子!”金飘深老泪纵横道。“我一直没告诉你,我爱你!”
爱这个字,让金雍宇长久的心结打开了,他再也不需要以冷漠、叛逆来武装自己了。
他嚎啕大哭。“爸!妈!哥哥……我也爱你们!”他伸出双手,抱着他们。“过去,都是我的错,是我无知、愚昧……我恨你们,却不知道你们对我的爱超过了一切……”
“这些都不重要了。”金炎骏鼓励地说着。“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哥哥,”金雍宇转头抱住金炎骏,感动道。“是啊!从小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你会永远保护我。”金雍宇用力地抱住哥哥。好像哥哥是他永远的靠山,永远不变的崇拜对象。
他在心底说着:哥哥纵使不是金家人,可是他的慈悲和善良却比他更像金家人,而他虽然流着金家人的血液,却十分冷血,比哥哥还不如。
原来,血缘不是一切,而且血缘又能证明什么呢?
重要的是心中有爱……
历经了一趟“死亡之旅”,金雍宇的人生再也不同了。
那一夜,是金家有始以来,最温暖的日子。
金家人虽然十分好奇金雍宇在加尔各答所发生的事,在这段时间里,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让他整个人有了重大的转变?
可是,他们却没有“逼问”金雍宇,或许他们认为,金雍宇能平安归来最重要,而且也解开了多年的“心结”,其他的就不必要求了。
金雍宇重回到文明的世界,对于尔虞我诈的商场却觉得生疏无比。反而时时想到死尸满地、哀鸿遍野的战场,而觉得心有余悸。当然最让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萨儿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他还没有完全复原,却已经用电话指示蒋幻笛调查“组织”的成员名单。
蒋幻笛一开门进来,就开始叨念个不停。“你应该多休息,好好调养调养,不要急着动脑筋。”
隔了那么久之后,她首次看到金雍宇,忍不住眼里泛着泪光,激动地说道:“见到你真好,知道你平安,我真的好高兴!也终于放下了心底的一块大石头!”
她特地避免与金家人碰面,因为他们老以为她是金雍宇的女人,会是金家的二媳妇。另外,也为了躲避媒体,以免再度被误传,或是过度渲染两人的关系,因此直到今天,蒋幻笛才敢偷偷地来探望金雍宇。
金雍宇嘲笑着。“怎么像个小女孩似的爱哭呢!在我的严厉教导下,我以为你应该会冷血冷心才是!”
“是的。”她立即拭去了泪水,换上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这才是我的好女孩!”金雍宇幽幽叹口气。
一直以来,他和蒋幻笛彼此关怀,相依为命。幻笛为了他,甚至可以牺牲生命,而金雍宇也竭尽所能的保护幻笛,他们之间的感情比兄妹还要深。
“有没有萨儿的消息——”金雍宇焦急地问着。
“我确定我们被萨儿骗了。”蒋幻笛面色沉重,取出所有相关的调查报告。“我几乎查遍了全球的慈善组织,都没有苏萨儿这个人。我认为……”她撇撇嘴,不屑地说:“‘他’不过是借捐款为幌子,实际上是想诈财,不然,就没有必要用假名来骗我们,由此看来,他应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金雍宇闻言,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突如其来的寒意满了全身,让他眼前一片黑暗。
等到他渐渐冷静下来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仔细思考了一遍,试图抽丝剥茧,找出真相——
和萨儿分开时,她再三叮咛的话,仍环绕在耳际,久久无法散去。她显然很了解那两个中东人的“身份”,而他们来自于“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