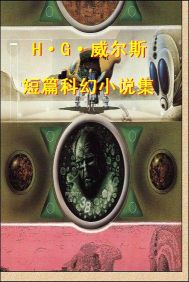乔治·法莱蒂-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皮埃罗,你能保守秘密吗?”
男孩胆怯地看着他,眯着眼睛,好像在考虑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
“秘密的意思,就是我对谁也不许说。”
“是的。现在你是个警察了,你也参加了警察的调查,警察可不希望透露秘密。这是超级机密。你知道它的意思吗?”
男孩用力摇摇头,晃着已经该修剪的头发。
“就是说,它非常机密,我们是唯一可以知道它的人。皮埃罗特工,你明白了吗?”
“是,长官。”
他用手放到额头上,敬了个礼,可能是从电视上学来的。弗兰克拿出吉罗姆从录像带上截取并放大的那张打印文件。
“我要给你看一张唱片封面。你能告诉我它在房间里吗?”
他把图片举到皮埃罗面前,后者聚精会神地眯缝起眼睛。男孩抬起头看着他,脸上挂着失望的表情,不像平时他找到答案那样心满意足。
“不在那里。”
弗兰克没有表露出失望之情,而是让皮埃罗感觉他做出了正确回答,“很好,皮埃罗特工。太棒了,现在你可以走了。但是别忘了,超级机密!”
皮埃罗用手指竖在嘴唇上表示沉默。他离开房间,朝导播室走去。弗兰克收好图片,离开电台,让摩莱利留下来应付局势。他走的时候,看到芭芭拉穿着极富诱惑力的黑色裙子,她走上前和警长说话。
他正回忆着摩莱利不知所措的可笑样子,大门一开,海伦娜走了出来,弗兰克看到她从反射镜映出的暗淡光线中慢慢走出。
他看到她优雅的身姿,听到她踏在碎石路面上的脚步声,尽管地面凹凸不平,她的步伐还是从容流畅。然后他看到浓密金发下美丽的脸,它被金铜色和浅金色的卷发环绕着,然后是她的眼睛,里面仿佛充满全世界的哀愁。
他走出汽车,绕到另一边打开车门。海伦娜·帕克穿着一套深色立领长裤套装,衣服很有点东方韵味,想必是哪个大设计师的手笔。不过,她的衣服并不张扬财富,只是静静地表明主人的品位。弗兰克注意到她几乎没有戴什么首饰,而且像其他时候一样,脸上也只化着极淡的妆。她走近时,一阵香水味袭面而来,像夜晚一样馥郁。
“弗兰克,你好。谢谢你为我开车门,不过你以后不必非这样做不可。”海伦娜进了汽车,抬脸对仍旧站在车门口的弗兰克说道。
“这不仅仅是出于礼貌,”弗兰克走到梅甘娜前面,冲她点点头说,“这是一辆法国车,如果不用点小手段,这车就启动不了。”
海伦娜显得很欣赏他的玩笑,开心地笑了。“你真让我吃惊,奥塔伯先生。有时候幽默的男人简直好像都绝种了。”弗兰克觉得她的笑容比任何珠宝都更美丽。面对这样的笑容,他突然觉得孤立无助,解除武装。
他一边绕回座位,一边思忖这些念头。他发动汽车,不禁想在切入正题之前,他们还要这样调侃多久。他也不知道他们俩当中,谁有勇气先提起真正的话题。
他看着海伦娜的侧面,车灯照到路面又反射回来,使她的侧影明暗交替。他不知道身边的人心里是否也是这样悲喜交加。她转过头,和他交换了一下目光。在阴影中,她眼中的欢快迅速消退,悲哀复又回归。弗兰克意识到她打算开始交谈。
“我知道你的故事,弗兰克。我父亲逼着我听。我被迫接受他知道的一切,就像我知道的一切也必须告诉他一样。我很难过。我觉得像冒犯你的生活一样,这感觉并不好。”弗兰克想起男人是猎手,女人是猎物的老话。就海伦娜·帕克而言,他觉得他们的角色被颠倒过来。这女人无意中成为了猎手,也许是因为她充任猎物太久了。
“我唯一能和你交换的,就是我的故事。我觉得不然这样太不公平:我和你在一起,提一大堆让你很难回答的问题。”
弗兰克听着海伦娜的声音,跟着从罗克布吕纳到蒙顿的车流慢慢开着。他们周围充满生机勃勃的气氛,全是光明和普通的生活,人们沿着炎热、灯火明亮的海岸散步,寻找着各种其实无甚意义的小乐子,目的不为别的,就为了享受懒洋洋地寻找本身的乐趣。
没有财宝,没有岛屿,也没有地图。只有幻象,也不知能延续多久。有时,幻象的尽头是一个重复着单调词语的声音,“我杀……”
弗兰克几乎下意识地伸手关掉收音机,好像他担心一个不自然的声音会突然出现,把他召回现实。轻音乐消失了。
“你知道我的故事,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有一个故事。我希望你和我不一样。”
“要是不一样的话,你觉得我会在这里吗?”海伦娜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轻柔。这是一个在交战中寻求和解的女人的声音。“你妻子是什么样子?”
弗兰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有点吃惊。他直率地回答,“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她不能一句话说清楚。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样看她的,但是现在没必要说到这个。”
“她叫什么名字?”
“哈瑞娅特。”海伦娜像接受一个老朋友一样记下这个名字。“哈瑞娅特。我感觉我已经很熟悉她了,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你可能会奇怪,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充满苦涩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脆弱的女人总会彼此理解。”
海伦娜向窗外看了一会儿。她的话像旅途一样快要到达终点。
“我妹妹亚利安娜比我坚强得多。她明白一切,离开了,她逃离了我们父亲的疯狂。或者她只是不喜欢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我却逃不走……”
“因为你的儿子?”
海伦娜把脸埋在手中。她的声音透过手指透了出来,像穿透一个悲哀的监狱。
“他不是我的儿子。”
“他不是你的儿子?”
“不,他是我的弟弟。”
“你弟弟?可是你说……”
“我告诉你斯图亚特是我的儿子。”海伦娜抬起脸回答。没有人能忍受她双眼中的痛苦而不抑郁地死去。“他是的,但是他也是我的弟弟。”
弗兰克屏住呼吸,试图理解她的意思。海伦娜哭了起来。女人喃喃低语着,但是在小小的汽车空间里,它听起来仿佛一声被压抑太久的解放的呼喊。
“见鬼,内森·帕克,愿你下地狱去!但愿你在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
弗兰克看到路边有个停车场,便打开转向灯,把车开到那里停下。他关掉马达,让车灯还亮着。
他转向海伦娜。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一样,女人滑进他的怀抱寻求保护,沾满泪水的脸寻找着他的上衣,他的手爱抚她的头发,多少个邪恶的晚上就是这些头发遮掩着羞耻的脸。他们这样呆了很长时间,弗兰克觉得仿佛长得无穷无尽。
他脑海中涌过千思万绪,一千个生活的一千个故事,现实和想象混为一体,过去和现在融合,真相和可能性混同,色彩和黑暗胶结,鲜花的芳香和泥土的腐味重叠。
他仿佛看到自己在父母家中,看到内森·帕克把手伸向女儿,看到哈瑞娅特的眼泪,看到匕首刺向绑在椅子上的人,看到刀光在他的鼻孔里一闪,看到10岁大的男孩蓝色眼睛的凝视,他生活在最粗野的畜生中间而不自知。
在他的思绪中,仇恨转变为一道炫目的光,光渐渐变成无言的高呼,它如此强烈,震裂所有反映着人类邪恶的镜子,所有藏掖邪恶的墙壁,所有那些渴求摆脱绝望处境的人徒劳地敲击的门。
海伦娜只想忘却。这也正是弗兰克需要的东西,就在这里,在停在碎石路边的汽车中,在这个拥抱里,在墙与长青藤的相逢能归结为的一个简单词语中:终于。
弗兰克始终记不得谁先松手。他们的目光终于交接的时候,他们都带着同样宽慰的心情感觉到,一件重要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们接了吻。在这个初吻里,他们的嘴唇出于胆怯而不是爱情胶合在一起。胆怯是因为对这一切恍恍惚惚的担忧,担忧绝望被误认为爱情,担心孤独被改头换面以另一个名称,担心幸福只是海市蜃楼。
他们身不由己地一次又一次接吻,直到渐渐有了信心,直到怀疑变成一线小小的希望,因为他们俩现在都无力支付奢侈的幻想。
他们喘息着对视。海伦娜先恢复神智,她抚弄着他的脸庞。
“说点傻话吧?说点又傻又有趣的话吧。”
“我们错过订的晚餐了。”
海伦娜又投向他的怀抱,弗兰克听到她宽慰地轻笑,搂着他的脖子轻轻颤抖。
“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弗兰克·奥塔伯。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和你在一起。掉转车头,我们回到我家去吧。冰箱里有食物和酒。我今天晚上不想把你分给世界。”
弗兰克发动马达,沿着来时的路开了回去。什么时候发生的?可能是一个小时,或者是一生之前。在这种情境中,他没有了时间概念。他只知道一件事。要是内森·帕克将军这会儿出现在他面前,他会杀死他。
※ ※ ※ ※ ※ ※
男人藏在秘密的地方,躺在床上,滑进令他心满意足的酣睡中,心情像小船驶回港口一样单纯、感激。他的呼吸平静均匀,几乎听不到声音,盖在他身上的床单只有微微一点波动,表明他还活着,证明覆盖在他身上的只是毯子而不是尸衣。
他身边,枯萎的尸体在玻璃棺材里同样一动不动。他戴着格里格·耶兹明精致的面具,仿佛在炫耀似的。这次,割下的面皮简直是个杰作。它不像是个面具,倒像是那干枯的头骨上真正的面孔。
男人躺在床上睡得非常香甜,还做着梦。他的睡眠时不时遭到莫名形象的惊扰。
首先,到处是黑暗。然后,一个建筑旁边的土路隐隐出现在满月温柔的光线中。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季之夜。一点点地,男人走近一幢巨大房子的侧影。这房子处于阴影中,几乎不为人注目,散发出熟悉的薰衣草香味。男人感到碎石戳着赤脚。他希望往前走,但同时又感到害怕。
男人听到隐隐的沉重呼吸声,他发现这呼吸声是他自己的,突然涌出的恐惧很快平静下来,烟消云散。他走到院子里,院子里有一个石头壁炉的烟囱,它从屋顶轮廓上突然竖起,好像一只指向月亮的手指。房子周围一片安静,仿佛在邀请他进去。
突然之间他就进了房子,爬上楼梯。他抬头看着头顶微弱的灯光。从楼梯顶层,依稀可以看到一盏灯,光线在楼梯上投下阴影。灯光中有一个人站着的清晰身影。
男人感觉恐惧又回来了,像一条过紧的领带。不过他仍旧不顾一切往上爬。他不情愿地爬着,一边好奇在楼梯顶端究竟会发现谁,他一边想,一边发觉自己很怕这个发现。
一级,又一级。木头在赤脚下嘎吱作响,吓得他屏住再次变得沉重无比的呼吸。他的手扶在木头栏杆上,渐渐染上从上面照射下的灯光。
他即将走完台阶时,身影突然转过身,走进有灯光的门里,把他单独留在台阶上。
男人爬完最后的台阶,他面前有一扇敞开的门,明亮、晃动的灯光从里面倾泻出来。他慢慢走到门槛那里,跨过了它,沐浴在犹如噪音的灯光中。
一个人正站在屋子中间。他的身体赤裸着,灵活、结实,但是他的脸是变形的。好像有只章鱼包裹在他的脸上,抹去了五官。一双浅色眼睛从长得奇形怪状的肌肉中鼓突出来,哀求地看着他,仿佛在企求怜悯。不幸的生物在哭泣。
“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