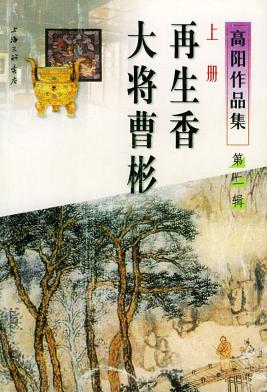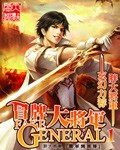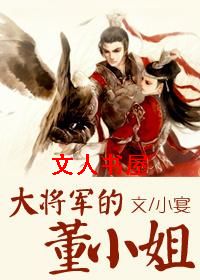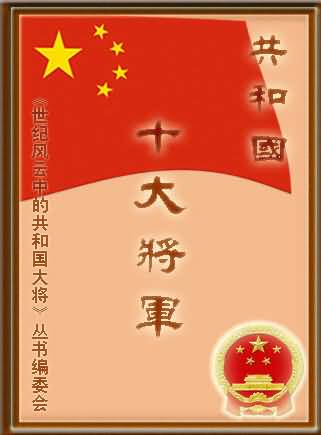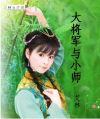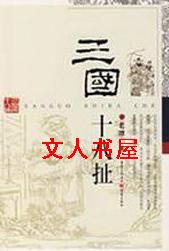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4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一天,右江各县城乡,都热烈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前委派我到田东去参加当地的庆祝大会。天气特别晴朗,田东万人空巷,都聚集到镇北的广场上来。红军战士们威武、 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农民们敲锣打鼓,妇女和小孩穿红着绿,从百十里外赶来,广场上挨挨挤挤站了足足5 万多人,红旗如海,欢声雷动。庆祝会开过后,就在广场上进行了各种文艺活动,演戏、唱民歌等等。这一带农村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饱受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摧残而新翻了身的农民们,当着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成立的时候,怎不欢欣鼓舞呢。这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苏维埃政府招待到会的5 万人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
下午,我们乘着一艘挂满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时,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着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同志也不断地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一7 一股巨大的声浪。这时,晴空万里,阳光耀眼,红旗招展如画,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革命力量,巩固胜利!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全中国去!”
红七军能够这样迅速、顺利地建立与发展,首先是由于党的坚强的领导,和党员们团结一致、艰苦努力的工作。我们部队里的党员,虽然有些是外省来的,有些是广西地方上来的,还有大部分是在部队中新发展的,但是大家非常团结,革命热情很高,都能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们都是红七军的政治骨干,也就是红七军能够发展和巩固的有力保证。
其次,是教育群众、争取群众。从旧式军队转变为新型的革命军队,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必须提高广大战士的革命觉悟。、而反动军官正是压制民主、阻碍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一种恶势力,是改造旧军队中的绊脚石。广大士兵群众对反动军官的虐待非常痛恨,我们如果不搬掉这块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就不可能更好的联系群众,甚至会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我们才能最迅速地取得士兵群众的拥护。因此,发动群 众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就成了改造旧军队的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抓紧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因而我们就教育了群众,从而争取了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
第三是争取领导权。我们采取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党的活动,取得了部队的领导权;另方面,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在群众积极要求惩办、撤换旧军官的愤激情绪下,我们接受群众要求,即分配党员干部担任各级领导。由上而下地采取命令方式,使撤换、调配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又由下而上地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两者一结合,我们所掌握的领导权便不可动摇了,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部队也才能更加巩固。
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了,促使部队内部益发团结一致。这也是红七军建成和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部队的内部因素以外,革命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当时,广西还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一支群众武装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因此,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革命武装的配合,右江群众的革命运动也才能进一步开展,并且迅捷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政权,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
关于红七军在湘赣边活动的一些情况1930年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决定红七军打大城市,与朱毛红军会师武汉,我们公开的提法是:开始打柳州,然后打桂林,会合朱毛红军。具体的任务是:搞总暴动,打大城市(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建立两广政权,与全国红军会师武汉。中央派邓刚为中央代表,监督贯彻执行。当时红七军有一万多人,执行此任务有些困难,红七军党代表邓小平同志,曾对此产生怀疑,与中央代表有些争执,后来还是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为贯彻立三路线,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曾冒险攻打柳州。因部队训练差,完不成任务,连受严重损失,两门山炮也埋掉了,根据地丢掉了,以后就没继续攻打桂林。到了全县(此时中央代表邓刚回上海),行委接受了教训,但考虑到当时如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两三个月,困难较大;乃决定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此时七军已由原一万多人减员为4000多人,只有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每团9 个连。从全县经湖南道县到江华,沿途与敌挨户团进行战斗。在江华城受敌袭击,我们守城门,外有敌人进攻,城里有内应到处打枪,有一连未撤出来。部队受阻后,又返回全县(此时正值1931年元旦),改道向广东进发,在连县打了一仗,至乳县与湘粤军六、七团之众作战一天,部队损失很大,牺牲师长一人,伤师长一人,团长2人。此时部队只剩3000余人。当时部队相当疲劳,到乐昌西北的梅花地区(大革命即有党的基 础)找到地方党的组织,才听到立三路线是错误路线的传达。在梅花得到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休息了两天,决定继续东进到江西去。在乐昌以北过乐昌河(武水)时,由于船只少,部队过河慢,敌人从韶关、乐昌用汽车增运兵力,向七军进攻,此时邓小平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两个营过河后经湖南汝城、桂东到达赣南。被阻于河西之五十八团一个营和军直属队一部和伙食担子等,由我率领抵抗韶关方面来的敌人,未能过河,又返回梅花地区,整理部队,丢掉大行李,留下不能走的伤病员,把军直属队的警卫连、特务连(李天佑任连长)和五十八团的一个营编为两个营6 个连。
休息了两天,在地方党的帮助下,从梅花转道向湖南进发,梅花地方党组织派人担任向导,经湘粤交界之坪石(属乐昌)乘由群众伪装之运粮商船,于夜间顺利地渡过武水,这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是不行的。过武水后群众帮助带路,到达郴县东××山岭休息了四五天,湘军分数路进攻,部队转到了桂东、资兴。在资兴附近过的旧历年。敌又以3 师兵力进攻,又转移到酃县王里塘,迂到当地游击队(朱总司令建立的,有几十个人)。这时汝城大恶霸匪首胡凤璋和他的儿子带1000多人追来,当即将其击溃,缴了百多条枪,休息一下过了水口,在酃县附近一个山上与王震同志率领的湘东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了。这时大约是1931年2 ~3 月间(旧日历年一月)。
会师后,七军与独一师两个部队共约2000人,后向茶陵进发。在严塘与陈光中的部队打了一仗,俘虏了一个团长。到达茶陵苏区,补充了一部分棉衣,受到苏区人民的热情招待,部队情绪高涨。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到了根据地感到有了依靠,感到根据地人民的亲切,深深认识到毛主席创建井岗山根据地和他的根据地思想的英明伟大。
以后到莲花休整了一个短时期,就到永新与湘东南特委机关会合,安置了后方与伤病员,留下了河西教导队,特委给七军补充了七八百人。这时没有接到中央指示,我们也没有过河东的打算,与红七军主力也没有联系上,我们就在湘东南特委的指导下进行行动。
中央红军反对敌人二次“围剿”时,红七军的部队和独立第一师与红二十军会合(军长肖文久、政委曾炳春)在河西积极配合行动,进攻敌人。
为了统一指挥河西部队行动,临时组织了河西总指挥部,我为总指挥,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兼总指挥部政委。当时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同志正在湘赣,我们有事即和他商量。'奇·书·网…整。理'提。供'这时的军事行动任务是湘东南特委决定的,主要是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巩固扩大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红七军、红二十军、独立一师,在总指挥部指挥下统一行动,大约是四五月间,首先进攻吉安永阳镇敌人的一个旅。独一师部队作战是勇敢的,和七军进攻永阳,二十军在战斗中垮了下来。敌人迂回到后面包围了我们的指挥位置,相当危险,后终于打退了敌人。敌人跑了,我们占领了永阳,这个仗是胜仗也是败仗,二十军的战斗力太差。永阳镇战斗后,我即带部队去找红七军主力。会合之后,七军和独一师向安福方面行动(二十军没有去),安福之敌向我进攻,我将敌打垮,追至城下,包围了敌人,大家商量确定进攻守城之敌,打了一下,没有打下来就不打了。
袁州(宜春)行动是因为那里敌人对群众摧残的很厉害,红军好久没去,群众情绪低落,地方工作开展困难。于是特委决定七军和独一师到袁州附近游击一下,相机歼灭敌人(找点小仗打),以鼓励群众斗争情绪。部队在袁州西活动,为了找报纸看消息,曾打了一个靖卫团的据点,几十个靖卫狗子向袁州逃跑,部队追了一下到河边也就回来了。没有攻城,我也不记得打过泰和。
由于没有电台和中央联络,当时交通十分困难。在二次反“围剿”中,中央没给什么指示。行动是由湘东南特委确定的。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之前(5 月),滕代远和张启龙同志就带特务团过河东去了。
袁州行动之后又向湘东南行动,曾两次攻克茶陵,又打开攸县和安仁县城,两次占领酃县,后回永新。六七月间中央命令七军过河东,这时已粉碎敌人二次“围剿”,正当反三次“围剿”开始,七军过河东是为执行反敌三次“围剿”任务的。王震同志率领独一师送七军到赣州以西之沙地,我们从赣州以北过了赣江。
一次重大的失策“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企图变我国为殖民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群众一致的要求。可是,卖国贼蒋介石却悍然不顾民族存亡,继续驱使其军队进攻我红军根据地。1933年1 月,我党发布了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3 个条件下与一切军队合作抗日。这个宣言,受到各阶层广大爱国群众的热烈响应,并且也影响了一部分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被蒋介石从上海抗日前线调来进攻红军的十九路军,便是仇恨日本侵略者,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响应我党抗日宣言的一支国民党军队。
1933年春,我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以后,驻在福建的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先派陈公培,后又派秘书长徐名鸿与陈公培和红军谈判。
和不和十九路军谈判?在党内曾一度引起争论。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对当时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更是毫无认识。正如我党中央在“关于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