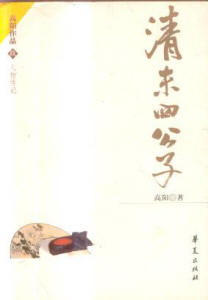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第40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二哥,你替我欢喜的是哪一门子呢?”万呈祥抢着答道:“王大哥,你可不知道,他专好替人家算隔壁账。将来你如果住在湘君屋中,他能在窗户底下趴一夜,遇巧了你们做梦,他还许睁着眼呢!”其盛赶过来要打呈祥,说:“你满嘴还要喷些什么?”呈祥赶紧请安讨饶,说:“张二哥,你千万可别打我!提防打出斗粘儿来,脏了你的衣裳。”呈祥这样一说,天宠道:“真是我也忘啦,万兄有瘾,我怎么不让你吸烟呢。”吩咐家人快把小客厅床底下那一份烟具拿到这屋来,再到账房跟舅老爷支一大盒烟膏,快去快来!不大工夫家人将烟膏、烟具一齐拿来,安放好了,燃着烟灯。天宠请他两人躺下自开自吃,说:“恕我手笨,不能替你们烧烟。”两人也不客气,呈祥先抄起签子来,蘸了一点,在灯上一烤,便喝彩道:“好烟好烟,这多半是香港大土吧。”天宠笑道:“万兄空是老瘾士,却不知这烟的来历。实对你两位说,这是完全国货,产自山东莒州。前年该省老瓢把子(按:瓢把子即杆子头也)孙百万有事到河南去,在我寨里住了一个多月,临行之时,送给我二百两莒州烟土。我当时至再不收,说自己既不吸烟,何必空放着它,还是请大哥留着自用吧。他说存得很多,你留着应酬朋友,也是好的。因为这种土与众不同,直可充作冒牌的大土公膏。”呈祥连吸了两口,说:“果然真好,可惜你守着这样好东西,自己却不用,怕是口福太薄。要放在我老万身上,早就吃得精光精光了。”他一壁说着,又装好了一口,一定叫天宠尝尝,说:“你尝这滋味,比昨天我家里那烟又高出十倍了。”天宠情不可却,躺下吸了一口,果然觉得这烟的香味比昨天的深长,而且口力也格外来得沉重。他吸完了,自己也烧了一口,转敬张其盛吃完,便跳起来,说:“咱们一同到春云班去吧,这时湘君许盼得眼穿了。”呈祥此时正抓住便宜好大烟,恨不将他明天的瘾,今天都一气过足了,哪里还肯动一动,说:“你不要瞎闹了,人家班子里,这时还不能起床呢。咱们跑了去,堵热被窝儿,多么没意思。”其盛道:“岂有此理!这时都四点多了,纵然起得晚,也不至落太阳才起来啊。”天宠道:“已然四点多,我们何不等吃过晚饭再去,也可以多坐一会儿,白天有什么意思呢?”呈祥道:“着啊,你听人家主人,都能沉住气,不像你那样着急,你闹的是哪一门子毛包呢?”其盛没得说了,候至六点钟,天宠提倡到骡马市大街瑞记黔菜馆去吃饭,吃完了饭,到春云班去过瘾。呈祥赞成,把吃剩下的半盒子烟膏揣在怀里,说:“咱们自己有烟,不犯着吃他班子的。”天宠吩咐套车马,三人同乘马车,到瑞记吃过饭,一直来春云班。
看门的见是王将军到了,这一声喊下去,真能惊动了四邻。老鸨金氏三步并一步地迎出来,一直往湘君屋里让,说:“我们姑娘今天胃气病又重了,不能亲自迎接诸位大人,请诸位格外原谅吧。”三人走进来,果见湘君在床上蒙被躺着,见大家走进,仰起头来,说了一声有罪,请诸位老爷恕我吧。天宠在灯光下,见她玉容消瘦,确显露十分病态,很动了一种怜惜之意。忙过去执了她的手,问道:“你昨天还是好好的,为何一夜工夫,竟病成这种样子?”湘君两眼有些湿润了,说:“我这病原是时犯时愈,没想到今天竟会加重了。”万呈祥极力撺掇她吸大烟,湘君至再不肯,说:“昨天吸了两口,当时虽觉着好一点,哪知转眼工夫,竟自加重。看起来大烟是吸不得了。”天宠也说:“吸烟不过一时止痛,究非根本治疗之法。我们河南有一位大夫,专能治胃气病,不过这个人并不出马行医。他现在公府中当着一份秘书,错非我,谁也约不来他。”呈祥道:“你说的可是陶一鹗吗?”天宠道:“正是。”呈祥摇头咋舌,说:“我的王将军,你如何能请他来?这位先生脾气非常乖僻,要论医道,诚然是再高明不过了,但是他从来不给人治病。比如公府中的茶房差役,谁要有了病,他倒赶着给治,有时候还自己掏出几块钱来,给他们作药资。说来也真怪,一剂药下去准好,并不用吃第二剂。要是有钱有势的谁想请他,你便摆上几块金元宝,也休想他抬一抬眼皮。这样怪物,要请他到班子来给姑娘治病,如何做得到呢?”天宠笑道:“别人当然是请不来,唯有我王天宠,哪时请他,就得哪时到。他不伺候项大总统,也得伺候我王将军。你们要不信,明天这时候,仍在这里晤面。如果没有陶一鹗,我情愿罚酒席一桌,请你们大家白吃。”张、万两人说好好,就是这样。因为湘君在病间,大家也不便久坐,随便谈了几句,便各自散了。临行之时,湘君再三嘱托:“明天务必将先生请来,我的肚腹中,仿佛有什么虫子乱撞乱跳。每逢撞跳到剧烈时候,我就眩晕过去,看起来这病如没有高明人,是不得好了。”天宠再三安慰:“你不要害怕,明天我一定请先生来,保管药到病除。”金氏也再三央求,说:“将军是我们姑娘的救星,您明天要不来,她的小命儿可就不能保了。”一壁说着,又用手帕子直擦眼泪,表示关切之意。天宠点点头,出门上马车去了。第二天张、万两人,果然在下午三点钟同到春云班,来访王将军。进门一问,王将军尚未到来。呈祥笑向其盛道:“何如?我早知道他约不来,他偏要同我们打赌。这一来,他只好认输吧。”其盛道:“这天气还早,我们也不能武断人家准约不来,再少候一刻,自然就知道了。”金氏说湘君折腾了一宵半日,此时好容易睡着了,请两位大人先到我屋中坐吧。张、万走进老板的屋子,见大烟灯点得十分明亮,呈祥早已欢喜得笑逐颜开,说:“我早知道老板屋里有这样好宝贝,何必在姑娘屋里坐呢?”金氏笑道:“只要万大人肯赏脸,我天天把烟灯点得亮亮的,欢迎您来过瘾。”呈祥一歪身躺下,掏出昨天在王宅拿的烟盒子,打算实行过瘾。不料正当这时候,看门的大喊王将军来了,其盛一把将他揪起,说咱们看看去,到底陶一鹗来了没来。呈祥摇头,只隔着窗帘向外观看。见王天宠陪着一位六十多岁须发糁白的老先生,手中拄着文明杖,拱肩驼背,走路有点不大得力,天宠在一旁扶持着,一同进了湘君的屋子。其盛又反过嘴来,问呈祥,你看如何?呈祥挑起大拇指来,啧啧地赞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不怪人家吹,我们真得甘拜下风。”
不提他两人在这里捣鬼,却说天宠陪着陶一鹗进了湘君的屋子,金氏赶忙过来应酬。天宠说:“陶大人吃水烟,不吃烟卷。”金氏连忙捧出赤金水烟袋,请陶大人吸烟。此时湘君仍在酣睡,因为她疼了一夜不曾合眼,此时实在乏了。天宠向一鹗道:“因为这一点小事,惊动老乡长,晚生心里实在深抱不安。只因这个人与我们同乡,多少有一点桑梓之情,而且她是火坑难女,理应加以援救,晚生知道老乡长平素不入花街,这一次实在出于无法,还得求您格外原谅。”陶一鹗也不答他的话,呼啦呼啦地吸了两筒水烟,然后用命令式的口吻,吩咐金氏道:“你把她叫起来!我好诊脉。”金氏赶紧过去,轻轻地呼唤:“湘君姑娘醒一醒,王大人还同着一位看病的大人都来到啦。你醒醒,人家好替你诊脉啊。”湘君“哎呦”了一声,睁开两只病眼,见是她假母立在身旁,便有气无力地问道:“王将军可曾来吗?”金氏道:“王将军不但自己来了,还同了一位陶大人来。你勉强挣扎坐起,人家好给你诊脉啊。”陶一鹗摇头道:“这倒无须。只要醒了,能伸出手来,就可以诊脉。”说罢便走过来,坐在炕沿上。金氏忙取一个小花枕来,放在前边,又把湘君的手,替她拉出来,放在枕上。一鹗闭目合睛,用三个手指仔细诊脉。右手诊罢,又诊左手,直诊了有二十分钟,方才立起身来,向天宠皱眉道:“这是冤孽病啊!”一句话把天宠同金氏都吓了一个不轻,天宠忙问道:“怎么是冤孽病?难道病里还有冤孽吗?”一鹗坐下,慢条斯理地答道:“她这胃病不是一天了,她的肠胃中,现在涵育着一种生物。这种生物其名曰赤火蛇,乃是河水中一种才出壳的小水蛇,其细如线,身长不过数分,因为饮冷水时,随着到了肠中。这种小蛇,遇冰不僵,见火不化,所以能在肠胃中生育。幸而这两条蛇俱是雌性,并无雄性,要不然,它在肠中还能孳生繁殖,病人更受不得了。”一鹗说了这一大篇,把金氏吓得目瞪口呆,连忙跪在地上,向一鹗大磕其头,说:“我的陶大人,您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千万想个法儿,把我们姑娘的病治好吧。她倘然有一个山高水低,可怜我这苦老婆子,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啦。”她一壁说着,三行鼻涕两行泪,真叫人看着可怜。天宠在一旁也一再恳求,说:“这样冤孽病,错非老乡长,再无第二人能治。无论如何,您也得想法子。”一鹗只是皱眉不语,停了有一刻钟,摇着头叹气,对天宠说道:“治病容易求药难,我纵然开了方子,你也没有地方去打药啊。”天宠笑道:“这个请您放心,无论多贵的药,不惜它是千两一换的野参,千金一架的鹿茸,晚生也肯拿出钱来去买。”一鹗冷笑道:“你以为是贵而难得吗?这药并不贵,连十个铜子也不值,可是仓促之间,拿千金也没地方去寻。”天宠纳闷道:“是什么物件呢?”一鹗道:“一钱红矾、两枚鹊卵,只用两味药,便可以收功,其余任什么也用不着。”金氏“啊呀”了一声,说:“红矾能吃得吗?”一句话招恼了一鹗,站起来便往外走,说:“你既知道吃不得,何必请我看呢?”天宠忙拦住,作揖道歉,说:“她是一个糊涂妇人,老乡长何必同她一般见识。”又转回头来申斥金氏:“你不要胡说!陶大人用药,连总统都吃,怎么你们这样人倒吃不得?”金氏诺诺连声,不敢再说什么,却跑到自己屋里向张、万两人诉委屈:“倘然我们姑娘吃出一个好歹来,岂不活活地坑死了我?”张其盛笑道:“没要紧,如果吃死了,我叫王将军赔你五千块钱,你还不放心吗?”金氏道:“但愿吃好了,我也不希图那五千块钱。”万呈祥道:“你放心吧,死了都没亏可吃。不要说红矾,果然是陶大人开的方子,绿矾也一样吃,决然吃不出祸来。”金氏心里有底,这才又到湘君屋中,只见天宠向她问道:“你们这左近可有乌鸦巢吗?”金氏仰头想了想,说:“真巧极啦,我们这春云班旁边,原先是一处饭馆子,叫作槐荫楼。因为饭馆子后边有一株老槐树,高与楼齐,它的枝叶完全罩在楼窗上,每逢夏令,不用搭天棚,屋中自然凉爽。后来饭馆关闭了,因为欠债太多,下不下匾来,到如今,房子还闲着。那老槐树上,搭了不少的乌鸦巢,每逢早晨,喜鹊同老鸦叽叽呱呱地在树枝上打架,大概它是为争巢。但不知王将军问这个可有什么用处?”天宠不理她,却向一鹗笑道:“只要有巢就好办了,您开条子,打发人去买红矾。鹊卵的事,完全交给我啦。不怕在树梢上,我也一样能取下来。”一鹗笑道:“从前听说你飞行无迹,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