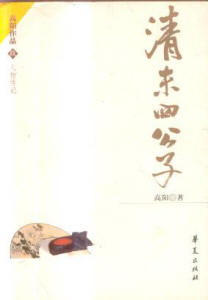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第40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叫来的妓女已先后走净,只剩了湘君一个人,她的意思也想走,却被张其盛留住,说:“你的胃气病吃几口大烟准好,万老爷这里有新从香港来的大土公膏,你吃两口再走,我这确是一番好意。”湘君道:“谢谢张老爷!改天再扰吧。来的时候,我娘就嘱咐早回去,现在已经掌灯了,再一吃烟,不定要晚到什么时候了。”其盛笑着对天宠说:“这可用着你安驾了。”天宠果然对湘君说:“你不要害怕,晚回去一刻半刻的,算不了什么。难得张万两位老爷这份厚意,你怎好拒却呢?”湘君见天宠这样留她,果然迟疑不走了。其盛笑道:“到底是王将军一言九鼎,快点烟灯,看我来伺候王太太吃烟。”天宠说:“张大哥,你不要这样开玩笑,叫湘君心里岂不骂你?”其盛尚未答言,湘君早抢着说道:“只怕我们没有这大造化,要果然有这造化,感激张老爷还来不及,为什么骂人家呢?”其盛鼓掌大笑,说:“这是弦外之音,王将军,你就赶紧建筑金屋吧。”天宠一笑,呈祥将烟灯点着,其盛真给装好了一口,让湘君吃。湘君说:“罪过罪过,诸位老爷都未上口,我怎敢占先呢?”大家全说:“这有什么?你是有病,理应先吃这一口,不必让了。”湘君果然吸了一口,第二口让天宠吃,天宠道:“我向来不吃这个,当年在河南当杆子头时候,保险的烟土每年都不下几千包,我不止一口不吃,连我手下的弟兄们,也一概不准他们吃。后来同白朗闹意见,还是因为吃烟呢。他的烟瘾很大,却瞒着我不叫知道,那如何能瞒得住呢?我始而婉言劝他,他不肯听,后来索性揭明了,彼此的意见越闹越深,结果才闹得归于决裂。假如我如今要吃上大烟,也对不起白朗啊。”呈祥大笑道:“你以为嘴一沾枪,就有了大烟瘾吗?那真是笑话了。实对你说,这种东西是很不容易上瘾的,按准了时候,按准了口数,天天地吃,月月地吃,过三年都不准能上真瘾。何况是逢场作戏,偶然吸上一口半口呢?你不信请天天到舍下来,吃上三个月,如果有了瘾,我万呈祥情愿输你一辈子大烟吃,并且给你当一辈子烟奴,你不信就试试看。”天宠大笑,说:“我也不贪图这便宜,你也不必供我一辈子大烟。”其盛接过烟枪来,说:“让我吃吧。”他一气将三分重的一口大烟吸了个精光,自己又装了一口略小的对天宠笑道:“王将军,你所以不肯吸大烟的缘故是怕上瘾,有损你的英雄体质。请你看一看,我老张的体质比你何如,我是没有一天不吸的。假如要是吸烟就与体质有伤,那早就当皮包骨了,还能这样筋粗肉厚,像一个赳赳武夫吗?”他这一套话,却把天宠说活了心,觉得其盛所言不为无理,自己偶然吸一两口,也不见得就与体质有伤。他心里一活动,其盛早就看出来了,立刻将烟枪递上,说:“我替你看斗,你就闭着眼吸吧。”天宠果然不再推辞,一口气将烟吸光。他是生平未尝此味的人,如今忽然尝着了,但觉香喷喷的,不呛不辣,较比什么大炮台、吕宋烟,又别有一种不同的滋味。吸过了,向其盛拱手致谢,他要想坐起来,其盛却将他一手按住说:“先躺一刻,不要忙,俟等烟力散一散再起来不迟。”天宠果然躺着不动,但觉得四肢百体、周身血脉,全都酥酥然,有一股舒畅之气在里面运行。他心里想:怨不得世人多愿吸大烟,原来有这样不可思议的魔力。他正在想着,其盛又装了一口,比方才略小一点,说:“吸烟不吸单,请把这一口再饶上吧。”天宠本是一个再豪爽不过的人,他既觉得这大烟滋味很好,便不肯再事虚让,接过来又一气吸光。这两口烟到了肚中,格外觉得精神焕发。此时人客差不多全走净了,只剩下张其盛、李松林、王天宠,还有天宠新认识的湘君。她因为连吸了两三口大烟,觉得有点头晕,不敢到外边,恐怕见风醉倒,因此同天宠对面躺着。天宠便搭讪着同她谈话,说:“你是什么地方人?因何流落在烟花队中?你家里可还有父母兄弟?”湘君被问,眼圈一红,低低地叹了一口气,说:“王老爷,按说咱们是初次见面,原不能过什么深谈,不过彼此是同乡,多少说有一点乡情,我看王老爷,又是一位豪气冲天的好男子,因此我才剖肝沥胆地对你说一说。我是河南府城里的人,原本姓贺,我父亲是一位黉门秀才,母亲司氏,膝前只生我姊弟两人,家中开着一座书店,兼卖南纸笔墨,字号是秀文堂。因为我父亲名文美,字子秀,所以才起了这个字号。每年的生意虽不甚好,但是对付着可以糊口度日。我十六岁上,便在女子中学毕业,原想着再入大学,我父亲说供给不起,况且女孩子多念书,也没有用处,因此便在家中帮着母亲操作。我那弟弟名叫贺炳新,比我小两岁,他也考入洛阳中学肄业。那一年伏假,因为学校中带着学生到鸡公山旅行,可就出了意外的祸事了。”天宠忙问什么祸事,湘君含着两泡眼泪说道:“我那弟弟炳新才十五岁,身体又弱,走起路来哪能赶得上人家,因此在鸡公山游山时候,便失落在后面了。校长到山上一查点人数,就缺他一个,当时急了,赶紧向回路搜寻,哪里寻一点影儿。回到客栈中,又差人四下寻觅,始终也未能发现。他们空在信阳滞留了一星期,也未能将学生找回。结果还是我父亲在书店中接到一封信,信上说你那儿子已被我们绑了票了,快预备三千块钱,到某地方去赎,只限七天限,过了七天,便撕票,再想赎也不成了。信后并注明,他们是白朗部下。我父亲见了这信,如何不急,反倒先寻了校长去朝他要人,闹得不可开交,后来有人出来调停,算是学校与我家中各认一半。在学校无论怎样穷,一千五百块钱尚不至拿不出来。唯有我们家中,可就真为难了,一个小书铺,把货物全算上也不值一千块钱,何况书铺一倒出去,家中孩子大人立刻就得挨饿,只得把住房出卖。这所房子,本值一千多块,因为急卖,仅仅就卖到七百,还下差着八百块钱没有着落呢。借贷无门,可想什么法子?这时候我们街坊有一个叫郭四的,他给出主意,说目前有北京某某贵官想要纳一房姨太太,要果然人材好,一千八百的彩礼他都肯拿,何不把你家大姑娘说给人做姨太太?既可救了目前之急,又可攀一门好亲戚,姑娘也有了享福的地方,这真是三全其美,为什么不这样办呢?我父始而不肯,说我家世代书香,女儿不能给人做妾。后来倒是我出来说,弟弟可以接续贺门后代,比我这做女儿的关系大得多,您莫若想开了,就这样办,好救我弟弟出来。虽说给人做妾,将来还有见面之时,父亲何必这样拘泥,眼睁睁地害了我弟弟性命呢?是我哭着喊着,将父母说活了心,由郭四往来穿说,人钱两交,那面付八百块钱,即刻派人将我接走,有家人仆妇将我护送到北京。我父亲此时救儿子心急,也顾不得许多,只要把钱付过来,怎样都能迁就。钱倒是如数给了,一刻也不等,便将我用车拉走。接我来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据她自己说,姓金,是北京某阔人宅里的女仆,宅里都称呼她为金妈妈,特特奉了主人之命,前来接姨太太,另外还有两名马弁,随着保镖。据金妈妈说,主人如何慈善,家中如何阔绰,因为年将半百,尚无子嗣,所以想娶一位如夫人,嫌北京的姑娘太好浮华,不如外省人规矩,曾当面托过郭四爷。因此郭四爷才出头管这事,也为的是一双两好,你们老夫妻只管放心,将来决受不着一点委屈。她是口若悬河,说得天花乱坠。我母亲虽然难过,也不能不放我走。自从那一天辞别了双亲以后,家中消息如何,简直连一个字也听不见了。及至到了北京,才知道是完全受骗,哪里有给人做妾的事,原来那个金妈妈,乃是北京一位著名的大养家儿(按:北京土语,凡买女子学唱为妓者,呼之为养家儿,又名领家儿)。她每年总要到各省去采买良家女子,偏偏这一次来至洛阳,就住在郭四家里,她早就看上了我,情愿出一千块钱买,始而郭四说不成,人家是书香体面根柢,岂能出卖女儿?也是活该我命中注定,偏偏出了我弟弟这一场祸事,郭四便乘隙而入,居然达到目的。金妈妈出了一千元身价,郭四使了二百。我来到北京,金妈妈便另换了一副面孔,对我说,你要好好帮我挣钱,我便拿你当亲女儿看待;你如果不听,轻者饿起你来,重者便打你一个皮开肉绽,你要仔细好了。可怜我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女子,经她这一吓,哪里还有抵抗余地,只得含羞忍辱,操这皮肉生涯。她因为我是中学毕过业的,便标出牌子去,什么中州才女,洛下名媛,胡吹一气。因此慕虚名而来的,终日车马盈门,生意总算十分旺盛。不足一年的工夫,我就替她挣了足有七八千元,她仍然不甚满意,说我太老实,不会敲客人的竹杠,不过面子上待我还算不错。只是昼夜防闲,不许我有一点自由,那金妈妈纡尊降贵,给我做一名贴身女仆。面子上我是她的主人,当着客人面,把姑娘敬得天神一般,小心伺候,连一口大气也不敢出。等客人走了,一转脸的工夫,她便拿出假母的威风来,从头发根直数到脚底板。我那胃气病,生生是她气出来的。今天她因为交运,听了瞎子的话,在屋里闷着不出来,怕见生人。要不然,早就跟着我一同来了。但是她本人虽不能来,却派了班子里一名女仆,一个跑厅的,四只眼监视着随我同来。张老爷有话,不许女仆跟进屋中,把他两个留在门房,所以我才敢对王将军说这一套。假如她们要在眼前,我连一个字也不敢说啊!”天宠听她从头至尾述说这一段历史,心中很动了无限感慨,说:“你舍身救弟,心眼儿总算好极了,将来结果一定也坏不了。不过你在这里坐的工夫太大了,就这样去回,保不定你那假母又要胡乱疑心。”一句话提醒了湘君,立刻柳眉紧蹙,发起愁来。其盛笑道:“这事好办,待我老张给你出一个主意吧。你不是有胃气病吗?就说在这里因为喝了两杯酒,忽然犯病,躺在床上起不来。王老爷劝你吃了两口烟,方才好一点,直躺到现在,才勉强挣扎起来,由王老爷坐马车陪你回去,我们大家也随了去,这样你的面子上十分圆满。不止可解除她的疑心,还可叫她十分高兴。你们想,我这法子总算面面俱圆吧。”大家鼓掌赞成,说这法子果然真好。湘君道:“好固然好。但怕王老爷未必肯这样做吧。”天宠道:“这有什么,只要你不受委屈,我陪你走一趟,是没要紧的事。”张万两人见天宠肯送湘君回春云班,真是意想不到的高兴。天宠自己本有一部马车,万呈祥又吩咐家人从马车行中叫了一部来,天宠湘君坐一辆,张、万,李三人坐一辆,风驰电掣地来到春云班。
此时鸨母金氏早已盼得眼穿,她曾三番两次派毛伙到万宅去打探,知道湘君尚在万宅,并未他去,心中略为放下。但是候之许久,仍不见来,她可真有点急了。说:“叫条子也不能把人留下啊!待我自己看看去。”她才要叫车子到万公馆,忽听外面人喊马嘶,跑厅的高声喊道:“张大人,万大人,还有诸位大人,送湘君姑娘回来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