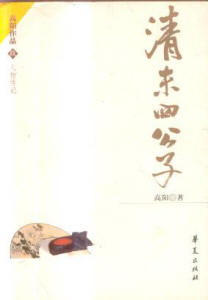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第38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等到今天吗?”见龙点点头,很佩服叶树芬忠实可靠,有许多话瞒着洪化虎的,反倒不瞒叶树芬。叶树芬也随时替他参赞一切,因此两个人的感情,比从前更加密切了。在见龙出院的前两天,他曾对树芬说:“我的病已经完全好了,用不着再住医院,我想明天同他们算清了账,就要迁回团部去了。”树芬说:“你还是多住几天的好,党里又没有什么重要事,何必忙在一时呢?”见龙说:“明天看吧,如果精神好,我就出院;精神不好,再歇几天也无妨。”叶树芬从当天起,对见龙的行踪,更格外注上意了。她以为见龙在医院中住了一个多月,关于革命的机密,当然不能进行。至于那些革命同志,也不见有一个人来访他。他此次出院,一定不肯先回本党,说不定到谁家里去。有什么秘密,这恰是侦探他的好机会,我不要错过了。第二天她一早就出来,在医院的左近寻了一座茶楼,一个人走上去,选了一间临街的雅座,沏了一壶龙井茶,隔着玻璃向下窥着。因为是在上午,茶楼非常清净,而且斜对着医院的门,看得更加清楚。此时医院门前,倒是很热闹,因为有许多看病的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直到十二点钟以后,方才显着清净。树芬有点饿了,叫茶博士叫来一碟三鲜包子,一碗鳝鱼面,自己慢条斯理地吃着,仍用眼光盯住了医院的门。包子才吃了一个,面只喝了两口汤,倏地立起身来,掏出一块钱给茶博士,说:“你先收着,回来再算账。”便匆匆地下楼要走,茶博士在后面喊道:“太太!你的点心还吃不吃啊?”树芬说不吃了。她出了茶楼的门,点手叫过一辆黄包车来,说:“方才从医院出来那一位年轻的先生,他雇车到哪里去了?”车夫说:“他到法国巡捕房去。”树芬说:“好好!你拉我在后面紧追他,只要离十几步远,千万别开过去。咱们按钟点算,每一个钟点给你四毛钱。”车夫说:“五毛!少了不拉。”树芬也不理他,跳上车去。车夫飞起两条腿来,好像刮风一般,就追下去了。追了不大工夫,便看见见龙的车子,在前面跑得飞快。树芬这辆车,只在后面远远地哨着。果然到法国巡捕局,见龙的车子停住不动了,树芬也叫车子打住,却把脸扭过去,由侧面窥看。见龙开了车钱,便一直走进去。树芬掏出五毛钱来,也将车夫开走。她又在左近寻了一个影身地方,瞪大了眼睛,倒看见龙同什么人出来,再到什么地方去。后来见他同白荣华一起出来,坐了局子里的马车,风驰电掣而去。树芬仍随在后边,直跟到离荣华家门还有一二十步远近,见车停了,两人携着手一同进去。
树芬此时心里完全明白了,因为她知道华自强在上海失败,藏匿在巡捕头白荣华家中,这是各报纸都登过的。树芬此时,知道见龙在暗中仍与平民党接近,他当然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主张,将来一定免不了有意外举动。那时连我的女婿区广,也免不了要受牵连。两害相权取其轻,说不得,只有牺牲见龙,也不能牺牲我的女婿啊!可怜见龙的运命,只在她这一转念间,便完全决定了。叶树芬同见龙始而确是同志,自从到北京后,她的女婿区广一再向她恳求,无论如何得帮助总统,保全我那秘书地位。要不然,不但官做不成,遇巧了还许变成嫌疑犯呢!因为警察总监吴必翔已经把这件事完全栽在我的身上,我想脱干净,都办不到了。叶树芬因女儿女婿哭着喊着地央求,自己有心答应了吧,实在对不住见龙;不答应吧,又怕将来对不起女儿女婿。始而是替见龙解释,说他那社会团并不含有危险性质,不过是注重下层民生,与平民党之谋夺政权者,迥乎不同。后来区广拿来许多侦探报告书给他岳母看,说你老人家一看这个就明白了,那些报告书上,说社会团发源于俄国的虚无党,完全是一种暗杀机关。该团内部人员,有数十之多,完全散布于京津间图谋暗杀,若不及早扑灭,前途不堪设想。该团副团长田见龙,现预备到上海运输爆力极大的炸弹,将来运至北京,在总统选举前便要起事云云。树芬一见这报告书,也不觉吓了一愣,说:“这些话是从哪儿说起呢,我终日在团部中,也没听见一点影子啊!至于见龙要到上海去,确是不假,他因为北京的侦探,对于他太注意了,连一点行动自由都没有,因此想到上海住几天,不过是为避避风头,并没有旁的意思,怎么能说他是运送炸弹呢?”区广道:“我的妈妈!您既知道他去上海不假,别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到而今,他已经成了中央注意的人犯,您还庇护他做什么?难道您这大年纪,将来还跟着他打官司,把老命送掉吗?那也太犯不上了!”她女儿在旁边也一再地说:“妈妈怎么越老越糊涂呢!您自己要把算盘打清了,我是您亲生的女儿。”又指着区广说:“他是您养老的姑爷,不要说这件事明显易见的,是他图谋不轨,丝毫也不冤枉他。就算是冤枉了他,保全您姑爷的功名,又成全了咱们母女永久的团聚,您也没有什么不合算的啊。”叶树芬究竟是一个女子,又兼她骨肉情重,被女儿女婿包围一说,她的初心便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说:“这样吧,明天我也赶到上海,在旁边监视见龙,倒看他有什么动作,我随时给你们来电报,你可千万严守秘密,不要叫外人知道一个字。”区广说:“这是自然,还用您嘱咐吗?”
第二天叶树芬赶到上海,同见龙会面,过了不几天,见龙身入医院,及至病愈出来,树芬在暗中监视他的行踪。见他到白荣华家中,自己不便在外边久候,先回社会团本部,注意见龙回来,携什么物件,有什么动作。直到掌灯多时,见龙回来了。树芬同他住对面的屋子,隔着窗户,正看见见龙手中,只提着一个皮包。心说见龙出院时候,手中任什么也没有,怎么忽然变出皮包来?再说见龙常提的皮包是黄颜色的,今天这皮包却是黑色,一定里面有什么危险物。看起来北京侦探的报告,还许不假呢。她一壁想着,跑到见龙屋中,装作很恳切的样子,说:“你高低还出院啦,多住两天有多么好,何必忙在一时呢?”见龙粗粗地敷衍她两句,便到洪化虎屋中去了。他认定树芬是自己人,连屋门也不锁。树芬故意将手帕遗落见龙屋中,随见龙出来,走了没有几步,说:“我的手帕忘在你屋中了。”返身回去到见龙屋里,先用眼瞧那皮包,皮包放在床底下了,树芬弯下腰去伸手一提,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这皮包死沉死沉的,分量真不在小处,连忙轻轻放下。拿起她的手帕来,匆匆走出,仍回她自己卧室去了。她反复地想,见龙的皮包中,一定有很厉害的危险物,我倒是报告不报告呢?如果报告,见龙的生命就要不保;要不报告呢,吴必翔一定说我女婿区广同他伙同一气,代为隐瞒,将来连我也脱不了干净。没有两全的法子,只好狠一狠心,给我女婿去电报吧。但是天到这时候,怎能再出去拍电报呢?岂不叫洪田两人生疑。如果今天不拍,倘然明天一早,见龙就邀我一同北上,那不更没有闲空了吗?她正在为难,见龙却来对她说:“我们后天一早搭轮北上。”树芬真是喜出望外,第二天神不知鬼不觉地,她就把密电拍到北京去了。可怜见龙还在鼓里蒙着,哪里知道一点影儿。幸而他格外存了一番细心,他想这次到京不比从前,从前未带危险物,不怕他翻,从前侦探不认识自己的面貌,如今这两种便利全都没有了,若不预先想一个万全的法子,只怕人没到北京,就被他们捕去了,还能替华自强办那一局事吗?没有旁的法子,只好化妆幻形,遮掩人的耳目吧。他罩上面具,戴上假须,居然变成五十多岁半老的模样,同叶树芬一齐上船。把姓名也改了,田字出头,改姓为由,叫作由梦云。船到塘沽,便有许多侦探包围检查,可怜一个贩绸缎的客人姓田,年纪就在三十上下,竟被侦探给带走了,硬说他是田见龙。见龙在一旁看着,又是生气,又是好笑,他的姓名模样全变了,当然没人注意。同叶树芬在栈房吃饭休息,然后一同乘车到天津,虽在老站下车,却不敢一直到报馆去寻国九经,仍然住在德义楼饭店。
等到夜静之时,两人一同去寻九经,九经认得叶树芬,却不认得这戴胡子的老先生。树芬给引见,说这位是咱们的老同志由梦云,代表田见龙北上。九经不敢怠慢,忙将两人让至密室,才要周旋,见龙握住了他的手,这只手顺着下额向上一撂,把假胡子假面具一齐撂下,哈哈大笑道:“九经兄,还认得小弟吗?”九经不觉愕然一怔,说:“原来就是你啊!你来得太凑巧了,金二哥才有电报到来,说你在三日内一准到津,到津之后,叫我把你拦住,千万不可进京。你既到了,只好先在天津住几天吧。”见龙道:“莫非北京分部有什么变动吗?”九经说:“变动倒是没有。不过谨慎一点,总没有过失吧。”见龙道:“无论如何,明天早车,我是要到北京去的。我既有这易形的法子,无论走到哪里,不现本来面目,他们又有什么主意能对付我呢?”九经摇头,说:“你是艺高人胆大。金二哥何等精细,他是久住北京的人,不但情形熟悉,而且耳目也格外的灵。他既说不叫你去,总是不去为是。”见龙一面将假面具戴好,一面对九经说:“你不要害怕,就是龙潭虎穴,我自信也没有什么危险。事不宜迟,明天早晨我一定进京,倒得看一看北京是什么情形。倘然有一个风吹草动,我便连夜赶回天津。常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照你们这样胆小,真要寸步难行了。”九经听他的语气,直然是一肚皮豪情胜概,便是金戈二在眼前,也未必能拦得住他,何况自己呢?只得先给他们预备酒饭。见龙吃了一个酒足饭饱,自己特特到六国饭店去寻曾荷楼。荷楼因为有病,已经入了日本医院。见龙又跑到医院,想要会见荷楼,却被院中给挡了驾,说曾先生的病,必须早眠早起。他此时已经安歇了。如果要看他,可于明日午后两点钟,是病人会见亲友的时刻,来了一定能见,今晚是做不到的。见龙碰了一个钉子,赌气也不再见他了。假如他能见着荷楼,荷楼深明北京情形,一定原原本本对他说,拦着不叫他去。或者他也许听荷楼的话,暂时停止在天津,可以逃开了杀身之祸,岂不很好。只因为见不着他,第二天便匆匆入京,结果只落得有去没有归路,阴错阳差,也要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吧。见龙仍回报馆,九经正同叶树芬闲谈。原来见龙出去访人,九经借这机会同叶树芬攀谈,说:“咱们这位副团长,太过于任性了。方才我对他说的话,确是为他个人安全。他不但不采纳,话里话外,反倒讥诮我胆小。叶先生您想,我们做朋友的有多么难啊!”树芬笑道:“国先生是一片热诚,见龙太年轻,他自恃血气之勇,当然有些听不进去。不过我看他长大的,深知道他的为人,很有临机应变之才。你只管放他进京,决然可以无虑。”九经点点头,说:“既然这样,我又何必拦他呢?”两人正在议论之间,见龙已走进来了,连说:“不巧不巧,曾先生没有见着,我们难道就坐着吗?寻个地方消遣消遣去吧。”九经道:“听落子馆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