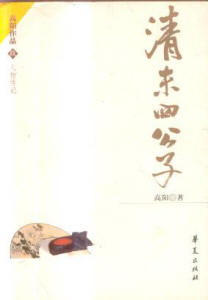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第34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客知应处,叫他们开条子,即刻派一部马车来,送陈小姐回寓。”紫艳应声去了。这里素娟直抹眼泪,向美珍道:“陈小姐,你为何请这许多日子假?我一天看不见你,心中就要想出病来,怎禁得十几天不见面,岂不要把我想死了吗!”周女士同美珍全都笑了,说:“傻丫头,你真会说呆话,十几天一转眼就过去,我们相聚的日子长得很啦!何争这一时呢?”周女士又乘势打趣她,说:“你同陈小姐这样好,将来陈小姐出阁时候,我把你送给她做陪嫁丫鬟,你看好不好呢?”几句话把素娟也招笑了,说:“周师爷,你老人家向来不说玩笑话,怎么今天也拿我们开心呢?我实在是舍不得陈小姐。她天天讲些海外的故事给我们听,比听《红楼梦》《镜花缘》还有趣味呢。”美珍道:“你盼我早早好了,我便早早来,给你们讲故事听。”三人正说着话,紫艳已经回来了,向周女士回:“马车已经开到门外,陈小姐什么时候走全可以的。”美珍强挣扎着要下床,说:“我这就走,晚了恐怕再犯病。”素娟扶着她,紫艳替她扎好了裙子,扣好了外衣的纽袢。然后两人一边一个,架着她出了卧房。她临行时,向周女士深深鞠躬致谢,又紧紧握了周女士的手,说:“一切都拜托先生了,祝你前途无限,咱们相聚的日子很长呢!”周女士也再嘱咐她:“珍重养病,这里多请几天假是无妨的。”又一直送她到第一层房门外。马车就在门前停着,车夫在一旁躬身侍立,敬候小姐上车。素娟同紫艳,一边一个,把她搀上马车。素娟还拿了自己的一条锦被,蒙在她的身上,恐怕早晨天凉,沿路上受了风。又再再地说:“陈小姐病好了,早早销假,别叫我们长久地盼望着。”美珍向大家拱手,说:“我一定很快回来,不劳你们盼望。”周女士带着素娟、紫艳,这才回到自己屋里。
车夫一摇鞭子,蹄声“嘚嘚”,从府里的旁门赶出来。出顺治门,向骡马市大街丞相胡同走来。因为美珍的私寓,就在这个胡同里。她是住在她姨母家里,后来她嫌不方便,便在她姨家隔壁租了一所房子。她从南方带来一个随身的丫鬟,名叫鹦哥。到京以后,又把她小时候的乳母也叫来了。她的乳母祥妈妈是北京旗人,自她落生时候便雇了来哺乳她,一直乳她五年。后来不吃乳了,仍然在她宅专伺候美珍。及至美珍的父亲亡故,家人回南之时,本想带她一同走,她因为舍不得自己的女儿,这才作罢。此刻美珍来京,便先去看望她的乳母。祥妈妈见她出息得长身玉立,上下西装,变成了一位洋小姐。错非她自己道姓名,简直就不认得了,摩挲着老眼,喜欢得不知如何是好,拉了她的手,叫一声:“小姐!”又叫一声:“干女儿!你可想煞我了。”老眼中止不住扑簌簌地直往下落泪。美珍也直叫:“干娘,你老人家,还是这样康健。”祥妈妈又笑了,说:“傻孩子,我们这命小福薄的人,要再不硬硬朗朗的,更该着饿死了。你干哥哥当巡警,每月只有七八块钱的饷。我同你嫂子,也能浆,也能洗,也能缝连补做,每月帮着他们,过这份穷日子。再想老爷在时,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只怕今生今世,做梦也梦不到了。”美珍听她说得这样可怜,便点了二十元钞票,说:“这是给干娘买点心吃的,您收下吧。”祥妈妈接过去,千恩万谢,说:“难得我有这样一位干女儿,直比我那不济的儿子还强得多呢!”美珍乘势便撺掇她,还同自己住在一处。祥妈妈也很乐意,这才租了丞相胡同的房子。到底是乳母关切美珍的饮食起居,自有祥妈妈照应着,觉得舒服了许多。本来旗人全都善于调和五味,也不必用厨子。她一个人早晚做饭,美珍吃着也很适口。
这一天,美珍到总统府去贺喜,临行嘱咐祥妈妈:“不必等候我吃饭。”哪知到了晚间,她仍然不回来。祥妈妈很觉着不放心,直给她等了一宵的门。鹦哥早去睡了,自己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直到天亮,太阳出来,才合上眼矇眬要睡。外边门响,赶紧出来开门。见美珍坐着马车回来,车夫对祥妈妈说:“小姐病了,您快搀着下车吧。”这一句把祥妈妈吓了一跳,忙跑过去亲手拧开车门,瞪着老眼直盯美珍面上,问道:“我的小姐,你怎么病在外边了呢,倒是什么病啊?”美珍道:“干娘先不要问,您搀我到屋里再说吧。”祥妈妈忙伸手轻轻地把她搀出来,一步一步地扶着,把她扶到上房卧室中坐下。美珍坐定之后,便从票夹中取出一张十元钞票来,递给祥妈妈,说:“您把这票子赏给赶马车的,那一床锦被,便托他捎回,还给素娟姑娘。”祥妈妈接过票子来,却有点犯踌躇,说:“我的小姐,你怎么赏这么多钱!要雇马车也够雇出十辆来了。”美珍笑道:“干娘,你知道这马车是哪里的?这是大总统府自用的马车,在别人赏十块钱,他还嫌少呢,您快给他去吧。”祥妈妈听说是总统府的车,知道美珍昨夜必是住在那里,连忙把钱送出去,照着美珍的话对车夫说了。车夫说了一声“谢谢!”便赶着车仍回公府去了。
这里祥妈妈三步并两步地跑进来,拉了美珍的手,说:“小姐,你怎么病得这样快,害得我一宵也不曾睡好。有心到总统府去打听,我又不认得道儿,难得你回来了。请哪个大夫看,我快给你请去,可不要耽误了啊!”美珍道:“我这病不用请大夫,是一时急火上攻,竟致昏晕过去,过一两天自然会好的,吃药也不管事。”祥妈妈很诧异地说:“你为什么事着这大的急啊!”美珍道:“咳!不要说了,昨天在总统府席上,遇着一位女朋友。她是才从天津来的,给我带一个口信,说我母亲上北方来了。因为有一个南洋华侨当选国会议员,同我叔叔是把兄弟,他到我叔叔家辞行,我母亲一定要随他到北方来看看女儿,因此匆匆地同船而来,也没给我写信。不料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长发栈中,第二天就病倒了,并且病势还十分沉重。某议员又因有事绊着,不能即刻到京,所以托付了我那女朋友,给我带一个口信,叫我即刻到天津去。我昨天听见这信,当时便急昏,一脚跌倒,幸亏周先生把我扶到她的卧室,用姜汤把我灌救过来。我本想昨天便到天津去,怎奈四肢无力,实在动弹不了。今天晚车,无论如何我是一定要走的。好在有鹦哥随着伺候我,就请干娘先替我看几天家,等我母亲病好了,我们三人一同到北京来。那时我先给您来信,您好到车站接我们。”祥妈妈听了,也很着急地说:“太太既病在天津,你当然得去看看。但是你的病还没大好,再一受奔波,岂不要更加重吗!要不然,我也随你一同到天津,一者看看太太的病,二者你路上倘然有些参差,我也好随时照应,但不知你意思怎样?”美珍一想,这个老妈妈待我如亲生女儿一般,我无论走到何处,有她在旁边照应着,实在是难得的一个亲人。想到这里,便慨然应允,带她一同到天津。三个人赶紧收拾了收拾,只带两只软箱,两个皮包,其余粗笨家具,一概不带。临行之时也不知会她姨家,只把房东叫来,说:“我们到天津看病人。”房东因为人家不欠房租,当然无可留难,说:“陈小姐请便,我替你看守几天房子,算不得什么。”美珍带着奶母丫鬟,直奔车站。因为避人眼目,全打的是三等票。站上虽有侦探,见是三个妇女,还夹着一个病人,便毫不注意地放她们走了。
美珍走后,只有周文锦心中总是忐忑不定。她自己想,电报虽烧了,然而那杆盒枪仍放在自己柜中,依然不妥,我必须把它消灭了,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消灭在什么地方呢?想了多时,忽然灵机一动,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一天晚间,恰赶上天气极热,她一个人偷偷把手枪放在衣袋中,对两个侍女说:“我到南海边上乘凉,少时就回来。”她住的柳香院,背后便是南海。海边上有现成的沙发,她坐下东张西望,见前后左右并没有一个人,心说:这是天假之缘。她站起来独行了几步,拣那水势较深的地方,把手枪取出,早用手帕裹好,自己蹲下身去,假装拾什么东西,向水中轻轻一甩,甩出有一丈多远,扑通一声,坠在波心,立刻水中起了一个圆圈,被月光照得非常清楚。自己心中也不觉扑通扑通地跳起来,没敢耽搁,便匆匆回房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还不曾上班,府中的侍从武官长印长,便派人来知会周师爷,说:“少时陈美珍参议来了,请知会我们,有重要公事同她面谈。”周女士吓了一跳,忙说:“陈参议因病请假,已经三天不曾来了。”她虽把来人支走,心里却觉着害怕。正在这时候,总统的九公子忽然跑来,向周女士报告,说:“总统传谕,叫扣起陈美珍来,您看这事怪不怪?”周女士借此机会,忙向他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周女士的学生,师生的感情又最好。周女士问到他,他便据实地告诉说:“今天早晨,总统接到上海镇守使郑尔成一封电报。自看见这封电报,脸上气色很不喜欢,停了一刻,就写出那一道手谕来,一面又传警察总监吴必翔,执法处长云雷。这时候他们全来了,我快看看去,到底听他们说些什么,我再回来报告给先生。”周女士至再嘱咐他:“千万不要对总统说我打听这件事。”九公子答应着就跑了。
此时不先不后,吴、云两人都来到了。传宣官一直把他们领到总统办公室,二人进来先向总统鞠躬。看总统脸上的气色很有愠怒之意,全都吓得不敢坐下,好像笔管似的,立在总统身旁,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总统左顾右盼的,每人看了他们一眼,气哼哼地说道:“有话坐下说吧。”两人这才告坐,欠着身子,把屁股略挨在椅子边上,同唱戏的虚坐差不多,真是受罪极了。总统未曾开谈,先冷笑了一声,说:“你两人职司警备,关系北京全部治安,责任是何等重大。你们手下养的侦探成千累百,他们每人全吃着很大的钱粮,不是叫他们预防奸宄、消弭反侧吗!如今革命党遍布北京,上回社会团的事,你们始终并没办出一点头绪来,如今连我这公府中也发现了革命党,你们还在睡里梦中。似这样溺职,真是太说不下去了!难道说你们豢养的侦探,除去吃饭拿钱之外再没有第二样本事吗!”总统劈头盖脸地教训了一顿。两个人哪里还坐得住,不约而同地全立起身来。吴必翔吓得身子乱颤,哪里还答得上一句话来。云雷究竟是武人出身,胆子比较大些,他便低声下气地回道:“卑弁受大总统厚恩,不能尽职,实在罪该万死。但不知总统所谕的本府之内竟有了革命党,这个革命党究竟是何人,还求总统的明白吩示。”项子城听他这样问,不觉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难得你脸皮真厚,反倒问到我头上来,你看一看这个电报。”说罢把上海拍来已经译过的密电,随手掷与云雷,说:“你看这个就知道了。”云雷如同奉到圣旨似的,战战兢兢把电报捧着,仔细看了一遍,吴必翔也立起身来,站在一旁侧目而观。他本是一个文人,一过眼就明白了。云雷还在捧着一再地读。总统也笑了,说:“笨人,看一张电报也值得这样费劲。”云雷被这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