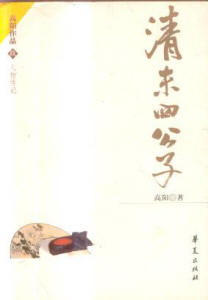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第1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显堂吃饭,大家乐得扰他一顿。连唱戏的带玩票的,一共也有三四十人。在宗显堂这一吃饭,便彰明较著,全知道兴大爷收了朱少爷做义儿干殿下。
也是活该凑巧,他们吃过饭走后,紧跟着恩王府长史海亮,也同着七八个人来这里吃饭。跑堂的小王嘴快,便对他说,二爷来得不凑巧,早来一步,大爷正在这里吃饭呢!海亮忙问道:“大爷同谁在这里吃饭?”小王笑道:“怎么这大的喜事,二爷全不知道?”海亮忙又追问什么喜事?小王道:“大爷认干儿子,认的是朱大帅的少爷,今天才磕的头,同着谭老板一干人在这里吃喜酒。这样天大喜事,二爷怎么不知道呢?”海亮听了,心中一动,便随口答道:“我当什么要紧的事,原来是为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大爷的干儿子,车载斗量,这有什么稀罕的。”说着便同一干人坐下吃饭。吃过饭,大家约他游逛,他说府里有事,还得进城呢。
海亮回至府中,问值日的:“大爷可曾回来吗?”值日的回说,尚未回来。海亮又问:“老王爷在什么地方?”值日的说:“老王爷现在花园里荷亭上,同二福晋斗蟋蟀呢。”海亮听了,忙吩咐快把我昨天带来的朱砂头,预备在手下,我这就到花园去。左右答应一声,即刻将一个赵子玉蛐蛐盆儿放在眼前。海亮揭开看了看,便自己提着到花园来,先叫小太监上去回明。恩王传谕叫他到亭子上来。海亮上了荷亭,先朝王爷、福晋请过安,说奴才今天得了一头上好的虫儿,特来送给老王爷助兴。恩王尚未答言,二福晋先笑道:“你送给他不成,必得要送给我的。我的虫儿已经败了两头了,有你这一支生力军,我也好捞捞本儿。”海亮道:“反正爷同福晋,不拘谁要全是一样。”说着将盆儿放在桌上。恩王抢着揭开看了看,哈哈大笑道:“我当是什么出色的虫儿,原来是一个红头子。这种虫儿,中看不中用,白给我也不要。”二福晋过来看了看,说:“你不要我要,咱们立时便斗一斗看。我想你那大黑,一定不是他的对手。”恩王哼了一声,说:“好!斗上看吧!”二福晋道:“这一次不能白斗,得大大地赌一注财。”恩王道:“你想赌什么呢?”福晋道:“八月节朱宝田汇来的两万元节敬,我叫上到我的折子上,你一定不肯。如今就赌它吧。如果红头子赢了,这笔款便拨给我,你看怎么样?”恩王笑道:“红头子要输了,你给我什么呢?”二福晋道:“输了这算你的,我不要了。”恩王大笑道:“好公道的赌博,就是这样吧。横竖你也赢不了,乐得叫你死心塌地,省得再惦着了。”说罢将大黑拿过来,同红头子放在一个盆里。海亮在旁边看着,见两个虫儿大小差不多,全在八厘上下。红头子身略小一点,可是头颅却比大黑又宽又大。两个放在盆中,立时斗起来。大黑牙钳是黄的,红头钳却是紫的。恩王上了年纪,眼不得力,忙戴上花镜看。一见红头的牙,不觉失声叫道:“哎呀,我上当了!”他这句话才说完,大黑已经被红头咬在底下,只用六条腿乱蹬。哪里蹬得开,少时勉强翻过来,已经垂翅而逃,被红头赶出盆去。里面的红头,却鼓翅长鸣,十分得意。恩王道:“老了,眼睛不中用了!我要早看出是紫牙来,决计不同他斗的。从来朱砂头,全是黄牙,紫牙的百不得一,这就难怪输了。”二福晋此时得意极了,说:“你不要管他黄牙、紫牙,两万块横竖得归我了。”恩王道:“你们妇人家,就知道爱钱。你要知道这两万块钱,不是容易拿的,这是他做巡抚的保险费。摄政王爷同皇太后,哪时要问到他,我得撒谎调皮,替他说许多好话。你如果拿了去,我就不管了,以后摄政王爷再问到他,你上去回话吧。”
二福晋尚未答言,海亮抢着说道:“依奴才看,爷为这两万块钱,大可不必卖这气力了。”恩王道:“这叫什么话呢!常言说得好,使人钱财,与人消灾。哪有白要人两万块钱,到时候连一句好话不说的呢!”海亮道:“爷认着他是诚心敬意孝敬爷一个人吗?”恩王道:“这是自然,要不他肯出这么多钱吗?”海亮微笑了一笑道:“他还有大靠山呢,孝敬的数儿,比爷加一倍还不止。奴才今天无心中听见人说,想禀报给爷知道,又怕爷生气;不说吧,爷叫他蒙哄一辈子,还不明白呢!”恩王听了很诧异地说道:“他的大靠山是项老四,已经倒了。还有哪个大靠山呢?要比孝敬我还加两倍,他这吉林巡抚,能出产多少呢?”海亮道:“奴才今天会着麦加利银行大班,据他说,今年八月节,吉林抚署净给庄中堂一个人,就汇了五万银元。奴才假装糊涂,问朱抚台同庄中堂怎么这样近呢?大班告我说,庄中堂是朱抚台的老师,去年中堂买了一块坟地,今年大兴土木,栽树盖房,所以朱抚台孝敬这许多钱,是专为老师建筑坟山之用。奴才也曾问他,那吉林每年有多大出息?这大班是山东人,他在东三省经商多年,所以知道得十分详细。据他说,吉林在东三省是第一的富省,较比奉天还强得多呢!因为吉林幅员既广,出产尤多,只森林一项,每年就有好几千万。至于矿产、渔业、参茸种种,更是不计其数。无论哪宗哪项,全是抚台分头一份儿。据说这个缺,在全国巡抚中要算第一呢。他拿那五万块钱,不过是九牛一毛,算不得什么。爷如今得他两万块,还要替他说好话,这也未免太便宜他了。”海亮这一席话,气得老恩王直吹胡子骂道:“混账东西,我还拿他当好人呢!他看着庄中堂可靠,我偏叫他靠不上。不要忙,早晚总叫他知道我的厉害。”海亮道:“爷不用生气。这件事据奴才看,倒不可一次将他打倒。莫如先小小地使一点手法,叫他明白明白。他如果醒腔,急速打点,咱爷儿们倒可以大大地敲他一笔。”恩王点头,说你的话很对,早晚我自有办法。此时二福晋见王爷生气,也不向他要两万块钱了。又谈了几句闲话,海亮退下去。过了没有几天,也活该是冤家路窄,偏偏赶上宋耳顺召见,三言五语,打倒了一个丁大声,抬起了一个祥呈。二人一起一落,便连带着牵出一个朱宝田,又成就了一个陈明伦。老恩王借题发挥,总算如了志愿。其实,全是海亮一个人作祟。
自从这几道旨意颁布下来,最难过的就是庄中堂,一肚皮气说不出来,回到自己宅中,越想越不是滋味。别的倒还罢了,只有朱宝田由繁调简,心里觉着很对不住人。但是木已成舟,如何能挽回得来。左思右想,只好先派人将朱丝请来,向他解释一番,也好盖一盖羞脸。主意打定,立时派小厮二有到朱宅去请。二有回来,说朱少爷回禀中堂,今天因有要紧事,实在不得工夫。明天晚间,一定过来请安。庄中堂听了,心里很不自在的,说:“往常我派人去叫他,全是随叫随来,怎么今天忽然端起架子来!哦,我明白了,这必是因为他父亲调缺,看我不能维持,所以改了态度,不把我放在眼内。我叫他,他居然敢抗命不来,这个小孩子,也未免太浅了。别的不说,你父亲同我既有师生关系,你是一个小门生,对于太老师的命令,难道就敢不遵吗?”庄中堂是越想越气,一夜也不曾合眼。到第二天,便请假不曾上朝。原想休息两三天,自然就平复了。却没料到,第二天又惹了一场大气。
你道因为什么呢?原来项子城自从开缺回籍,他那长公子可敬,本想随他父亲一同回去,项子城却不许。说:“你现在商部做参议,也算一个小小的堂官。再熬三二年,便有侍郎的希望。为什么要辞官呢?再说我此次开缺,无形中已经变成了罪人,你如果辞官,也随着我回家,叫朝廷看着,仿佛咱爷儿俩有心同皇上家制气。这种疑似之间,关系很大。我正在倒霉时候,你谨慎着点,不要再给我种毒了。”可敬听他父亲这样说,只好仍住北京,照旧当他商部的差使。转眼过了一年多,照资格论,他应当升右丞了。怎奈官情如纸薄,人在人情在,项子城既去位下野,他的儿子当然没人肯照应了。此时商部尚书溥伦,是一个天潢贵胄、纨绔子弟,除去吃喝嫖赌唱二黄之外,并没有旁的本事。摄政王因为兴贝子的声气太坏,不好意思再叫他做商部尚书了,所以才选着这个宝贝。居然挂上尚书的头衔,一面还充着咨政院院长,仿佛他是神圣万能。这位先生,便也居之不疑。他到了商部之后,便想把项可敬免职。因为同项子城,平日很有嫌隙,一朝权在手,便想令来行。哪知老恩王知道这个风声,很不以为然,立时将溥伦叫到府里来,大申饬了一顿。说:“你一个小孩家知道什么!才做了官,就想作福作威,寻仇报复,那还了得吗!项老四虽然退职下野,我们对于他的后人,更应当格外照应,才不失同寅的义气。你为何硬要免他儿子的官?也未免太浅露了。我劝你趁早儿将这念头打消!如果不然,你今天免了项可敬的官,我明天便免你的官,你可不要后悔。”溥伦挨了这一顿申饬,只得忍气吞声,从此罢手。项可敬的参议才算保全住了。到底要再想升官,是很不容易的。他从前,原随着项子城住在东城。后来子城回河南,连本宅的家具全拍卖了完账,他只得搬到西城去住,同庄中堂的宅子相离不甚远。
这一天也是活该有事。项可敬早晨吃罢点心,吩咐套车上衙门。车夫大柳将马车套好,他跳上去,一摇鞭子便出了胡同口儿。本来他住家离工商部不甚远,出了胡同才要向北走,偏巧有一家广货店,当天开张。正在这时候,大祭财神,鞭炮齐鸣,外夹着还有双响儿。项宅的这一匹马是才买的,野性尚未脱净。如今忽然听见鞭炮响,将两个耳朵向上竖起,撒开腿好像箭头一般,直向前没命地跑起来。车夫无论怎样吆喝拉缰绳,也收不住了。恰巧迎面来了一辆洋车,因为躲闪不及,被马车撞翻。洋车也摔散了,坐车的同拉车的,也都摔伤了。这时候迎上两个警察来,将马车截住。马停住了脚,项可敬连忙亲自下来,过去看那摔伤的人情形如何。幸而全不甚重,坐车的只戳坏了手,将手上皮擦掉一块;拉车的磕伤了腿,站不起来。项可敬便对警察说:“老总,你可将他二位雇车送至医院,应当花多少钱的医药费,可向我宅里去取;这洋车子也可就近收拾收拾,应当用多少钱也由我给;我并且格外赏拉车的十块钱。你二位费心办一办吧,我还急等着上衙门呢。”内中一个警察,向可敬看了看,问道:“阁下姓什么?在哪衙门当差?”可敬忙掏出一个洋纸小名片来,交给警察。警察看了看,才要照着可敬的话办理,偏巧车夫大柳多嘴多舌,想用势力压人,便插话道:“这是项宫保的大少爷,你们难道不认得吗?我们少爷太好性儿了,像这样赏他两块钱就完了,还费这许多事做什么!”可敬听他这样说,才要申饬他两句,忽见坐车的那人跳起来,指着可敬骂道:“我当你是什么东西!敢在大道上横冲直撞。原来你就是国贼操莽的儿子,倚着你爹的势力,满街上闯丧招骂。今天撞到我姓智的手里,咱们是势不两立,非手拉着手到警厅去不可!”可敬同两个警察,骤然听他这无理的话,也都愕然不解。可敬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