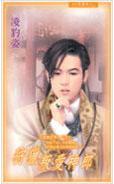欢喜郎-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还是想哭,眼圈儿红了,泪珠儿也像断了线的珍珠,一下子就弄湿了小脸蛋。
子丹深呼吸,胸口奇异地闷痛翻搅着,急急撩起袖子笨拙地擦掉她的泪水,绝望地低吼:“别哭了……妳……妳再哭……我就……就……”
她哭得更大声了,“事到如今你还要吼我?!”
“我没有吼妳……”他真的手足无措了,一个大男人,堂堂征北将军、定北侯爷被一个小女子的眼泪搅得束手无策。
宝兔一点都不得意,她真的觉得自己好笨、好可怜、好委屈,“我又不是不答应你,鸣……人家只是不知道要留在这里多久……人家只是多问了几句,你就对我这么凶……”
他心疼地拥她人民,口齿不清地自责,“我才是笨蛋……是坏人,好不好?我答应妳,不凶妳,以后绝不莫名其妙就凶妳了,好不好?”
她抽抽噎噎,泪水这才勉强止住,红着鼻头和眼睛,泪汪汪地问:“真的吗?那你几时要放我走?”
子丹凝视着她,猛一咬牙,“三涸月!三个月之后我必定遵守诺言让妳离开!”
她的心没来由地一揪,小睑苍白,小心翼翼地露出了一个勉强称作是笑容的笑容,“真的?”
他点头,闭了闭眼睛。
“好。”她习惯性地把满脸涕泪又擦在他胸前的布料上,这才笑得自然些了,“那你几时可以给我看碧珑?”
子丹睁开眼,定定地瞅着宝免,目不转睛,“三个月,三个月后,我让妳把碧珑……和妳自己一起带走。”
三个月后,他会给她一块精雕而成的美玉,也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戒掉“她“,这个一不注意就上了瘾的可怕习惯。
三个月后,侨归侨、路归路,他凤子丹依旧谈笑风生、洒脱如昔,这个突然出现的丫头绝对不可能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三个月……
宝兔蜷缩在他胸前双臂里,彷佛一切再自然不过,彷佛他就是她的主人……
三个月,三个月后她就可以顺利拿到碧珑完成任务了,虽然拖了一些时日,但是嫦娥仙子应当会见谅的吧?
金兔、银兔呢?她们届时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吗?
本能地依恋在他怀里,宝兔不愿意去倾听心底深处那个小小的声音——
三个月后,妳真能离开他吗?
实兔抱着一坛子各式细致宫点,吃得好不开心。
留在这定北侯府里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点心可以放胆大吃,而且样样都美味得紧呢!
她翻出了一个仿牡丹花样的杏子酥,张大小嘴,轻轻地放了进去……嗯,入口即化,香香甜甜的杏子馅儿随着外层的酥皮层层融化,好吃极了。
有得吃、有得睡……她实在是太幸福了!
说不定她在当兔子前是只小猪投生的,所以当了兔子仙以后还是难改猪性吧?
宝兔吃着吃着,突然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凤公子就是留她下来消耗掉他们家粮食的吗?
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他每次都是来看看她,和她斗斗嘴,再不就是把她抱在腿上玩偷尝她嘴唇儿的游戏。
她实在愈来愈迷糊了。
不过不知道金兔、银兔她们找到了其它两块定情物了没?
一想到这个,实兔急急忙忙丢下瓷坛子,盘腿而坐,手拈莲花指,闭目行起法术来。
“咕噜、咕噜、萝卜、萝卜……”她努力搜寻着其它两只兔子的消息。
可脑袋空空,眼前茫茫……她什么都弄不清楚,法力又严重失灵了。
实兔颓然地放下手来,有点疲惫,“都怪我,平时不多练练法术,现在可好了吧?”
她苦恼地支着下巴,这下子也没心思吃东西了。
她好想念金兔、银免和仙子啊!
就在她发呆的时候,青丝绾成高髻,别上朵朵红宝石、祖母绿镶成的花儿,身穿嫣红色宫装的燕奴轻轻巧巧、婀娜多姿地走了进来。
没有带任何随行婢女,燕奴依旧贵气袭人,一身盛艳。
实兔正发呆,浑然未觉她的来到。
“妳是谁?”燕奴好不容易摆脱了厅里众人,单独来到清秀小楼,当下不啰唆地兴师问罪。
宝兔傻呼呼地看着她,“妳又是谁?”
“妳没有资格问我。”燕奴精心描绘的黛眉一撩,冷冷地斥道:“我要妳立刻离开凤府,滚得愈远愈好。”
这句话可真是说进了她的心坎里,她也很想走哇,可那个恶霸就是不肯让她走。
宝兔叹了口气,真挚地开口,“这位姊姊,不如妳好心些,帮我求求凤公子让我离开好不好?”
她是说得很真心,可听进燕奴耳里却分外不是滋味,还以为她蓄意挑衅,不禁气得火冒三丈。
“我从未见过像妳这么不知羞耻的女人,妳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燕奴恨恨地说,“妳是不是笃定以后一定可以成为定北侯夫人?让我告诉妳,妳死心吧,就算他娶了妳,他心里爱的人永远是我!”
虽然她罗敷有夫,子丹也还在生她的气,可是她有把握,只要解决了种种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子丹一定会再回到她身边的。
到时候虽然她从安乐王妃降一级,成为侯爷夫人,但是宁可在有钱有权又英俊无匹的子丹身畔,也好过那个无权无势、只守着一份祖宗封邑吃穿用度的龙乐安!
眼前她最最危急的敌人就是这个小女孩。
燕奴紧紧盯着她像这种说胸没胸、说臀没臀的小女孩,子丹怎么会喜欢呢?不不不,子丹一定是故意要激起她的嫉妒,才会把这个女孩儿带回定北侯府的。
人人都知道他威名远播,有多少美貌仕女主动投怀送抱,他都看不上眼了,又怎么会看上这个绿豆似的人儿?
宝兔纳闷地瞧着她,不明白她美丽的容颜因何扭曲变形?还有,她怎么有些面熟呢?
她抓了抓头,突然想起来了,失声叫道:“我知道妳是谁了!妳就是凤公子的表嫂,那个拋弃他嫁给他表兄的姑娘!”
燕奴脸色一变,“谁告诉妳的?”
“凤公子告诉我的,妳忘了吗?那一天我们也见过的,“她不好意思地抓抓头,“我不是存心要偷听你们谈话的,对不起喔!”
她就是凤公子的心上人……
宝兔突然意识到这个事实,心头没来由地起了一阵怪异的闷躁感。
凤公子该不会就是因为心爱女子变成别人的妻子,一时心性大变,所以才会想要随便抓一个替死鬼来出出气吧?
那她不是很随便吗?
燕奴瞪着她,尖声叫道:“妳还偷听到了什么?”
宝兔凝视她,蓦然觉得她也很可怜。”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你们好可怜哪!”
燕奴受不了她故作同情的眸光,偏激地想着——这丫头莫不是故意讽刺她的吧?她以为现在胜券在握,就可以用一副胜利者同情失败者的嘴脸对待她了吗?
门儿都没有!
愤怒、惊疑交错,燕奴想也不想举起手来狠狠甩了宝免一巴掌。
“我不需要妳来可怜我!”她尖锐地叫道。
好痛!
实兔生平第一次被掴,她捂住火辣辣的脸庞,傻眼了。
燕奴面目狰狞如罗剎,“我和子丹的事,妳怎么会明白?别一副假惺惺的样子了,我知道妳根本就是想要抢子丹,对不对?”
“妳误会了。”宝兔没有生气,她只是觉得震惊和难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呢?
“误会?”燕奴冷笑,“不管是不是误会,我警告妳,识相的话快点走,要不然我会让妳吃不完兜着走。”
“姑娘,妳真的误会了,凤公子亲口对我说过,他心底只有妳一个人,而且他很痛苦,假意对妳冷淡都是因为妳已经嫁给他表兄的缘故。”实兔拚命解释。
可是她愈解释心愈发酸,真不知是为了什么……那胸口真痛呵!
燕奴嘴唇白了白,脸颊立刻红了起来,“妳骗我。”
她再叹了口气,难过地说:“我骗妳有什么好处呢?”
她说的是实话呀!
燕奴的心翩翩飞舞了起来,整个人像是醉倒在春风里一般。
“他果然是喜欢我的,果然没有忘了我。”燕奴娇呼欢然地捧住了心口,不可思议地甜蜜了起来。
嘴硬的他在她面前看似狠心,其实他心底还是没法子忘掉她的。
她就知道!
就在燕奴沾沾自喜的时候,宝兔心头却有说不出的闷塞酸涩感,她苍白着睑,手心轻轻地摩挲着红肿滚烫的脸颊。
白挨了一掌,她也真够倒霉的了。
不过能成全两个有情人彼此的一片痴心,她挨这一掌应该也是有价值的吧?只是为什么她此刻胸口好疼呢?
“我警告妳,“燕奴欢喜过后,不忘痛踩她几脚。”如此一来,妳该当知道我在子丹心目中有多重要了吧?妳千万别妄想取而代之,只要是我燕奴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会拿回来!”
“凤公子不是柬西。”她听来好刺耳,忍不住抗议,“他是个人,一个喜欢妳的男人,妳怎么可以把他形容得像个……像个……”
“妳又多嘴了,“燕奴高傲地睨着她,冷冷地嗤道:“我暂且饶过妳一回,如果让我知道妳在子丹面前卖弄风情,我发誓一定会杀了妳。”
宝兔嘴巴差点阖不拢——被她给吓呆了。
杀人?!杀人?!事情几时变得这般严重?
就在这时,龙乐安无声地走了进来,好象怕吵到人似的,轻轻唤着:“爱妻?爱妻?”
燕奴脸上浮起了一层厌恶、痛恨之色,勉强戴上虚伪的面具,娇滴滴地回道:“王爷,我在这儿。”
宝兔惊异地看着变脸比变天还快的她,尚未从这精采的面部表情表演中醒来,龙乐安已经来到她们俩跟前了。
他身穿枣色蟒袍,发上箍着一顶镶金玉冠,看起来虽然稍嫌单薄了些,却也自有股皇家优雅的气韵。
宝兔讶然地打量他,“你是……”
乐安希罕地回视,“我是龙乐安,乃是燕奴的夫婿,妳呢?小姑娘。”
“我?我是……凤府的丫头。”她郑重地点了点头,“嗯,没错,我就是凤府的丫头。”
“原来如此,妳知道少爷到哪里去了吗?”他还是很温煦地问。
“很对不住,他今日还没来,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她老实回答。
乐安笑了,“原来如此。爱妻,既然表弟不在,我们改日再来吧!”
燕奴不给好睑色,淡淡地说:“王爷先回去吧,我还不倦,还想寻姨母说两句话。”
乐安眼眸再次闪过一丝火光,随即一敛,恢复了笑容可掬,“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待会儿再让他们护送妳回去。”
她僵硬地点点头。
“小姑娘,我先走了。”乐安亲切地对宝兔一笑。
宝兔点点头,说也奇怪,她又同情起这个安乐王爷来了。
这三个人……都有可怜之处,心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在一起的又不爱自己……呼,凡间男女的情爱纠葛果然复杂,非她这只兔子精所能理解得的。
燕奴下巴抬高,很高傲地左瞄瞄、右瞧瞧之后,没有发现任何子丹曾在这屋里睡过的蛛丝马迹,这才满意地横了宝兔一眼,转身离开。
在离开之前还不忘拋下一句恫喝——
“记住!子丹是我的,妳胆敢打他的主意,我是不会放过妳的!”她的口气恶毒阴森。
宝兔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直到燕奴离开之后,宝兔才颓然地坐倒在椅子上,捂着“砰砰“狂跳的心脏喘气。
凡入实在太恐怖了,不行了、不行了,三个月后她一定得拿到碧珑,赶紧回宫交差,早早跟这一团是非脱离关系。
她模着被打的那一边睑蛋,边咕哝:“唉!这么娇滴滴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