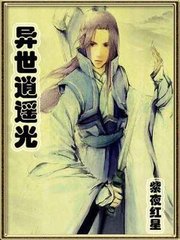宫闱乱:逍遥帝妃-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上去,无需陪着我在这里躺着。”看着曹渊将自己紧紧搂在怀中,陪着自己在这冰冷的池子里,她心里也是极为过意不去的。
可她一面是这么说的,另一面却是痛苦的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即使是在这样冰冷的池子里,额上也依旧有冷汗渗出,不经意间抓紧了身畔的胳膊。天知道此时此刻她浑身是有多难受,又痒有燥,好想好想找个渠道将所有的束缚全都解除掉。
“公主体弱,又中了药,末将不放心!”淡淡的几句话将脆弱的刘蔓樱逼得再无话可说。
刘蔓樱低吟一声,顺然地躺在他的怀中,这样的滋味太熟悉了,她透着清冷的月色,用迷离的双眸看向他,那寂冷的表情,在这一刻像极了他。蔓樱闭上眼,什么时候开始,她已经习惯了那个人的气味,看到男子,总是会不自觉地和他作比较。她眸中晶莹闪烁,想着想着便没了意识。
清晨醒来,蔓樱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冰冷的池子里了,身上燥热的滋味儿也消磨殆尽,但她依旧是躺在曹渊的温热的怀中的,所以丝毫没有冷意。她禁不住睁眼看向还抿着双眼的他,曹渊,真的很瘦,而且身材又很修长,但是因着警惕之意,肌肉的线条却又丝缕明了。
曹渊乃真君子啊!
忽然间,曹渊睁开了如墨的双眸,刘蔓樱一怔,赶忙尴尬地回过目光,却好像已经是来不及了,她只得死睁着双眼,似天然呆地看向天空,努力忽视身边的人,努力忽视……
他看着此时狡黠灵动的刘蔓樱,其实心中又何尝没有潸然心动,顿了顿后,神思似乎有些凌乱,墨眉越蹙越深:“公主,昨晚之事,末将,末将……”
“哦,昨晚之事啊!”刘蔓樱忽地反应过来了什么,昨晚虽是神志不清的,但那些个让人面红耳赤的情节还是历历在目,恍惚前一刻他们还在抵死缠绵一般,她本有些惨白的脸色在想起那些个羞人的事情后,一下子就红了起来。猛然间,蔓樱坐了起来,逃离了二人之间暧昧尴尬的姿势,佯装不在意地捋了捋额间散落的碎发,“昨晚之事,本宫会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将军也莫要往心里去。”
将军也莫要往心里去?他心中将这句话默念了好多遍,心中说不出的难受,昨晚公主是那样地疯狂而又美妙,他想说,若是公主不嫌弃,他愿娶公主为妻,一辈子对她好,将她视若珍宝。
可想来也算了,公主是金枝玉叶,岂是他这样的莽夫能随意玷污的?
只要能守护在她的身边,那也是一件极其快意之事,他安然道:“公主放心,末将已经忘了!”
刘蔓樱抬眸看他,其实心里有些失落,昨晚他们那样的缠绵,他说忘就忘,这也太快了些,不过细细一想来,那也好,总好过他死活记着这件事要来的安稳些。
“嗯,本宫就知道曹将军也是爽直之人,等到了梁国,定叫父皇母后……”刘蔓樱一个激动就又使出了以前的公主模样,不过忽然想起来现在梁国正值国难当头,哪里还经得起她这么折腾,她戛然而止,略显沮丧地说,“等到日后国家危机平了,再好好报答将军吧!”
“公主言重了!”曹渊抬头看她,淡淡地说了一句。
他不想要她的任何报答,过去他想要的生活是加官进爵,妻妾成群,可是遇到了平华公主后,一切就变了,而且还变得那样快,一下子就把他男人的霸业全都磨平了,他想要她好!
担心启睿的人追上来,他们改走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原本三天的路程一直跑了五天才到了大梁宫中。
一路上,大梁看起来似乎还是那样的平静和美,可是那种滋味却怎么看都觉得怪,为了方便此时的刘蔓樱是一身男装着身,她与曹渊早已下马开始走路,在闹市一家小酒楼里停下来歇脚。
那酒楼看起来不大,里头也是鱼龙混杂,她忽地听到一个长相肥硕的彪形大汉在地上不雅地啐了一口子唾沫,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摆,粗野地坐下来和身畔几个粗人道:“这大梁迟早是要亡了啊!”
“杀猪龙,说不得啊说不得!”一旁一个长相稍微斯文点的中年男子赶忙止住了他的话语。
那被称作是杀猪龙的男子大手大脚地撇开斯文男子的话语,“怕什么,现在上头谁还有工夫来管俺们,俺不过一个大老粗都看出来了,这大梁还有谁不晓得吴国已经传来消息,发兵五十万攻打大梁,梁国早就不是以前世祖皇帝时候那个兵强马壮的梁国了,吴国一来,必亡!”
、051 珠帘花影逝(二)
蔓樱一惊,太快了,匆忙扔下一锭银子,拉上曹渊便快马飞奔前往梁宫。
她本以为吴国即使说起要攻打梁国也不会在这么仓促的时间内动手,可是照着现在的形势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筹谋已久的事情了。
“公主,圣主正在御书房议事,已经一天一夜了,公主还是先去见皇后娘娘吧!”大梁宫门口,大太监方德有一边小跑一边和公主说着现在朝堂的紧急。
“那也好,先去见我母后!”听着方德有叽叽喳喳的话语,蔓樱也听不出到底什么花头来,大抵也就只知道吴国已然发兵伐粱。
她飞速赶往琼楼殿,见母后依旧淡漠地坐在贵妃榻上绣着花,似乎一切都与她毫不相关,可是蔓樱知道,母后眉间淡淡的痕迹正在毫不留情地揭示着她的伪装。
“母后!”蔓樱对着那个雍容华美的女子神情地叫了一声。
岳修容缓缓抬眸,如水的眸子多了很多哀愁,在听得那一声“母后”后,直直地站了起来,快步向蔓樱走去。
没有多余的言语,有些颤抖的双手拂上了她的面容,将她的眉,她的目,她的唇,她的鼻都仔仔细细的描绘了一遍,她似乎变黑了许多,不像以前那样白的像纸一般,不过这样的她看起来更美了,也……更像当年的岳修容了!
许久许久,岳修容才含着泪轻呼一声,“回家了!”
“女儿回来了,女儿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母后了,娘!”蔓樱终究忍不住趴在岳修容的怀中嚎啕大哭,这些日子受的苦受的累她好想一口气全都告诉自己的母亲,似乎只有在她这里,才能得到心头最真切的慰藉。
可是这个时候,她不能说,她要坚强,大梁正值风雨飘摇之刻啊!
此时不是叙说母女情深的时候,蔓樱咬了咬牙,抬起头,凑到母后的面前,直直地看着她的眼,一字一字认真地道出自己所知道的消息:“母后,儿臣身上有定王的军事布阵图!”
岳修容一惊,“你如何得来的?”
“自然是定王身上,儿臣与他朝夕相处一月多,这是儿臣应得的!”蔓樱双手紧紧捏着拳,以此来掩饰心里的慌乱与酸苦。
“蔓樱,委屈你了!”修容携了蔓樱坐下,又开口试探问:“那宫中的那位又是谁?”
“母后不知吗?”刘蔓樱本也想问问母后藤兰妹妹的事情,但看母后这表情,也丝毫不像是装出来的,她拨了拨垂在胸前乱成一片的长发,声音有些低哑,“是,是藤兰妹妹!”
“啊,藤兰完了!”岳修容毫不留情地直言。
刘蔓樱看母亲如此认真,定然不是在同她开玩笑,她迫不及待地问,即使她心里已经隐约也猜到了一些,“母后此话怎说?”
岳修容的容颜有些阴沉起来,脸上的严肃与认真是平日里甚少出现过的:“你想想,此番你偷了定王身上的布阵图,定王必定会记恨与你,决然不会再顾及你而来护你周全,他心头的气没处发,那就必定会惦记上宫中的那一位。吴国伐粱,本是不义之师,吴王等不及了才开始动的手,他们少的就是个理由。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出师得有因,所以必定会在此事上大做文章,藤兰……必死!”
“可是,可是启睿他答应过我会护藤兰的!”蔓樱支支吾吾道。
“傻孩子,男人在温存迷离之际说的话是不能信的,在男人的心目中,女人永远都比不上他们的无上霸业,你明白吗?”修容附上女儿的手,一字一句开口。
“蔓樱回来了!”忽而一个低沉的男声入耳。
原本倒在母亲怀中的蔓樱慢慢抬头仔仔细细地看向大步进门的男子。
刘家的男人集合了数代优良基因的遗传,无疑皆是长得高大而英俊,而眼前的刘显,分明就称得上是良品中的极品。在岁月的冲击下,依旧可见他桀骜飞扬却微微蹙起的眉,深邃似寒星且犀利而凌厉的丹凤眼,就连鼻子也高挺而轮廓分明,唇形更是堪称完美。她的父亲是这样完美的一个男子,可为什么他不过不惑之年,却是半头银丝?
刘家的女儿也是能挑起大担子的,蔓樱憋住已经到了眼角边上的泪水,笑了一眼,拿出塞在衣襟里的东西跪下道:“儿臣参见父皇!”
“我儿快起!”刘显扶起女儿,接过布阵图,摊在榻上一看,吴国伐粱时北面的兵力状况已经清晰地跃然纸上,可是……东南西面的呢?
“怎么了父皇,莫不是这个东西是假的?”刘蔓樱看着刘显越来越促然的眉头,忍不住凑上前去担忧地问道。
“图是真的,只是少了大半!你看,这里只有北面攻进,其他的都没了!”刘显语气有些焦躁。
刘蔓樱即刻凑上身去观察,果然如此,她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那一日她拿到图后他的表情和话语,他眼中甚是没有多大的慌张,他果然不是这样好忽悠的人,装的可真不容易,她捏紧拳头,对他的最后一丝愧疚也消失地无影无踪了!
“报……启禀圣主,已经查明,吴国的兵马已经在城外十里处的十面亭扎营,此次吴国派出的伐粱大元帅正是定王启睿!”未容下刘显稍稍休息喝下半盅茶水,殿外便有小将匆忙来报。
刘显赶忙站起来,带上还杵在一旁的曹渊,急切地回去议事。
刘显一走,蔓樱再也支撑不住,软软地倒在了椅子上,双目之间也没有多大的神色,他真的恨了,他真的狠了!
那晚他伤得那么重,可不过短短几天,他就带兵来伐粱,若不是因着满腔的恨意,他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真么狠心?
“母后,儿臣信了,日后再不会相信男子之言!”蔓樱淡淡地说了一句便径自往自己的寝宫去,惨淡的背影仿佛没有生命的躯壳一般。
岳修容看着女儿凄凉的身影,无奈地苦笑摇头,蔓樱她……是对那定王启睿动情了!
、052 梅枝残雪败(一)
雪意娇春,腊前妆点春风面。粉痕冰片。一笑重相见。
在寝殿里,刘蔓樱唤来侍婢准备了热水沐浴,她要将这些日子的所有记忆都洗干净,洗空白。
她双手抓紧了木桶,十指深深的抓着,似乎想要陷入其中,内心极力的挣扎着,究竟是什么,让她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她恨,她不甘,她又有无比的辛酸苦楚!
思及当年,吴国也曾因战败而臣服于梁国,岁岁朝贡,看起来似乎很是谦卑,却不料,短短几年之间,吴国迅猛之中兵强马壮,如雨后春笋般一夜崛起。果然事应证了那句花,会咬人的狗都是不叫的,那吴国的启氏兄弟又怎会愿意如此久居人下,被人奴役,所以,他要来报仇,洗雪当年的羞耻。
细细思量一番之后,刘蔓樱不由在心里暗自喟叹,这世道真真是恁地诡谲,人心险恶,风云变化之下,这天下真的是要大乱了。
她只是一个女子,管不了多少,即便是家破了,国亡了,战乱骤起了,天下大乱了,她一介弱女子又能改变些什么,既不得袖卷朝堂,也不可倥偬沙场,只能静静地,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宣判吧!
她唤来碧霄,关上门,将自己关在这略微有些萧条死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