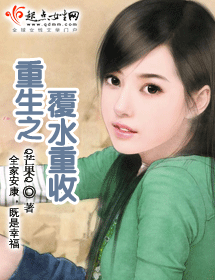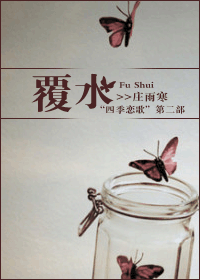覆水-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八卦
要问一个单位最适合和最集中八卦的地方在哪里,答案莫过于两个:厕所和食堂。这两天,B市人民医院这两个八卦最集中的地方议论的都只有一件事。
“听说了吗,脑外科的陆子谦停职检查了……”
“你是说脑部‘陆一刀’的陆子谦,陆大夫?”
“就是他!”“八婆”扫了一眼食堂四周,刻意压低了声音:“我听说啊,最近天天在院长办公室闹的那些人就是他最近一个手术病人的家属。”
“是嘛?我听说,那可是个事故……”
“不是事故干嘛无缘无故停职了?”
“可是,这么多年,他的技术可没得说啊,怎么会出那么大一个事故?”
“八婆”的头凑得更近了,“我还听说,他半个月前和他老婆离婚了,没几天就做了那个手术……”
“嘘,别说了,那不是陆大夫吗……”
陆子谦端着打好的饭菜坐下的时候,那张桌子上的人已走了个七七八八。这人啊,说白了就是个比低等动物更势利一点的高级动物。你得势的时候,那八杆子都打不上关系的人伸长了脖子也往你这边靠;而一旦你失势,那些八杆子打来的“亲朋好友”准保个个脚底抹油,唯恐跑得慢了让你沾上个一点两点的。现在,“亲朋好友”们演的就是这一出。想当初,陆子谦一术成名,完成省内首例脑干瘤切除手术被捧到B市人民医院光荣榜最高那个位置时,走到哪儿不是赶着和他打招呼套近乎的人;现在,还只是“停职检查”谣言阶段,人家看着他过来,就跟看到一个传染病人似的……
陆子谦就在一群“传染病科大夫”们的注视下,端着饭菜,慢慢地坐在那张已经没有一个人的桌上。放下饭,在桌上一一排好打来的几样菜。这桌上没人有一个好处,可以像开博览会那样,把食堂那色香味其实不咋样的东东摆得跟皇家御宴样,而不像以前,再好的饭菜也委委屈屈地挤在一起,还有人硬伸过用还沾着饭粒菜汤的筷子和着那些个唾沫横飞的嘴巴到你跟前跟你套近乎。现在,终于可以安静地——吃一顿饭了!
陆子谦扫了一眼桌上的三样菜:烧白、红烧蹄花、辣子藕丁,想也没想,夹起面前的一块烧白,狠狠地塞入嘴中。
这烧白,在B市人民医院中有着另一个亲切的名字———四指宽浪里白条。七个字说来并不顺口,可端端把这毫无色香味形象还特怪的东东形容了个淋漓尽致。因此,这道食堂“名菜”一般都属折价促销货。要放在以前,别说打来吃,就是看,我们的陆大夫也不会多给一眼的。
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
陆子谦的嘴角突然往上牵了牵,嘴里那块肥硕油腻的东西也顺带着再在嘴中转了两圈,直转得满嘴的油引来胃上一阵恶心时,他听到了那个东东滑进食道滑向胃肠的声音……
几乎是立刻,胃里便升起一股熟悉的燥热感,什么东西便有些复苏的迹象了。他下意识地按了按那个蠢蠢欲动的部位,再度无所谓地笑了笑。抓起筷子准备伸向面前的另一盘菜——辣子藕丁时,他的手机响了。握着筷子的手在半空中顿了顿,终还是回到原位放下了筷子,拿起了手机。
'郑院长让你再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陆子谦一惊,猛地抬头,立刻便对上了邻桌王月担忧的眼睛。只一秒,他便迅速移开自己的,推开面前的饭菜站起身来向外走去。
“王月,你说大家说的是不是真的?”一看到陆子谦离开座位,陈芳便碰了碰一直拨拉着白饭的王月,有些好奇地问。
“什么真的?”
“你不会没听说吧,关于陆大夫的……”
“别瞎说,他不是那样的人!”王月声音不高,气势却挺盛。
“可别人都这么说,你是他科里的,当时那个手术你也在场……”
“我吃饱了!”王月没有接话,站起来,没有再看陈芳一眼,自顾自地走了出去。
“这人今儿怎么了,毛病!”
********************************************
出B市人民医院大门右拐,再往前直行两公里,就是B市一中——号称B市的“北京四中”。别具一格的大门、红色花岗岩的校名碑、高大气派的教学楼、簇新宽阔的标准体育场……处处彰显着它的卓然之气。
梁音笛站在校门口,漠然地望着这一切,手中打的那点饭菜早已成了凉粉凉菜……
“想什么呢,梁老师?”高三数学组的官晓清碰了碰她的手臂
“没……没什么……”梁音笛有些尴尬地笑笑:“我在看,这个暑假,学校重新修的跑道……”
“没有吧?那个跑道不是暑假前就修好的吗?”官晓清顺着梁音笛的目光往前看,目光中的疑惑反而深了。
“哦……是我……记错了。”
“哎呀,知道你们学中文的,看到一点点风吹草动就浮想联翩了,个个跟林妹妹似的。走了,开会时间到了,一会儿莫主任训起人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官晓清和梁音笛是同级毕业生,同年分到B市一中,又同时分到一个班教书。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几年下来,虽说不上是多好的朋友,却也多了点默契。官晓清原本不是个太积极的人,这会儿这么主动积极地拉着梁音笛,后者就知道她一定还有事要对她说。
“说吧,又有什么事?”梁音笛端着自己那一盒凉粉凉菜按着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走着,问出去的话却是直截又了当。
“那个……”官晓清掩饰性地笑笑:“什么也瞒不了你。你知道的,我姐还有大半个月也就该生了。”
“嗯。”
“她一直在人民医院检查的,也打算在那儿生……”
梁音笛已经猜到官晓清接下去要说的话,她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饭盒,平静地打断官晓清:“那里又不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你姐夫家里条件那么好,去**医院生吧。”
“谁说不是啊,我也这么劝过她。可她就一认死理儿的人,我也没法。不过,听说人民医院妇产科的病房也挺紧的,尤其是单间,没熟人根本就订不了。我又只有那么一个姐姐,这不,想东想西想了好几个晚上,就想到你了。好音笛,今儿回去跟你们老陆说说,帮我姐想想办法。”
梁音笛听到自己的心似乎漏跳了一拍,就在刚刚,官晓清云淡风轻地提到“老陆”这两个字时。
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多顺溜的一句话,可不知道哪个字生生地堵在嗓子眼了,梁音笛除了差不多把手中的饭盒攥出一道印儿来,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哎,好音笛,我知道你们家老陆有办法的。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上,帮帮忙……”官晓清见她半天不说话,误会了她的沉默,赶紧地又加上一句:“我姐夫那人你知道,特讲义气,这事儿完了,他明白的……”
“晓清,你想到哪里去了……”梁音笛的脸涨得通红,好一会儿才回复正常,咬了咬唇,她才淡然一句:“我先帮你联系下吧。”
作者有话要说:终于得到编辑首肯,新文和大家见面晚了,不好意思哈。
这文可能有些慢热,不过,你们懂的……
不多说了,爬下去折磨陆G了,哈哈哈哈……
PS:要花花,要收藏,要评论……小寒开始耍赖撒泼了哈。越多的话越兴奋,越兴奋则文思泉涌哈……
还有,本打算上来就双更,可是年终了,小寒事多,在不保证每天能写文的情况下,先保守点,等一切确定了,就双更哈。至于时间什么的,你们知道的啊。。。。
、电话
走出院长办公室的时候,早就叫嚣的胃突然到达了顶点。陆子谦只得一手按了那个今天特别不安分的部位一手扶了墙慢慢向前挪动。
“子谦啊,你把手上的工作整理整理,特别是安排好还没做的那些手术,下午我让顾磊来这里和你办一下交接……”
“你应该知道,我也是没办法。你这次闹腾的事儿实在太大,省卫生厅都来人调查了……”
“子谦,我一直很看好你的。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就放弃了自己。我听说你最近身体不是太好,正好可以利用这个空隙好好回家休息下……”
“小梁是个不错的姑娘,我听说……以前你是太忙了,现在也正好利用这个空闲,好好和小梁再谈谈,夫妻嘛,难免有矛盾,谈开了,就好了……”
郑院长刚刚说过的话一遍一遍在脑海中翻滚云涌,带出了陆子谦怪异的笑,和着他额上不断淌下的汗和按在腹上不断深入的手,让他虚脱得几乎迈不动步子。
“我终于失去了你,在茫茫的人海中……”手机中为某人特别设定的铃声突然响起,惊得身子已顺着墙根缓缓下滑的他猛地停住。深吸了一口气,拿背抵了墙,腾出扶墙的手勉力地摸出手机,迅速地按了接听键。
“音笛?!”尽管提前深吸了口气,声音还是有点哑。
“是我。”声音淡淡的。
“这两天,医院有点事,等忙过这阵,那些东西……我会尽快拿走。”
婚是协议离的。两人原来住的房子本来就是梁家出钱买的,搬出去的毫无疑问该是陆子谦。不过,考虑到两人离婚的事都不想张扬,所以当初说好,陆子谦的东西会在十天半年月之内陆续搬走。可是婚离了没两天,他的手术就出了那啥事,一忙起来,还真把这事儿给忘了。现在,看到梁音笛的电话,陆子谦估摸着,这个时候,她会给自己打电话,多半是提醒自己来着。所以,想也没想,那些话就顺溜地出了口。直到说完,才发现那个不争气的胃到这时候竟然闹腾得更凶了,一只手几乎快压不住那狠狠抽搐着的东西了,他迫切地需要另一只手的帮忙,不能再跟她罗嗦了。
“就这事?放心,不会占着你地儿的。挂了……”
初接电话,听着那个有些沙哑的声音,梁音笛的心不由自主地沉了沉。正寻思着该怎么着问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又不让他听明白自己的关心免得他得意了去了的时候,那个声音已恢复成这近半年来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不耐烦,那些原本藏着掖着的点点滴滴随着这声音哗啦啦地在脑海中炸开,炸得她瞬间晕头转向。除了反击,她再也想不起别的。
“陆子谦,离婚协议上的条款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这10来天就把东西搬走也是你自己说的。怎么,现在这摊儿成阿Q头上的瘌疮疤了,连提都不让人提了?”
这梁音笛气性劲一上来,把自己给陆子谦打电话的真实目的给忘了个一干二净。心里想的,尽是怎么着把电话那边那个人的嚣张气焰给打下去,这语调提高了几十分贝不说,还把自己学中文的那点底子迅速地给搜肠刮肚了一番,怎么尖酸刻薄就怎么说。
“你要是实在找不到地方,得,我梁音笛也不像你陆子谦那么绝情。我会好好地把你那些东西供在家里固定的地方,一动不动放上个几十年,逢年过节还拜拜……”
“梁,音,笛……”陆子谦整个人已经在墙角一端几乎蜷成了团,那只手已经捏成了拳头陷在胃里。可是,还是痛。这个老毛病今天似乎特别和他过不去般,疼痛以排山倒海的势头向着他一浪一浪地涌过来。他已经没有办法说出句顺溜的话了。
“别那么咬牙切齿的!”他的一字一顿听在梁音笛耳朵里完全就变了味。这要放在几年前,她也能体会出点不对劲来。可是,现在,他们已是陌路,不,应该说是仇人,那些不对劲在梁音笛看来,不过又是那个男人冲自己发火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陆子谦,我梁音笛从来就不欠你的。你也用不着把我叫得跟阶级敌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