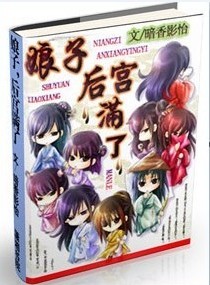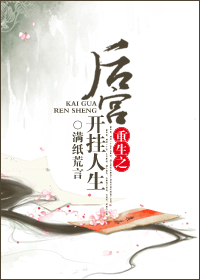后宫沉浮之萧后野史-第8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萧清婉此时只穿着家常旧衣,并未大妆,还在床上卧着,因是病中,赢绵如今又是自己的小辈,也不起身,只叫传了进来。
须臾,赢绵入内,进了内室,与皇后请安磕头已毕,萧清婉令宫人放了凳子,叫他坐了说话。
赢绵见她果然清减了许多,身上着一件杏黄丝绵衣,额上戴着一条翻毛貂鼠卧兔,一把青丝散挽,只插了个关顶的翡翠簪子,面上脂粉不施,右手上笼着一串玉钏儿,露出一截白腻的腕子,就是一副病弱西子之态。当下说道:“儿臣才入京,听闻母后染了风寒,便进来与母后请安。如今天气寒冷,母后如何这般不当心,熬汤调药都是小事,只是亏了自己的身子,倒让……儿臣担心不已。”萧清婉听他语露关切,怕为宫人瞧出,便岔了话头,道:“也不是大病,吃了几副汤药,精神许多了。倒是你,听你父皇说,你往陕西去了?”赢绵道:“是,西边有些暴民,在闹什么红花教,搅得当地百姓不得安宁,儿臣过去料理此事。”萧清婉便道:“正是太平盛世,怎会有暴民?”赢绵说道:“任是什么时候,怎会没几个不安分的人?他们都是犯了王法,被朝廷流放的罪人,心有愤懑,就生了这些事出来。不算什么大事,已是平息了。”萧清婉道:“纵是如此,你才从南边回来,又往陕西去,这事儿岂无当地官员处置?何必你去辛苦这一遭。”赢绵低头,半日不曾言语,倒将床下摆着一双绣鞋看了个真切。
萧清婉见他这般,恐为宫人见笑,便对穆秋兰道:“姐姐才打发人送了些吃食过来,你去瞧瞧,估摸着本宫不吃的,就拿去赏人罢。”穆秋兰心知其意,略踟蹰了一阵,便去了。
赢绵见四下无人,方才说道:“我不去怎样?留在京里,三五不时便要进宫问安,瞧着你同皇帝恩爱情深?如今京里都传遍了,说皇上与皇后娘娘琴瑟和鸣,鸳盟和谐,直叫世间夫妇无不羡慕,我听得还不够,还要进来看?”说着,又冷笑道:“凭着你人物心性儿,也难怪他宠你。入了宫,于你倒是如鱼得水了。”他满心妒恨,只顾说来解气,却把萧清婉气得发怔,两手冰冷,好半晌才说道:“你这是什么昏话!莫不是要皇帝冷待于我,将我丢在一旁,将这坤宁宫变作个冷宫,才趁了你的意是不是?!我但凡能自己做主,我岂是甘愿弄到这步田地的?!已是这样了,我又能怎样?何苦来,说那些有的没的,白白叫人生气,你又能得些什么好?!”话说着,两只眼睛便先红了,就拿了帕子擦拭。
赢绵话一出口,便先悔了,又看萧清婉抹泪,心里更觉愧意,禁不住伸手去拉她,口里道:“婉儿,我一时失言,我……”话不待说完,萧清婉将手一缩,正色呵斥道:“这是做什么,尊重些!我叫她们出去,就是不想人看笑话!如今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心里没个成算么?吹到皇上耳朵里,你要活不要?你要我活不要?你父皇不待见你,你自该好生干你的前程要紧,别总思量这些没用的事。”说毕,便一叠声唤了宫人进来,青莺应声进来,萧清婉便冷声道:“二皇子要去了,着人好生送出去。”
青莺看这情状,不敢多问,只上前请赢绵起身。赢绵见萧清婉冷着脸,心底又愧又悔又妒又恨,也知再坐不下去,只得起来告退去了。
第96章 递状子
赢绵出了宫门,日常跟他出门的小厮来宝正在门口候着,见他出来忙迎了上去。至跟前,又见他面色不愉,便问道:“殿下脸色不好,敢是皇后娘娘病体沉重?”赢绵微微摇头,灰着脸不言语,半日方才叹了口气,道:“走罢。”说毕,便翻身上马,待要去,忽见赢纬的轿子自门内出来。跟轿子的侍从,见着他主仆二人,也毫无停下的意思,一路呼喝着去了。
赢绵也不以为意,只问来宝道:“皇兄几时来的?倒比我走得还晚。”来宝却是很看不过赢纬的跋扈气焰,狠啐了一口方才道:“回殿下的话,奴才在这儿与宫门上的侍卫闲聊,他们说大殿下一早就进宫了,来的比往时还勤快。他如今还在禁中,想是闷的很了,借皇后娘娘染病一事,进宫逛逛也是有的。”赢绵微微颔首,便策马去了。
青莺将赢绵送至坤宁门上,往日还在相府时,自家姑娘同这二殿下的事儿,她心中最是明白不过的。现下瞧着赢绵闷声不语,适才皇后又冷面逐客,大致也猜到了些,只是不好说什么,将人送走也就罢了。
送走了赢绵,青莺立在坤宁门上出了会儿神,方才折回去。才踏进院门,忽见李明贵匆匆往外去,便问道:“李公公这是去哪儿?这般匆忙。”李明贵见是她问,立住了脚,道:“娘娘不知为何,又发起热来,穆姑姑叫我去请了太医来瞧瞧。姑娘快些进去罢。”青莺听了,连忙快步进了宫室。进了内室,果见皇后倚着靠枕,歪在床上,脸红过腮,如抹胭脂,便走上前去侍立在侧,又因方才的事儿,不敢吱声,只低着头听候吩咐。过了好半日,萧清婉方才轻声道:“送他出去了?”青莺听皇后开口,才回道:“是,奴婢瞧着二殿下出了坤宁门去远了,才回来。”萧清婉微微颔首,坐了起来,道:“身上疼的厉害,你给我揉揉。有烧开的滚水,让明月端一盏上来,口渴的很了。”青莺应诺,就挨过去,跪在床畔,替皇后揉捏肩膀腰腿。外头,明月就用定窑白瓷描金茶盏盛了一盏热水,进来捧与皇后吃了。
少顷,李明贵请了蒋世成过来与皇后把脉。
蒋世成进来与皇后磕头见礼已毕,便隔着屏风,为皇后把脉。一探之下,蒋世成眉头微皱,疑道:“娘娘在哪里着了气恼?肝火倒起来了,脉象也有些虚浮,这病后着气,不可轻视。小医这便为娘娘再添几剂药上去,娘娘且吃着瞧瞧。”话才说毕,一旁宫人早已研好了笔墨送上,他写了药方递与穆秋兰,又道:“娘娘还要保重凤体,宽心调养为上。”萧清婉轻声道:“本宫知道,蒋大人辛苦了。”蒋世成忙连称不敢,又停了片刻,不见皇后声响,一名宫人自屏风后头出来,笑着低声道:“娘娘睡了,大人请回罢。”蒋世成这才离去。
一时,宫人已取药回来,送入厨房煎熬。得了,青莺亲去拿了,端了上来。明月见了,道:“娘娘还在睡着,还是待娘娘醒了,再伺候娘娘吃罢。”其时,她二人心结略有松缓,又有文燕插在了里头,倒能说上些话了。青莺便应了,将药盛在青花瓷海碗里,又放进棉套子里暖着。明月看了看时辰,又道:“差不多是换值的时候了,咱们去吧,叫她们两个上来。”青莺笑道:“娘娘病这几日,姐姐也累坏了,还差几刻钟呢,姐姐就想换班了。”明月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如今娘娘病着,不出门,也不必梳头。倒便宜了她,平日里的差事也不必做了。就让她早来上几刻,也不算什么。”两人说着,就打发了个小宫女去喊了文燕绛紫来换值,便一道去了。
那宫女去时,文燕还在床上歪着,绛紫只坐在桌前描样子。那宫女进门,就说道:“两位姐姐,明月姐姐叫我过来让你们两个过去换值。”说着,又抬脚跑了。绛紫才待起身,那宫女已跑远了,便笑骂道:“这小蹄子,也不知哪里有热馒头等着她,跑的这样快!”说着,便往妆台跟前,对着镜子理了理鬓发,向文燕道:“你怎样,还起不来么?你总这样闷着,也不是个长法,今儿的早饭又没吃。不成,还是跟穆姑姑说了,请个大夫瞧瞧。总说不爽快,也好长日子了。”文燕翻了翻身,道:“又没怎么样,叫大夫来瞧什么?且娘娘又病着,我再去淘气,凑在里头添热闹,惹人动那唇齿。”绛紫低头想了一回,道:“也是,如今明月姐姐也不知怎的了。每每见了你,总有那许多带刺儿的话说,听在人耳朵里叫人不舒服。”文燕只笑了笑,道:“这地方难站,几时能离了才是好呢。”绛紫梳了头,道:“时候可是不早了,我去了,你略躺躺也赶紧上来罢。”说毕,径自去了。
文燕躺了一刻,忽有日常服侍她与绛紫的一个名唤琳琅的小宫女进来找她。文燕见她进来,忙坐了起来,问道:“这会儿进来,可有话说?”琳琅却先瞧了屋里,见并无别人,才自怀里拿了一样东西出来,递与她,悄声道:“那边传话过来,说总进宫来,惹人注目,皇后娘娘又病着,这边耳目众多,不方便。还是待下元节酒宴那日,宫里人多,倒是便宜。”文燕自琳琅手里接了那物件,又问了琳琅几句话,便打发了她出去。取了那物件细看,却是一件绣了红香美爱四字的荷包,里头又填着许多香料,并一张胭脂红小笺,其上写着一首艳词,观其字迹正是那人的,脸微红了红,匆忙收了,就起来整衣理鬓,也往前头去了。
赢绵同来宝一路回府,走至西大街牌楼下,就见远处一群人闹吵吵的围在一起,中间停着一顶轿子。观那轿子规制,乃朝廷正五品官员的乘轿,却不知为何停在这里,又被人围着。赢绵心起疑惑,便对来宝道:“去瞧瞧,什么事情。”来宝一溜下马,快步上前,打听了半晌才回来,说道:“是大理寺推丞李十洲李大人的轿辇,被一书生拦着告状呢。”赢绵闻言,道:“此事倒新鲜,什么事竟要告到大理寺去,地方官员又是做什么的?且便是告状,为何不到大理寺,反在街市之上,众目睽睽之下拦截朝廷官员的轿辇?可见这人刁钻。”来宝应和道:“殿下说的是,只是那书生口齿上极上的来,说的朗朗动听,又哭得声泪俱下,让人瞧着可怜。”赢绵轻笑了一声,道:“李大人接了状子了?”来宝道:“瞧那情形,李大人是打算接了。”赢绵颔首不语,又策马往府邸行去,一路无话。
回至皇子府,赢绵换了衣裳,还不及问旁的事,便吩咐来宝道:“带几个妥帖的人,去打听打听街上咱们撞见的那件事儿,问清事情始末,再来回话。”来宝是个机灵的,一听吩咐,便领其意,忙出去办差。
不出一日的功夫,来宝回府,打听主子正在偏厅上歇息,便过去回话。
其时赢绵正听几个管家禀告离京期间府内各项事宜,听来宝回来,便叫他们都出去了。来宝入内,将打听到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述说明白,道:“那书生婢女被临朐县县令的家奴霸占,告状不成,反被县令赵文广一顿杖责,连状子也撕碎扔了出来。那临朐县位处京畿之地,上头再没州府管辖,只好进京来告,就寻到了大理寺。”赢绵自椅旁的红木小几上端了茶碗,自啜了一口,方才道:“我依稀记得,那临朐县县令,乃是赵贵妃的侄子。那书生生了七个头八个胆,敢告他?就是进了大理寺,民告官,依律法五十杀威棒是免不了的,那五十棒子下来,还有命在?”来宝道:“殿下说的是,只是那书生告的并非是赵文广,而是他的家奴。也是赵文广不收诉状,这才进京上告。论起来,也不算状告朝廷命官。”赢绵沉吟道:“便是如此,这书生胆子也未免忒大了。他可有功名在身,家中可有人在朝为官?”来宝道:“他本人只是个不第的秀才,并没功名。倒是他亲叔叔,是宫里御前总管太监张鹭生。”赢绵道了句“原来如此。”言毕,便起身,在堂中来回踱着步子。
来宝在旁立着,久不见他出声,禁不住问道:“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