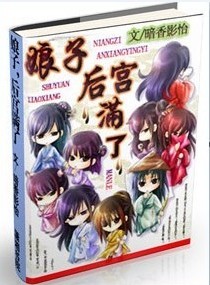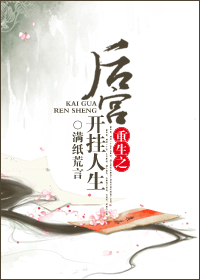后宫沉浮之萧后野史-第1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赵红药冷笑道:“安分守己?我若安分守己,就只会是个太子府里蹲在角落里抱着孩子流泪的侍妾了!你想想当年,你那府里有多少内宠?!你在我身上才花了多少心思?!皇帝陛下,你要我如何安分守己啊!”赢烈冷声道:“这般,你便残害旁人,毒杀朕的孩子?”赵红药仰起脸来,狞笑道:“不错,当年自你宠了我之后,我就打定了主意,就算踩着别人的尸体,我也要往上爬。谁挡了我的路,谁就得死。但凡不是我生的,就只好怪他自己命不好——谁让他不投在我肚子里呢?老二的母亲死后,老二已形同不在,我这才容他活着。老三的母亲是个愚拙的蠢物,老三也没什么作为,我这才留他一命。只可恨那贱|人命好,又防守严密,我无从下手。否则,我真想剖开她的肚子,把那胎儿挖出来!看他还如何同我儿子争夺储君之位!”
赢烈见她言辞激烈,神色狂乱,只摇头道:“真是丧心病狂!朕,真不该来这一遭。”说毕,便向刑房的太监道:“打发娘娘上路罢。”赵红药却厉声喝道:“不必你们动手!我就要死,也绝不死在你们这些下作奴才手里!”赢烈转过脸来,说道:“他们是下作奴才,你是什么?你忘了你的出身?”赵红药朝他笑着,说道:“原来皇上心里,我永远都是那个卑贱的侍女。你对那贱|人宠爱有加,也不过是冲着她的出身家世罢了。你们,也不过如此!”赢烈淡淡道:“朕与她之间,有你置喙的余地?皇后贵为一国之母,焉容你这泼贱无休止的辱骂?!”赵红药笑道:“我就是要骂,横竖我是要死了。皇上,如今你又能奈我何啊?!”说毕,又连骂了十数声贱|人,眼看皇帝下令命太监上来,她便自头上取下钗子,捅进自己的喉咙。登时只见乱红遍地,她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便不动了,一双眼睛仍旧死死的盯着赢烈。
赢烈看着她尸横就地,只长叹了一声,迈步出门。
同年八月,庶人赢煕因为时气所感,风湿发作,暴病身亡。
作者有话要说:好吧,这两人over了。
赵红药,活的疯狂,死的也疯狂……
第一百六十章
待荣亲王谋逆一事尘埃落定;已是七月中旬的时候了。除却京城菜市口竖起的杆子上;挂着的盛装二十八颗人头的竹笼;此案竟再无半点痕迹。只是京城官媒教坊里;忽然来了许多年轻貌美的女子,她们言行举止都颇为不俗,也各自都会些琴棋书画,京中那起贪恋风月、自诩风流的墨客骚人;都闻名而至。一时之间;这些秦楼楚馆,竟有些应接不暇、人满为患的光景。
宫中,自打谨妃伏诛;往日里那起为她所欺压的嫔妃;均大感心胸畅快;皆出来说笑走动。又见如今宫中为皇后与皇宸妃独大,也都来趋奉。就是那些往昔与谨妃有些相交的,先自惴惴不安,坐卧不宁,闭门不出。但过了一段时日看皇后并未与她们为难,也都慢慢出来走动,先是硬着头皮来与皇后请安,落后见并没什么,也都各自放下了心。
而那起新遴选的秀女,入宫已两月有余,因着皇帝正忙着处置逆反、并东海兵乱一事,一时半刻也顾不上她们。就有些性子急躁的秀女,眼看皇帝回宫,敕封侍寝等事宜仍是毫无消息,便有些按捺不住了。
这日,正是暑热天气,萧清婉因怀了身孕,分外畏热,于是吩咐了门上宫人不见外客,在后院老槐树底下放了张湘妃塌。她自家散了头发,穿着一件天青色纱罗对襟衫,下头穿着白绫绸裤,罩了一条白挑线纱绉裙子,躺在榻上,让宫人在旁摇扇纳凉。如今宫中谨妃被诛,朝中荣王一党也都烟消云散,皇长子废做庶人,再不会有什么作为,前朝后宫为之一清。虽则宫中事端总是无穷无尽,但眼下总会清净上一段时日。她心中十分安宁,看着头顶微微颤动的槐树叶子,不由星眸半眯,困意来袭。
正在半睡半醒间,只听得一阵裙子拖地之声,绛紫快步走了进来。那正在一旁为皇后摇扇的春雨,见她进来,连忙摇手示意她噤声。绛紫见皇后似是睡了,便压低了声音,才问了句:“娘娘睡着?”萧清婉便懒懒的问道:“什么事?”绛紫见问,赶忙上前,凑在榻旁,小声说道:“若不是,奴婢不该来打搅娘娘,只是御花园里出事了。”萧清婉闻言,睁了眼睛,说道:“怎么回事?”绛紫说道:“今儿皇上下了早朝,说到御花园走走,才过了万春亭,就听到有歌声传来。那人唱的声儿极大,跟随的人都听见了。皇上就叫人去把那人找来,待人到了跟前,皇上见面目颇生,就问她是何人。谁知,她竟是一位新选入宫的秀女。还没位份呢,就敢跑到皇上跟前讨宠,也真是稀奇的紧。”
萧清婉淡淡一笑,眸中流光一闪,轻轻说道:“这是仿了前头钱宝林的成例,也算不得什么稀奇。”随即便含笑问绛紫道:“可是皇上瞧她才色双全,要封她做个什么?”绛紫却摇头笑道:“这回娘娘可猜错了。那秀女命不好,偏赶上皇上心情不佳,当面便斥责了她不守妇道,不安于室。又说她是专一打听了,埋伏在这里等着,可见心思诡诈阴鸷。皇上把这秀女斥骂了一顿,方才拂袖去了。那秀女只是个十来岁的姑娘家,哪里受得了这个,哭哭啼啼的,好容易才被跟着她的宫人送回延禧宫去。”
此事倒是颇出萧清婉意料之外,她先是扬了扬眉头,继而点头笑道:“是了,近来前朝事多,又是荣亲王谋逆,又是东海退敌不顺,皇上心里烦躁也是有的。偏有人不长眼,这时候撞了上去。她效仿钱氏,却又没钱氏那样的好命,可见东施效颦,只是徒闹笑话。”随即问道:“皇上没说怎么处置么?”绛紫摇头道:“皇上生气的很,说这样的人怎么配留在宫中,却倒并未下什么旨意。掖庭局也就不好擅专,只是打发人来问娘娘的意思。”萧清婉略一思索,又问道:“那秀女是谁家的姑娘?”绛紫赶忙道:“她姓章,叫章媛,好似是忠武将军的小姐。”萧清婉秀眉微蹙,说道:“又是她!前番在御花园里闹事,今次又生出这样的祸端。也罢,既然连皇上都说,她不配留在宫中,那便送她出宫罢。知会掖庭局一声,叫把她在册子上除了名。到晚夕,本宫还跟皇上说。”说毕,她略停了停,又叹道:“也是本宫近来怠惰了,这些事儿也还该管起来,姐姐一人终究忙不开。又有些事,她也做不得主。”便向绛紫道:“打发人对掖庭令说,叫把这些秀女入宫以来的日常行止记档全都送来,本宫看过做个决断。”绛紫应声去了。
至午后,钟韶英果然将记档送来,萧清婉令青莺在旁一桩桩的念了,听到哪里不妥当的,便命明月在此人名字下头做了个记号。待全都念毕,萧清婉又将册子取在手里,看了一回,心里琢磨了一番,便定了七个人选——皆是举止不端、言行张狂,家世出身也未见什么了不得的。这样的人,留在宫中,迟早也是祸患。遂吩咐明月抄录下来,放在妆台上的红木匣子里,只待晚上皇帝过来,与他商议。
晚间至掌灯时分,赢烈果然过来,先问了问她今日身子状况,饮食安好等语,便令宫人上来脱了外袍冠带,到明间里闲坐。
宫人端上了龙井,萧清婉见皇帝神色疲乏,便问了几句。原来黄河水患已然退去,只是正是伏天暄热,又发起疫情,朝廷调拨了大批草药并自各地太医馆中派遣人手前往。但这等天灾,自古便难以消弭,如今虽是倾尽人力,却也只得听天命了。赢烈略提了提,又道:“倒是东海那边,自朕过去,揪出了几个内奸,与本初贼兵已渐成平手。但本初乃一岛屿国度,极善水战,徐文达虽骁勇善战,一时也拿他不下。国内天灾未净,正需大批粮草银两安顿黎民,东海战事若再旷日持久,朕倒有些忧虑后手不接。”
萧清婉耳里听着他谈论前朝之事,心里却忽然忆起赵红药被擒时口里的话语,眼看赢烈正靠在软枕之上,端起茶碗轻啜,袅袅的水汽之后,他的面容却有些不大分明。
赢烈吃过茶,放了杯子,抬头见她正望着自己发怔,便笑着摸了摸她的脸,说道:“呆妮子,又想什么呢,这样出神。”萧清婉这才回神,连忙遮掩笑道:“臣妾在想,新晋秀女入宫已有一月了,除却那行止不端的须得剔除出宫,旁人则要给与封号,分赏居所。不然总这样没名没分的在宫里耗着,终也不是个事儿。再拖久些,又弄出今日御花园里的事儿来,也是不好。撵几个秀女出宫事小,坏了君臣和气就不好了。”赢烈点头说道:“你说的不错,只是近来前朝事儿多,朕一时也顾不上。你是皇后,这些事儿你就瞧着办罢,何人该定何位份,居于何处,你自己掂量着办就是。待完了,告与朕一声。”说毕,又道:“至于侍寝……她们既新迁住处,必要安置适应一段。那便十日之后再说罢。”
萧清婉应了,又将白日里拟定的人选交予赢烈阅览。赢烈略看了看,也并无二话,此事便定了。
到得禁灯时候,萧清婉一面叫人收拾床铺,一面向赢烈戏谑道:“臣妾有着身孕,不能够侍寝。皇上还是日日在臣妾这里厮混些什么呢?也得不着什么好处的。”赢烈只笑了笑,上前环着她道:“守着你,朕心里安定。”语毕,又在她耳畔轻轻道:“如今赈灾有朝廷行事,你父亲宦囊本不充裕,那粥棚还是撤了罢。”萧清婉心中微微一震,脸上仍旧挂着笑意,嘴里就说道:“臣妾也是这般说,百姓有难,自有皇上朝廷体恤管辖。臣妾与臣妾父亲,虽欲尽些绵薄之力,却如何能与朝廷相比呢?不过是白忙活罢了。且臣妾是皇上的妻室,臣妾父亲也是皇上的臣子,臣妾等就行些善事,天下百姓心里所记的,也是皇上。”赢烈莞尔道:“你这般懂事,朕才喜欢。”言毕,两人便携手入闱,共入梦乡,一夜无话。
次日,掖庭局将皇后懿旨向延禧宫中宣读了。那七名被驱逐的秀女,尽皆花容失色,和衣而颤,继而掩面啼哭,又有拉着钟韶英哀求面君求情的。钟韶英颇不耐烦,只得一一劝解。
旁人也还罢了,知此事已难挽回,闹了一阵便各自去收拾行囊。唯独那章媛,本是将门虎女,日常行事颇有乃父之风,性情刚烈,听到这样消息,登时粉面通红,怒发冲冠,也不去收拾东西,抬起玉手便向着立在一旁的一名秀女,就是一记耳光。
那秀女本就生的单弱,章媛这一巴掌打得又用了十足力气,登时便将她打得髻歪钗斜,脸颊红肿,歪在一侧。那秀女似是十分怯懦,只捂着脸颊,抽噎哭泣,不敢言语一声。她本生的白净清秀,身子又纤瘦,这般流泪自伤,更显得楚楚可怜。那章媛看她这幅模样,气不止不消,反倒如火上浇油一般,将一口银牙咬碎,抬手又要再打。却早有旁的秀女拦住,那秀女喊道:“她是天子宫嫔,你是被驱逐出宫之人。你怎能够动手打她?!”章媛向着那挨打秀女破口大骂道:“唐玉莲,你这口蜜腹剑的贱|人,挑唆我去唱什么歌!如今皇上赶我出宫,都是你这贱|人害的!我今儿破着这条命不要,也得咬下你这小贱|人下截来!”她满口污言秽语,所行尽是市井泼妇撒泼的勾当。虽有人阻挡,终究还是将唐玉莲的头发扯下一绺来,身上的衣衫也撕破了几处。
旁人眼看不是事,又恐拖累自己,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