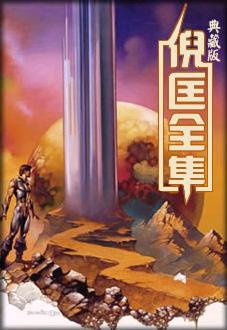影子二少-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今,却要投向别人的怀抱。
生命对于她来说,原来是个可悲的玩笑。
“初舞,这次回来妳好象不高兴?”父亲察觉到了她的不对劲。
她强做欢颜,“没什么的,爹,我只是有些累了,有太多的事情要准备,没想到成亲会是这么麻烦的一件事。”
“人生的第一大事嘛,当然会累些。”他笑着摸摸她的头,“当年妳娘嫁给我的时候,因为我正好要调职到立县,办得十分简陋仓卒,让我对她愧疚了一辈子。如今终于轮到妳出嫁,爹会尽全力为妳操办好这场婚事。”
“谢谢爹。”她喃喃轻语。
“对了,昨天君泽少爷派人来问妳,要在新房外种几株梨花?说是从国外找到了几个新品种,要移种到新房门前给妳看、妳瞧,君泽少爷对妳有多关心。”
初舞苦苦地笑,“是啊,君泽哥哥对我一向很好。”
“所以,能嫁给这样的丈夫真是妳的福气。”
父亲的连声赞叹、满脸春风,却引不起她一丝一毫的喜悦。
门外有侍女来报,“小姐,行歌公子来了。”
她一震,不知道是该说见还是不见,就在此时,行歌已立在门前,他的双手环抱胸前,好象抱着什么东西。
“伯父,好久不见了。”他先开口的对象却是她父亲。
夏宜修忙回答,“行歌啊,难得你会来。”
不知为何,即使行歌笑得优雅美丽,他每次看到却是深深的不安和心寒,彷佛在行歌的笑容背后总有某种让他害怕的东西。
“伯父可否稍让一步?我有话要单独和初舞说。”行歌非常谦逊有礼地问话,但是那眼神和气势却明显不是相询,而是高高在上的下令。
夏宜修心头的不安扩大,看了眼女儿,她的表情却淡得看不出情绪,对他点点头,“爹不是还有公务在身?你先去忙吧。”
于是,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行歌对那名侍女也微微一笑,“麻烦姑娘到偏房等候。”
侍女几曾见过这样优雅俊丽的公子?又何曾听过这样美妙悦耳的声音?脸色红透,踮着小碎步跑掉了。
反手关门,行歌炽热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初舞──她的脸上一片宁静,如湖水无波,清澈见底。
“好久没见妳着女装了,果然和我记忆中一样的妩媚。”
他微笑着赞美,慢步走向她。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妳时,妳盘着双髻,眼睛骨碌碌地转着,漂亮得好象画中之人。那时我就在想,等有一天妳长大了,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倾城倾国。”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她仍旧淡淡地望着他,“我是将要出嫁的人了,不便与夫君以外的男人单独见面,以后公子要见我请先让下人通传一声,在外面的大厅说话比较好。”
“以后?以后不需要这些繁文缛节了。”他始终环抱在胸前的手垂落下来,抖开一个卷轴,“还记得这幅画吗?”
初舞的眸光一闪,“这是……你的“子夜梨花图”。”
他扬眉,“是我画的,画中的人是谁,妳看不出?”
“你曾说过,画中有你一个极为珍惜的人。”明眸凝在画上,忽然她明白了──那婆娑舞动的树枝和那片清幽明亮的月光,难道都是在说……她?
“妳已经看懂了,是吗?”他的眸子亮如星、烈如火。“妳怪我从不肯对妳明言,但是十年前我已经把心捧给妳看,只是妳没有看懂。这幅画,我不肯送给妳,是因为我要将妳的身影刻在我的心上,留在我的身边。”
“我不信。”她的目光迷离,“你不是这样多情的人。”
依稀彷佛回到十年前,那时她曾说:“想不到雾影公子还是个多情的人呢。”
“多情自古空余恨,我但愿自己是个无情人。”记忆中他的回答与此刻说的话相重叠,连那黯然神伤的神情都分毫不差。
轻轻握住她的手,行歌柔声说:“初舞,跟我走吧。”
“走?去哪里?”
“天涯海角,哪里都可以,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初舞酸涩地笑,“永远跟在你的身边,永远只做你身后的影子?永远只做行歌的初舞?”
“做我的初舞,不好吗?这十年里,我们不都是这样一起过的?”
他的手轻轻环住她的腰,将她搂进怀中,灼热的唇落在她的耳垂上,吹吐着撩人的热气。
“初舞,妳的心中真能忘记我,视我如不见?妳真的可以安心地躺在君泽的怀里,曲意承欢?”
感觉到怀中的她在轻轻颤抖,他的唇角流露出难以察觉的浅笑,低垂下头,小心地含住她的耳垂,啃咬着她雪白的脖颈,一点点地挪移,直到双唇相碰,那如潮水烈火一般的浪潮骤然席卷了彼此的全身。
初舞的心彷佛都被他的热吻穿透。十年中,即使曾经相依相偎,即使曾经携手并肩,他与她始终以礼相持,没有过任何过分的亲密举动。
怎么也想不到,走入绝境之时,他会吻她。
他热烈而深切的吻让她无法躲避,或许是期待了太久,即使以为自己可以做到无动于衷,视同陌路,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她依然会忍不住沉湎于其中。
不知道他的吻到底纠缠了多久,直到最后她的双脚都已无法站立,他托住她的腰,手指摩挲着她滚烫的唇,悦耳的音色中还有一丝古怪的笑意,“这样单纯善良的妳,还能接受君泽对妳的爱抚吗?当他环抱住妳的时候,妳会像刚才与我那样,与他抵死缠绵吗?”
猝然,他松开手,退开几步。“这样冰冷的世界里,妳我只有像刚才那样拥抱取暖才可以生存。初舞,妳能否认刚才的一切不是出自妳的真心?妳能允许自己面对君泽时,还同床异梦地思念着别的男人?”
她的身子颤抖得更加厉害,不是因为身体的寒冷,而是心冷,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重重敲在她的心上,揪起了她的罪恶感。
即将与君泽成婚之前,她居然让自己投进行歌的怀抱,还不守妇道地与他……她还有什么颜面去见君泽。
“承认吧,初舞,妳只可能是我的,也只能与我在一起,无论时间,无论生死。”
那清冷的,犹如魔音一样的宣告,让她忍无可忍地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你走吧,求你,走吧!别再来烦我了,行歌。为什么你不让我平静地生活?为什么你要让我痛苦心碎才满意?”
行歌用力拉下她的手,静静地,一个字、一个字对她念出,“我最不想伤的人是妳,而妳在答应嫁给君泽的时候就已经伤了我,一个受伤的人,要怎样做才能自保?”
她怔怔地看着他,彷佛听不懂他的话。
“最好的自保方式,就是更重地去伤害别人。”他将那幅画塞进她手中,“初舞,我也不想让我们彼此伤害,我更不想伤害君泽和王爷,所以,请跟我走。”
初舞的嘴唇颤抖,眼眸中盈盈闪烁的全是泪光。
行歌彷佛等了上千年之久,才看到她的唇轻轻开阖,只吐出一个字──
“不。”
※※※※※※※※
吴王独子的大婚震动京城,连圣上都提前送来了贺礼,将吴王楚天君的威望声名提高到了极致。
热热闹闹的场面在王府中很久没看到了,虽然吴王每年的寿诞都会有不少宾客上门,但是近几年吴王放出话来,总推说身体不适,减少了会客的人数,所以寿宴也显得冷清了一些。
但是君泽的这次大婚不同,不仅震动了京城的富贾豪绅,重臣亲贵,边陲小国都派人专程送来贺礼,意图在这一天能博得吴王的欢心。
然而,就在这片热闹声中,却有几个人显得愁眉不展,心不在焉。
第一个,就是吴王。
自从行歌与他摊牌之后,一连数日都看不到行歌的影子,他派人去找,只得到回报说行歌不在踏歌别馆,无人知道他的去向。
以吴王对行歌的了解,的确相信他所说的话,也就是他想得到的,从来没有得不到手的话。
而君泽那天晚上与行歌到底谈了什么他并不清楚,只知君泽在回来之后,长长地慨叹了一句,“父亲不该将行歌的身世瞒我,更不该让他独自一人到江湖上去漂泊,这对他来说太不公平。”
吴王震动不已,“你不介意?”
“我怎么会介意多一个手足相亲的兄弟呢?”君泽微微蹙眉,“父亲,他已经孤苦了二十多年,如果我再……”
话未说完,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说下去了,但是王爷分明感觉到他后面所要提的是关于初舞的事情。
一个女人,居然牵住了两个儿子的心。于是吴王破天荒亲自到夏府去了一趟。
支开了惊喜惶恐的夏宜修,他瞪着初舞,直截了当地问:“妳的心中到底是想嫁给君泽,还是惦着行歌?”
她垂着眼睑,“王爷,我已经答应嫁给君泽,心中就不可能再有别的男人。”
“但愿如此!”吴王哼了一声,“别怪我没有事先告诉妳,行歌和君泽对我来说都如命根子,妳若是摇摆不定伤了他们两个人的心,我也绝不会放过妳!”
她云淡风清地笑笑,“王爷请宽心,我不会将这样的烦恼带到婚礼之后的。”
初舞的笑容似乎很古怪,却又让人说不出到底是哪里古怪?但是她既然做出了保证,他总算稍稍放心。
离开时,吴王忽然停住,若有所思地回头看着她,“妳娘去世前,有没有和妳提起过我,和我的王府中人?”
她摇摇头,“进京之前,从未听娘讲过。”
吴王露出黯然之色,喃喃自语,“妳娘比夜隐还要狠心啊。”
初舞不解地目送他离去。在眼前局势错综复杂的时候,王爷忽然提及了去世的娘亲,难道他与娘亲之间,也有着什么她不知道的关系?若有,为什么从未听父亲提过?
而那个夜隐,似乎是行歌的亲娘吧?
行歌与王爷的关系,也并不仅仅是养父子那么简单,否则王爷不会亲自前来,说出这一番警告。
她淡淡地一笑。如今这一切与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十指纤纤,抚摸着手中的一个玉瓶,清冷的瓶身圆润可人,瓶中的东西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沉香醉。
长醉就能解忧吗?
她微笑,只剩下微笑。
※※※※※※※※
王爷家迎亲的队伍很长,从吴王府到夏府不过七、八里的路程,却站满了无数看热闹的百姓。
或许是因为吴王身分尊贵,迎亲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新娘乘坐的是六匹马拉的花车,新郎并没有像寻常百姓那样骑在高头大马上,而是留在王府中等候。
应是刻意的炫耀,花车的四面都只用薄纱遮掩,微微飘起的纱帘后总是能让观者们隐隐约约地看到半张新娘的面容。
未用红纱掩面,这样的光明正大、毫不避讳大概也是刻意为之吧?因为如此,花车所过之处都留下一片惊艳之后木呆呆的表情。
“真不知道夏大人有这么漂亮的女儿,难怪可以嫁到王爷家呢。”
众人难免又是一番窃窃私语。
因为队伍行进得很慢,直走了两个时辰才走到吴王府门前。
君泽已经穿著红包的吉服在门前等候,他应该是等了很久,额头上都是汗珠。看到花车平安停在门口时,他的脸上终于露出淡淡的一笑,快步走了过去。
亲自撩开车帘,他轻声说:“初舞,我接妳回家。”
她的眼皮低垂,连睫毛都没有抖动,一只手交在他手中,缓步走出花车,满头的金钿玉珠也不曾摇晃。
“新娘进府,吉时已到!”
长长的喊声穿透了众人的耳膜,大家闪开路,目露艳羡之色,望着一对玉人般的新人携手走到大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