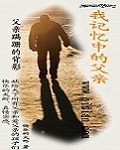中毒的父母-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种罪在人们看来是天方夜谭。父母,不管多么中毒,总是垄断着权力和信用。
“我觉得恶心”
乱伦的受害者所蒙受的耻辱是独特的,甚至很小的受害者也知道乱伦的事情应当保密。不管是否被嘱咐过要保持沉默,他们都能够感觉到侵害者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可耻的。他们即使年龄太小不懂得性方面的事情,也明白自己是在受侵害。他们对此感到恶心。
正像受到过言辞和身体虐待的孩子会产生自责一样,乱伦的受害者也会自责。但是,在乱伦的情况下,自责是同羞耻感交织在一起的。“全是我的错”这种信念在乱伦的受害者身上比在任何人身上都强烈。这种信念培植了强烈的自我嫌恶感和羞耻感。除了不得不设法应付现实的乱伦以外,受害者还要时刻提防不要被当做“下流、讨厌”的人捉住曝光。
利兹十分害怕会被人发现。
我当时只有10岁,但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坏的荡妇。我真想把继父的事张扬出去,但又怕家里所有的人,连同妈妈在内,会因此而恨我。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觉得我很坏。尽管我也觉得自己很坏,但对于在大庭广众面前成为坏人,却连想都不敢想,所以只能把此事深埋在心里。
外人很难理解,一个为继父所逼与其发生性关系的10岁女孩为什么会有负罪感。自然,答案就在于孩子不愿看到自己信赖的人竟是坏人。总得有人为这些可耻的、屈辱的、可怕的行为负责,既然该负责的不可能是父母,那就一定是孩子了。
卑鄙、邪恶、罪责难逃的感觉在乱伦的受害者身上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上的孤独感。无论在家庭内,还是在外界,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他们认为没人会相信自己可怕的秘密,而且这一秘密在他们的生活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常常妨碍他们交朋友。这种孤独感反过来又把他们推向侵害者的怀抱,因为这是他们能得到关注的惟一来源,不管这种关注是多么邪恶。
假如受害者从乱伦中还体验到某种乐趣的话,他或她的羞耻感便更重了。少数受害者成年后还能回忆起此种经历所带来的性快感,尽管他们曾为此感到困惑或尴尬。对这些受害者来说,此后要消除负罪感甚至更加困难。特蕾西实际上也经历过性高潮。她解释道:
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我觉得快乐。这家伙对我干这种事真是该死,但我和他同样有罪,因为我喜欢这样。
在此以前我就听过这种话,但此次听了仍然感到心痛。我把在她以前对别人说过的话又说给她听:
喜欢这种刺激并没有错。你的身体按照生物学的程序设计,就是喜欢这种感觉的。但是对这种事有快感这一事实并不等于说他做对了,你做错了。你仍然是受害者。不管你的感觉如何,作为一个成年人,控制自己是他的责任。
对许多乱伦的受害者来说,还有一条独有的罪:将父亲从母亲身边夺走。父—女关系的受害者常常谈起觉得自己像“另外一个女人”。自然,这就使她们甚至更加难于从原本有理由帮助她们的惟一的人—母亲那儿寻求帮助。与此相反,她们感到自己在背叛母亲,这又给自己的内心世界增加了一层负罪感。
第七章 终极背叛荒谬的妒忌:“你是属于我的”
乱伦以一种荒诞而极端的方式将受害者与侵害者融为一体。尤其在父—女的乱伦关系中,父亲常常狂恋着女儿,荒谬地妒忌她的男友,他可能打她,或用言语虐待她,让她明白她只属于一个男人:爸爸。
这种狂恋极大地扭曲了童年及青春期的正常发展阶段。乱伦的受害者非但不能逐渐脱离父母的控制,反而日益依附于侵害者。
就特蕾西的情况而言,她知道父亲的妒忌是荒谬的,但却意识不到这种妒忌是多么残忍无耻。因为她把它错当成对她的爱情了。乱伦的受害者把狂恋错当成爱情,这种情况很普遍。这不仅严重地妨碍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一事实,而且此后会破坏他们对爱情生活的憧憬。
许多家长都体验过当孩子与外人约会并与其建立亲密关系时自己的那种焦虑心情。但是有乱伦行为的父亲却将女儿人生的这一阶段当做女儿对自己的背叛、拒绝、不忠,甚至遗弃。特蕾西父亲做出的反应就是典型的:怒火中烧、破口大骂、实施报复。
我外出约会不回来,他就不睡觉等着我。回家后他就严词审问我,没完没了地问我同谁出去的,同他都做了些什么,让他摸我什么地方了,让没让他把舌头伸到我的嘴里。如果他看到我同男友吻别,他就会从家里冲出来,骂着“流浪鬼”,把人家吓跑。
当特蕾西的父亲用卑鄙下流的语言骂她的时候,他的行为同许多乱伦的父亲的行为如出一辙:把自己身上的缺点、邪恶和罪责统统推到女儿身上。但是还有的侵害者则以柔的一手束缚受害者,使孩子更加难以解决罪与爱之间的情感冲突。
“你是我的全部生命”
道格,46岁,一个瘦小、紧张不安的男机械师,因多种性功能障碍,包括反复发作的阳萎,来找我。从7岁到18岁,他一直受到来自母亲的性骚扰。
她总是抚摸我的生殖器,挑起我的性欲。但我总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性关系。每次她都让我对她做同样的事,她对我说,我是她的全部生命,这是她对我表示爱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是,现在每当接近一个女人的时候,我都觉得对不起母亲。
道格同母亲共同保守的那个巨大的秘密把他同母亲紧紧拴在了一起。她的这种病态行为也许让他迷惑不解,但她所发出的信息则是明确的:她是他生命中惟一的女人。这种信息在很多方面同乱伦本身具有同样的危害。结果,当他试图摆脱并且同别的女人结成成年人的关系时,不贞感和负罪感便极大地伤害了他的精神健康和性能力。
盖住火山口
许多受害者得以熬过早期乱伦痛苦的惟一方法就是戴上心理上的假面具,将这些记忆深埋于清醒的意识之下,这样它们即使不会永远,也会多年不在心间浮现。
由于某些特殊的生活事件,乱伦的记忆常常会突然回潮。我有的病人曾报告说,有关乱伦的记忆会因为某些事情而诱发,诸如孩子的出生、结婚、家庭成员的死亡、媒体有关乱伦的报道,或梦中重温乱伦的痛苦等。
受害者因其他问题而进行心理治疗时,此类记忆便会浮出水面,这种现象也是普遍的,尽管许多受害者如果没有心理医师的诱导,从来不会提及乱伦。
即使这类记忆出现了,许多受害者也会张惶失措,并以拒不相信的态度,极尽抹杀之能事。我作为一名心理医师曾有过的最富于戏剧性的情感经历就是46岁的朱莉的治疗过程。朱莉是供职于洛杉矶一家大型研究中心的生物化学博士。她听了我一次讨论乱伦问题的电台节目以后来找我。她向我吐露曾在8岁至15岁期间受到过哥哥的性骚扰。
我一直生活在这些可怕的幻觉之中,觉得自己要死了、疯了,在疯人院里了此一生等等。最近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床上蒙着头,除了上班以外从来不出门。在上班的地方我也几乎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大家都对我十分担心。我清楚这全同哥哥有关,然而就是说不出口,觉得快要淹死在这里面了。
朱莉十分脆弱,显然正处在严重的精神崩溃的边缘,她会歇斯底里地笑上一分钟,然后神经质地呜咽起来,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感。
我哥哥头一次强奸我时,我只有8岁。他14岁了,又比他的实际年龄强壮。打那以后他每星期至少要强迫我三四次。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于我有点儿想一死了之。现在我明白了他那时是疯了,因为他会把我绑起来,用刀子、剪子、刮胡刀、螺丝刀,以及他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折磨我。我存活下来的惟一办法就是假定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
我问朱莉,当这种恐怖发生时,她的父母在哪儿。
我压根不敢把汤米对我做的任何事情告诉父母,因为他威胁说如果我这样做他就杀了我。我信了他的话。我爸爸是个律师,连同周末在内,天天工作16小时。我妈妈是个吸毒者。他们俩都没有保护过我。爸爸能在家待上的那几个小时他希望能安宁平静地度过,并且希望我能照顾一下妈妈。我的整个童年,除了痛苦以外是一片空白。
朱莉受到了严重伤害,很害怕接受心理治疗,但后来她还是鼓起勇气,参加了我的一个乱伦受害者的小组。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她努力医治哥哥留给她的性虐待的创伤。在这几个月里她的情感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不再感到好像是在歇斯底里和沮丧压抑之间走钢丝了。然而,尽管她有了进步,我的本能告诉我,还缺少什么东西,在她的内心还有某种阴暗隐晦的东西在溃烂着。
一天晚上她心烦意乱地来到了小组。她在此前有一次让她恐惧的回忆。
几个晚上以前,我清楚地想起母亲逼我与她口交,我一定是疯了。当然关于这些事情我也会想到哥哥。我母亲根本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当然她从来离不开毒品,但却压根不会让我干这种事。我快控制不住自己了,苏珊,你得送我进精神病院了。
我说:“亲爱的,如果这种事情你想到了哥哥,怎么可能治疗得这么有成效呢?”她听了这话觉得有些道理。我又接着说:“你知道,这种事情一般不会出自人们的想像。如果你现在记得是同母亲干的这种事,那是因为你比以前坚强了—你现在更有能力对付这种事了。”
我告诉朱莉,她的这种潜意识对她有着很好的保护作用。如果她是在我头一次见她时那种非常脆弱的情况下回忆起这件事的,就可能精神彻底崩溃。但是通过在治疗组的努力,她的情感世界变得更加稳定了。她的潜意识使得这种受到压抑的记忆重新浮出水面,因为她现在能够对付它了。
极少有人谈到过母—女间的乱伦,可我至少已经治疗过十几个此类受害者。此种乱伦的动机似乎是对柔情、身体接触和关爱的一种古怪而扭曲的渴求。能够以此种方式破坏正常母女关系的母亲通常都是极度心理失常者,并且往往还是精神病人。
正是朱莉拼命想压抑她记忆的举动把她推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但是,尽管这些记忆是令人痛苦不安的,将其发泄出来却是她逐步康复的关键。
双重人生
乱伦的受害者常常会成为熟练的儿童演员。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有着太多的恐惧、迷惘、忧伤、孤独和隔阂,这样他们在与外界打交道时便会培植出一个假我,装出一副似乎一切良好正常的样子。特蕾西对此有十分深刻的理解,她谈起了“表面”上的自己:
我觉得在自己的体内似乎有两个人。在朋友面前我是开朗友好的,但一回到公寓里,我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遁世者。我会不停地大哭。我讨厌和家里的人来往,因为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你不知道总得扮演这两个角色有多累。有时我真觉得一点儿劲都没了。
丹也能够得奥斯卡奖了,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对父亲晚上对我做的那些事有深深的罪恶感。我觉得自己是个怪物,我恨自己,但却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家里没人能够理解。然后,突然间,我不再梦想什么了,甚至也不哭了。我会装得像个快乐的孩子,我是班上的滑稽小丑,还是很好的钢琴手,我也乐于请客……为了让大家喜欢我,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