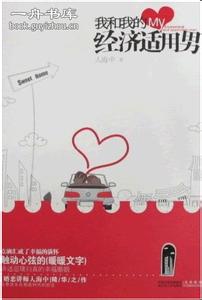经济史的趣味-第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条。
Milton Friedman (19122006),1976诺贝尔奖
真的是这样吗?有两种见解在争辩。主张上述见解的,是1976年诺贝尔奖得主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的基本论点是货币数量说:购银法案把白银价格拉高后,中国币的汇率被迫升值,造成奇特的「银贵金贱」(黄金的价格相对地贬低),造成出口困难、贸易赤字更严重。白银被美国吸走后,货币供给减少,政府的财政必然更困难,只能扩大债务让预算赤字化。蒋介石政府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打算在1934年10月脱离银本位,但此事拖到1年后(1935年11月3日)才正式宣布,终止了有几百年历史的银本位,改采法币制(纸钞制)。
脱离银本位后,政府印钞票时,就可以不必顾及白银的准备数量,导致过度印钞,造成物价膨涨。以上海为例,19314年间因购银法案的传闻,批发物价下跌23%,但在19345年间只下跌1%。1935年底改采法币制后,19357年间的物价上涨24%。雪上加霜的是,1937年7月日军侵入华北,中日战争爆发后军费激增。此事虽与美国的购银法案无关,但国民政府在脱离银本位后,大量印钞应付各方需求。在8年抗战期间(193745),货币发行量增加300倍,物价上涨得更快,将近1;600倍,平均每年上涨150%。Friedman说,中国经济先受到购银法案的打击,接着是1937年的中日战争,之后又有19459的国共战争。整个检讨起来,购银法案应该为国民政府失掉大陆,负起重大的初始责任。
Friedman言重了。他只根据一些表面事实,做了过度的推论。购银法案确实吸走不少中国银子,引发通商口岸的商业恐慌。但若要说购银法案对庞大的中国经济,产生致命的影响,那就需要更明确的证据与深度分析。有另一派见解,例如Brandt and Sargent(1988),就明白反对这种货币数量说的推论。但他们的分析,还是停留在宏观的总体统计数字解说,没有用数理模型与统计分析,去探讨其它因素。
Thomas Sargent
我们尝试用反事实推论法,透过较严谨的模型推论与计量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不支持Friedman的见解。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有较重大影响的因素,并非外来的购银法案,而是19317年间水旱灾的长期广泛影响。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受水旱灾害的程度如下:1931年有20。1%,1932年17。5%,1933年15。4%,1934(购银法案那年)38。9%,1935年9。8%,1936年11。3%,1937年19。3%。购银法案对中国的冲击确实不少,但激烈的程度是短暂的,也只限于工商业。相对地,19317年间的水旱灾,对以农立国的经济,所产生的冲击才是广泛深刻的。
参考书目
Brandt; Loren and Thomas Sargent (1989): “Interpreting new evidence about China and U。S。 silver purchases”; Journal of Moary Economics; 23(1):3151。
Friedman; Milton (1992): “Franklin D; Roosevelt; silver; and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1):6283。 ment by Rawski 1993; 101(4):7558。
Ho; T。C。; C。 Lai and J。 Gau (2010):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Silver Purchase Act (1934) on the Chinese Economy”; working paper。
10明清的税制与贪污行为
「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这类的说法,表示中国的领土过广,朝廷的旨意不容易在基层落实。但另一方面,从文官考试、军队调动、牢狱审判、治理水患、蝗灾、救灾蠲免,又可看出中央集权的实效面。领土过广就必须分治,以明代为例,除了有布政司、州府县的层级组织,还派皇子分驻各地申张皇权。简言之,与政治直接相关的事项(如考试、军队、救灾),帝国组织有它的效率面,但对经济性与生活性的事项(如课税),地方政府的力量就明显强过中央。
税制牵涉实质的利益,是中央与地方的重要关怀,但立场却又对立:中央政府提出既定的税收额,地方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向地方百姓超额收税,民间则贿赂官员来逃税。统治者、地方政府、民间百姓三方面的斗法,让贪污(贿赂)成为追求均衡点的必然手段与过程:中央要监督地方官员不让他们贪污,但地方官员的公费有限,必须超额征税才能让行政体系运作,民间有能力者必须靠贿赂才能减少课征额,小民百姓只好承受额内与额外的超重负担。
中央为了减少贪污贿赂,派出监察御史巡查,一方面提高监督权,二方面减少民怨。但从明清的税制史来看,答案是失望的:贪污贿赂盛行,中央的监督效果相当有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似乎是税制架构与政治结构的必然结果。贪污甚至是一种合理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润滑剂,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其中的两项关键点是:(1)监督的能力与成本,(2)惩罚的严厉度与有效度。
统治者的短期财政目标,是每年的税收极大化。长期目标是扩大税源与税基,最理想的状态,是「从鹅身上愈拔愈多毛,但鹅还不会乱叫」。其实是鹅不敢乱叫,只希望少拔一点毛。真的拔毛者是地方官员,「该拔多少」与「能拔多少」之间,就由贿赂额的高低来决定。
贪污有三种主要形式。(1)官员蓄意低估纳税者的应税额(高额低收),缴税者用现金或其它好处回报。这是官员与百姓互利,牺牲统治者利益的做法,在两种情况下较易出现:(a)税源难以估算,或估算的成本过高时;(b)纳税者的应缴额相当大,贿赂比缴税更合算时。(2)官员监守自盗,从税收内中饱私囊,通常发生在中央对地方控管不足时。(3)超额征收: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或自身利益,官员向缴税者收取超过规定的税额,长期而言这会损害地方税源引发民怨。
这些事情古今中外从未断绝,统治者的对策不外四种。(1)税官轮派制,(2)加强罚则,(3)严厉监督,(4)提高官员薪资(养廉)。这些方法都会增加税收成本。如果国家的每100元税收中,行政成本与监督成本超过50元,那还不如甘脆让地方官员贪污20元,来得省事有效率,国家的收入反而更多。
愈偏远的省份,基层税收愈容易贪污,原因很简单:监督不易,成本太高。另一个原因是:个别的贪污事小,因为金额有限为害不大;贪污通常是勾结性的、结构性的、共犯性的,贪污者的共生性与团结性,才是问题的根本。
从百姓的立场来说,当课税过高时,应税者有几种对策:(1)逃离本地,(2)隐匿应税的资产,(3)贿赂官员减免税额,(4)团结抗税(官逼民反)。整体而言,影响贪污程度的要素有三。(1)领土的大小:小国寡民不易贪污,如香港与新加坡;幅员广大的中国与俄国,贪污率必然较高。(2)地主的实力:个别的中小农民不易逃税,贵族地主必然贿赂或抗税。(3)统治者的棍子有多长、有多狠:中央政府是否愿意付出监督与惩罚的高成本。
明朝的鱼鳞图册
以下举实例说明,明清时期的贪污为何无法有效压制。第一个困难是官员人数太多,16世纪时中国约有3。6万官员,法国约有1。2万人。这么庞大的官僚体系,分布在这么广大的领土内,有效监督的困难与成本可想而知。第二个困难,反过来说,是官员人数和人口总数的比例太低:16世纪中国的3。6万官员要管理1。5亿人口,比例约14;200,而法国的比例约11;250。这表示明代的官员,很难确实掌握可税对象的实际价值,只能根据鱼鳞图册和黄册,这类几十年才修订的老旧税收资料。
再举一例,以规定国家财政收支的《会计录》来说,明代三百多年间,总共才修订三次(洪武、弘治、万历),这么长的间隔,怎能掌握社会财富的变化?再以清丈田亩为例,张居正当国时雄霸天下,但真正清丈的,也只不过是山西和北京少数地方。「每丈必反」已成常态,清朝在17世纪时,也试过三次清丈田亩,皆未成功。这表示明清时期,隐匿财产田亩避税的事态相当严重,愈有田产的人愈有办法逃税。据估算,20世纪初期时,约有33%到40%的家户,完全未缴土地税。
明朝的黄册
这么严重的逃税,难道地方税官不知情吗?逃税者必然贿赂,收税者必然贪污。监察系统说起来严密,执行起来严松不一。被举报者占贪污者的比例太低,因严重贪污而被革职者,19世纪时只有6%9%。
为什么不雷厉风行斩草除根呢?主因有好几项。(1)官员薪资太低,地方的行政经费太少,中央无法充份供应,只好纵容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2)如前所述,地广人多难以监督,因贪污而治罪者,通常是因为事态严重,中小型的贪污很少判刑。(3)如前所述,贪污是结构性的共犯,贪污群之间的关系紧密,团结对外难以清除,若强力清除,反而导致地方事务停顿。(4)因而在文化上与社会上,对贪污的宽容度较西方国家松缓许多。(5)交通不便讯息传达困难,若非重大事件,很少动用快速的驿站体系,造成监督与惩处的成本高居不下。
逃漏税的严重性,其实就是反映贪污的普及性。以171226年间,江南拖欠税款(其实就是逃漏税)的比例来看,1千万两的拖欠额中,欠税者承认的数额只有3%,其余的97%「仍在调查中」。要调查到什么时候?最后能追缴出多少?雍正皇帝发了怒火要清查此事,1728年的调查结果是:(1)拖欠税额中,应由高层官员负责的只有0。3%。(2)要由低阶官员和收税者负责的有41%。(3)要由地方士绅负责的有3。9%。(4)纳税者的逃漏有54。7%。重点在第(4)项:为什么能逃掉55%的税?应该是官员的查税不力与纵容。再追问下去,为什么会有这个局面,答案呼之欲出:应纳税者贿赂,查税者收贿。江南富庶地区有一半的税被逃掉,国家的税收怎么够用?
雍正皇帝随即展开税制改革,这些事情的面向复杂,其中与贪污相关的改善措施,是增加官员薪资,称为养廉银。平均而言,加薪最高的地区是四川(29。7%),这是偏远省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次是贵州(加薪11%),这也是偏远地区。奉天、山东、福建的加薪额度约9%10%,离中央政府较近的省份(河南、江苏),只加5。4%。有了养廉银制度后,税务改革的效果好吗?算得上好的是核心省份:山西、河南、陜西、直隶、贵州,偏远地区的效果仍旧有限,主因仍是监督困难、惩罚的效果难持久。
参考书目
Kiser; Edgar and Xiaoxi Tong (1992): “Determinants of the amount and type of corruption in state fiscal bureaucracies: an analysi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5(3):33031。
11明清时期的贪污规模推估
贪污是古今中外难解的大问题,这种事的严重程度,只能有个主观的判断,怎么可能估算出全国性的具体数额?难道你能估算出1900年代初期,广州市的贪污规模?这个念头听起来可笑,但有些经济学者试着用理论模型在推估,姑且一听。
税务方面的贪污,对经济成长有不同层面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税收减少,以及政府的开支减少。明清政府的可用资源降低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