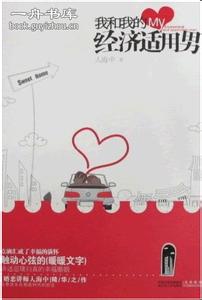����ʷ��Ȥζ-��4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Ժ����ѷǴ�ֻ��ɧ�Ŷ��ѡ�����ū������IJ����أ��ǻ����αغķ�4251ƪ�ľ�����۴��£�
��ū
��3�����õġ����͡���ʮ�����������أ�����������ū���ֱߣ��������������������ﹲ����ū�����Խ�������Ůϸ��Ϊ���������������֡���������ū�����������֡������빫�����飬�����ū���������ɼ�����ū���ֱߡ��������ʱ�������飿���۱��͡��أ�������ū���ֱߣ�����������������ּ��������ʹ�����顣��������Ϊ���ݽϼ�����ʹ����Ϊ����ū���ֱߡ���������ʱ�������͡��ļ�����������������������ܲ⡣���õġ����͡����Ǹ��ݡ����顷������������������ɾ���ɲ������顷��ȱ�ݡ�23���Ŀ�ȫ����Ҫ���ƣ������������ޡ��͡�ʱ��������δⶡ��������ɴ˿�֪���۱�ʼ����֮�ۣ�����������ū�ֱߡ�
��Ϊʲô����ʽ�����ڣ�141ƪ����ֻ����ƪ̸����ū���⣬���ڻ���ʱ�Ŵ�����۴��£�������Ϊ��ʽ�Ļ��飬������������Ϊ���ᣬ������ѧ���������۵���ڿ�����˰����������ϣ�����ū����ֻ����Ծ�Ե�Ӧ�𣨵�12��16��38ƪ�������ڻ���ʱ����Ȼɣ���һ��ʼ��̸��ū���⣬��ѧ�Ͳ������ط����ˡ�����ʽ����ʱ���ڡ�12�DZߡ��͡�16�ع㡵�ڣ�������ѧ��ɣ���Դ𣬵��ˡ�38������ʱ������ȫ������Ӧ��һ���������������٣������������ǵ�����ѱ�����ϣ�������4252ƪ�ھ���ȫû���ԣ�ֻ����ѧ��ɣ���˫��������š�
5���ط�ʽ������
�����ڡ�60���ۡ�˵����������������ǡ��������Ӳ�Ϊ���ԡ��������п��������Ͽ����������������Dz���������ѧ֮һ�����ѵ�ʱ���龰����ͬ���ĺ�����������Ҳ��������Լ��ļ��⡣����������ʱ��7149��BC����Ϊ�ɣ��ʵ۵��̴ӹ٣���ʷ�ƻ���ϰ��������п���������ʱ�IJ�ʿ���ӣ�����ʦ���հ��ֻ������棩������®��̫��ة����������ƽ�¼��Լ�����������ȷ֪�������������ʽ���Լ�¼��Ӧ������̫ʷ��ִ�ơ������飿������ȴ��ޡ�˵���������顸��ʱڵ�ѣ����������ġ����Ի���������δ���ܼ�����Щ��¼�����ļ����ǿ�����ת���ġ������飿������ȴ��ޡ��ƻ�������������֮�飬������Ŀ���������ѣ��������ԣ������Ծ����ң���һ��֮���ɡ�����仰˵���˻���д�������ۡ����ַ������ʡ�
Ŀǰ�������ۡ���õİ汾���o���ݵ�������Ϳ�������뺺����Զ�������Ĵ�������֪������������������ҵ�������֮һ���ƾٹ����ϵ���;��Զ����Ⱥ������ʷ��Ҳ����ò���Ӧ�е�У����������Щ���ֿ���ì�ܣ��������������Ļ��������磬��60���ۡ��롶���鹫����ȴ���Ի�������صľ��в��졣����Ի���������Ի�����µ�Ϊԭ�ģ����ô˶λ����͡������ۡ����Ӧ�IJ��ݱȽϣ����顷Ӧ�����д����Ĵ���Ȼ��Ҳ������ȫ�ų�������������ε�ɾ�ڡ�ijЩ�����ݵ�ĵط���Ҳ�����������ģ�������Щ��������Ϊ���鴫���ϵIJ�𣬵�Ҳ��Щ�ط������Ե��������硸��������š�����ɡ����������š���24���������ĵط�������Ҫ������֤��
ǰ���ᵽҦؾ˵������֮�飬�������������������֮�����������е���Ҳ������ǧ���ԣ�������������Ҳ�������������壬�����������ľ�ѧ��ͳ�йء���ʿ���������������ã�������ռ���֤���������С�Ԫ���Ժ��Ҳ�ʿ���С��¾䡹�����������������ԣ���֮�ڡ�Ӧ�����ѡ���25�ѡ���֮ʱ���˷��ѿ�������ʱ��С�ĺ���顷�����¾䣩����������ܵ������ķ��Ӱ�졣
�����ڻ�ԭ���������¼�Ĺ����У�������Լ������ۺͼ�����롣����������ɣ�����˼�����룬���Ҫ����Ļ������������������ɣ����ľ������硴10�̸����ġ������Ȼ���ԣ���������̾Ϣ�ɡ����͡�59���ۡ��ġ������Ȼ�ڲѣ��ľݶ����ԡ������������������20��֮�ࡣ��������Ҫ����ɣ��������ۣ��ַ���Ӧ�ð�����˵�Ǽ��˻������˷��У����Ƚϲ���ȥ���������۵㣬��Ϊ�ܴ�Ħ����ôǰ��һ�£�Ψ��ΨФ��Ҳ�����ס�
��˵�������ۡ��ĺ�벿�ǻ������죬Ҳ��������һ��˵������������Ȼ�����������۳���д���飬���ѵ۳����Ϲ٣��Լ���ʱ���������������������ѧ��Ҳһ�������˽��ڡ�����һ�����ǻ���δ�ظ���ô������������ͬʱ�������������������죬�Ե�ʱ˽�������ķ�����������ѵ��������±�Թ���µļ��ػ�����
�����Դ���һ���Ƕȣ����������ڴ����°벿��4259ƪ��ʱ����ʵĽ���̬�ȡ��ڡ�54����Ǐ���ɣ������۵�����ܵ����У�ת���������������ϡ������ʻ��൱�������ر�ǿ����������֮Ӧ������֮�项�������á���֪��Ĭ����ƈ�Ҷ�������������ѧ���������⣬һ��������������ҳ����۵ĸ��ݣ�����һ�����ƺ�Ҳ��û��Ҳ��ӣ�Ҫ����ѧ�Ĵ����У��������ɵĻ������Ƿ��ܰ��һ�ǡ����������������Ǵ����ŵ���ģ���Ϥ��������롶���飿�鷶������ѧ�ǣ�����������ϲ����ս��ĩ�ڵ�����̸��������ˣ������ء����˸�Ӧ����һ����������������������뵽������������ˡ��������������õ�ʵ�������ϣ������϶��Լ��ļ��⣬�ͺ����ײ������硣
Ȼ����ѧ��Ҳ����ʡ�͵ĵƣ�������֪ǰ��������������������飿�����洫���أ����������ι����Դ�������֮�����������Դ��У������꣬������������������ֹ�귴�ǣ���֮һ����δ�������������з�Ϊ�д�������ɶ���������������֣�����Ӽ���˵���⡣ܳ��δ�ϣ������Ⱥ����棬˽������֮������������ɡ����������壬������������治֪��ʦ�飬��Ϊ���ޡ���������������������گ��֮�������첻�Ҹ������졣��
�����ֱ����£���������������ѧӦ��ǣ����Ե÷dz��͵����������̡�˳�죬���������á����������ɱ�����Ͷ��������54��Ǐ����������ɣ�������壬ͬʱҲ�����Ե�˵�������ʳ������������������������б䣻���̲�������ˮ����ʱ����Ο����������֮ӦҲ��������54��Ǐ������ѧ�ڴ�����Ӱ��ɣ��������������ֹ��Ķ��ǣ������Ķ��߲�һ��������ᵽ��
�����Ǹ�����ѧ�ߣ����ؽ���ζԻ�ʱ����ȻҲ����ʶ�ؿ����Լ��ıʶˣ����ֵ͵���̬�ơ�������Ϊ�����ϵĸ�����ǰ����������Ҫ�����ֽ������ַ���д��26�������Ҫ���졶�����ۡ����°벿����Ӧ�ø����ر������ġ�
6����
���ĵ�ּ�����ں�ӦҦؾ���۵㣬˵�������ۡ����°벿��4259ƪ�����п����ǻ�������ġ�Ҧؾ���۵���ֱ���Եģ���û������ṹ�Ե�֤�ݣ�Ҳû���ⲿ���ڲ��������顣���Ĵӡ������ۡ����������ṹ����ĽǶȣ����������������Ӧ���Ĺ۵㡣�Ȼ�Ǹ���Ȥ�����⣬���ĵĻ���է��֮��Ҳ��Щ����������Ҫ��ȱʧ����������ȫ��Ľṹ�����������˴������ҳ�ϸ��֤�ݣ�������������⡣
��������෴���۵㣬˵�������ۡ�����������֮�䣬Ӧ�����л��Ĺ������ؼ��������Ƿ��л��ᡣҦؾ��������Ϊû�л��ᣬ��Ҫ�����ɡ�42��֮���������֡�������Ϊ�˶ο��������ģ�������½�����ѣ��������ģ����ڶϾ���Ӧ�������Ľ����ʽ�������ڵ���������µĶϾ䷨������֤����Ŀ������ڣ��������������֧�ֺܿ����й����ᣬ�����ǻ�������ģ�Ҳ���������������ԡ�
�������л��ᣬ�Ǿͻش������ĵĵ�һ�����ɣ�˫��������������⣩�����ǵĻش��ǣ�ة���ة��ʷ��δ��ϯ���ᣬ��ϯ���У���ʷ���ɣ��������������ʷ�����ˣ�����ѧ����ʮ�����£������������˻���٣���
�ڶ����ɵ㣬��4259ƪ�����⣬�������������ּ����ɡ��ǵģ�ɣ������ҪĿ�ģ���ϣ����ѧ��������֧�ַ������ţ���Ϊ���������ڡ�41ȡ�¡�ʱ���ж��ۣ����Ի������Ҫ���⣬��ת���������⣬��˫������ֲ��£�Թŭ��ɢ��
��������ū����ı��أ�Ϊ����141ƪ����ռ�ı������ֻࣨ����ƪ��������4259ƪ��ȴ��11ƪ�������ڵ��Ľ��������ۣ�����
���ĸ������ǣ�141ƪ�ڵ��ԴǼ�������ƪ֮���������Ծ�����ᣬ����4259ƪ�ڣ�ȴ���۵�ƽ�����ԣ���ƪ֮�������Ȼ��������Ϊ141ƪ���۵�������ӣ�������ֲ��ã����㲻���С���4252ƪ�е����ⵥһ���������⣩��5359ƪ������Ǵ�Ҫ�ģ��Ǹ����Ե���̸������ɣ�������Ҫ������˵��һ�����롴55�̵¡�����58گʥ����Щ����ʱ��ɣ���Ȼ������ѧ�ǵĶ��֣�������ȥ��Ȼ������Ȥ�����ԾͲ�����ɢ�ˡ�
���4259ƪ�Ƿ�Ϊ������������⣬���������һЩ�����Ե��۵㣬ϣ����������Ƕȵ����ۡ�
��¼����ة�����Ҫ����
ة�ǧ�������������ڵķ��Դ������٣��ڡ�29ɢ���㡵�����ε����͵Ļ����ڡ�31��ʯ����ͷ��һ�����е��������ڡ�39ִ����һ�����еı�������˶��ѡ�һ���������������γ��������ԣ���������Ϊ���ǻ������ϯ�����Դ�����Ҳ�Ϻ����鳣�顣Ȼ������ة��Ľ�ɫ�����ؽ�Ҫ����ʵ�������൱��Ҫ�Ĺ��ܣ�ֻ����Ϊ�����嵭�����ױ��˺��ԡ�
�ڡ�29ɢ���㡵��ǰ�����ڣ�ɣ�����ʵ�ѱ��������������¡����ĬȻ�������鱾�����Ե���Ϊֹ��ת̸���⣬����ة��ȴ�ٶ������������ɣ������ѿ����������·����ġ���ֻ�ᵭ��˵��һ�䣺��Ը��ɢ���㡹���������һ��������ӵĿռ䣬�ӵ�5��һֱ�۵���38�Σ���������֮�����Լ��ڼ����Ҫ����Щ���������ɣ����ʿƽ�յ���Ϊ��������ة����������ڹ���ʱ������ף�������������⣬ȴ����ʹɣ�����ѿ�����ة�����������������⣬���������������ֲ���ֱ˵�����������ֵ����������赶ɱ�ˡ�
��һ�����Ƶ����ӣ����ڡ�31��ʯ�����Σ�ة��˵��һ�����еĻ����ٶȽ�����������ѧ���������������ߣ�ɣ��������ʹ��˾����ȡ����֮�飬����������ѧ����ѷ֮������Ϊ������ȡҲ�����ع����о���������ѧ����������ΰ�ˣ���δ����������ʯ��ҽ����֮��Ҳ����
�������ѿ������ֳ�ة����ַ��������������飿��ǧ�ﴫ��˵�����ѵ۳���λ��������Ҽ�����������⣬ǧ���ة��λ�����ղ������ԡ����Դ���֮���������ڡ�60���ۡ���ĩ��Ҳʢ��ة�࣬˵�������ᴦ�У����Ҳ��ԣ�������ȥ�����գ����գ�����ة�����֡��ղ������ԡ��������������������ν赶ɱ�˵Ļ�������һ�¡����������赭д�������ַ�������������ɣ����ʿ�IJ������Լ�����������ѧ��֧�֣�ȷʵ��������������ȥ�������ָ߳����������Σ����ǡ����գ����գ�����
��ة����Ĵη��ԣ�����ȫ��������������۵㡣�ӡ�28������������41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