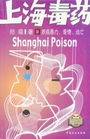深寒之巅上海滩-第6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果然不愧为吕当家的,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镇定自如!只是,现在不是讲派头的时候,对于他的反应,我不理解。
顾不得思考,反回过去拉住他就跑,可是他仍坐在那里不起来。
“快点啊,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我看着迅速蔓延的火势,急得焦头烂额,“聪明人不做湖涂事,你这是干嘛啊?”我走近他,高声嚷道。
“你的手怎么被铐上了?”这才注意到他另外那只手上铐着手铐,而手铐的另一头却是锁在庞大笨重的大铜的镶花里的。
真是的,一屋子的木制家俱,偏偏这张重笨的床却是无坚不摧的铜制品!
“你赶紧走,不用管我!”他说道,语气冰冷。
我看过他,心中一时怔忡。
“嗯,你等等!”想起那件很重要的事,抛下这句话便头也不回地赶紧向房外跑去。
迅速跑向三楼,对着房门我一脚踹开,整栋楼都火舌乱窜,而这间屋里却像是被隔离了似的,没有半点火星,看来老爷子还是吝惜自己的东西的,我扫了房中一圈,那个小铜人正放在醒目的博古架上,我来不及细想,冲过去就拿起小铜人。
“啊——”伴随着“兹——”地一声响,我尖叫了一声,那个小铜人随即滑落,掉在地上,发出“咚,咚咚”的几声滚动声响。
我咬着咬着牙摊开手,手掌有些焦黑,而且还起了一片大大的水泡,隐约还嗅到了些肉焦味。吕老爷子真是歹毒,居然将小铜人烧得炙热……再也不能耽搁,我顾不得痛疼,用衣服包住,拧开小铜人将钥匙取了出来。
“吕詹!”我高喊着冲进他的房间,却看到床上没有人,“吕詹——”我再次高喊了一声。
“咳——咳——我在这里,”他从床侧抬起头来,原来这房间已经浓烟弥漫,到处熏气呛人,他被锁住无法脱身,于是压低了身子匍匐于地板上。
我迅速扯过枕巾捂住鼻子,然后跑过去,他抬头看着我,眼神颇有震惊,更多的是感激,这样的眼神我以前从未在他身上看到过的。
绝望之后透出惊喜,此时,他的眼神传达给我的就是这样的信息,或许,这也正是我此时的写照,因为看到他信任的眼神,我也有逃出生天的庆幸感觉。
“吕詹,你等着!”我拿铜制钥匙就□手铐的锁孔里。
“咔嚓,”一声响,被扣上的锁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好在老爷子没有再玩其它的花招,要不以我的能力哪能办得到。
旁边的梁柱开始倒塌,周围的火势越来越大,烟雾越来越浓,而他的眉眼也是越缩越紧。
“走!”我把另一头还挂在铜床上的手铐一丢,拉着他就往外跑。
他却未发力,我被一股劲往后一扯,差点跌倒,转身一看,正对上他那双漆黑的眼眸,“谢谢你!”
我来气了,怒道:“大恩不言谢!你傻啊,现在逃命才是最重要的!”
他淡淡一笑,道:“我身上无力,你扶着我。”
我弯下腰来扶他,这才发现他手脚酥软,半点力气都没有。试了几次,仍是无力。
“怎么回事?”这下我是真急了,老爷子的招也太狠了些吧!
他没有回答,只说道:“你自己先出去,我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我抿着唇看着他,眉头拧过,背朝他半蹲下来,“我背你下去!”
我背对着他,不知道听我此话后是何表情,只听他难以自控地“嗯”了一声,很是不满。
“别想太多了,现在逃命要紧,”我知道他是难为情,没有见他有动静,我干脆负上他的手臂,把他背了起来。
瞬间,感觉自己很伟大。
他可真重啊,我踉踉跄跄地总算把他背到了门口,腿一软,差点跪了下去,赶紧用手撑住了门栏这才没有跌倒下去,但触及之处灼热滚烫,手上传来的剧痛犹如千百根针扎过,全身毛发顿时竖立,豆大的汗水从额头直冒上来。
“你把我放下来,”说话间,他头一磕,倒在了我的肩上。我顿时觉得他身子一沉,“吕詹,吕詹,”我叫了两声,他竟然没有反应,怎么回事?不再作思考,我咬着牙半拖半背地将他负了出来。
楼梯口前,我看着一级一级的梯子,觉得好长,背着他,手扶着扶梯,艰难地往下挪动着,脚下又是一闪,“啊——”两人咚咚地滚了下来,所幸的是只滚了两三级台阶。
被摔着七浑八素,我揉了揉撞到的肩,咧着嘴“唉哟”了一声。
“嗯——”听到身旁的吕詹闷哼出声,这一摔,倒把他摔醒了来。
我再抬过头,看到上方火焰开始朝下面袭来,赶紧又摇了摇吕詹,“快醒醒,快醒醒!”
吕詹终于睁开了眼睛,他下意识地挪了挪手脚,对我说道:“我现在可以动了,扶我起来。”
我赶紧站起来扶他,还是很沉,不过比刚才好多了,他自己可以走动。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扶着他,一步一颤地终于走出了那栋火焰肆虐的大宅。
于是乎众人所看到的就是我们不离不弃,相互搀扶着逃出火场的感人场景。
“少爷,您可出来了,把我们急坏了!”见我们出来,一个管事跑过来,喜出望外地道。
“给我抬凳子来,”吕詹不说其它,吩咐让人给他抬了凳子。
“快,快,把靠椅搬过来,”下人们手脚迅速,立马不知道从哪里搬了凳子。吕詹坐下去靠住,像是闭目养神。看着他气定神闲的样子,我暗暗心惊,前面火纵大楼,他居然能如此悠闲地躺在靠椅上,像度假般地泰然自若,隔了一会儿,他抬起手来,说道:“其它人赶紧去灭火,”说话间还颇为虚弱。
“少爷,火势太猛,大家不敢进去呀!”管事无奈地吐着苦水。
“谁再唯唯诺诺的把谁剁了!”吕詹铿锵了些说道。
这样管事再也不敢多说话,慢跑着过去下答指令。
这时,阿来带了一队人急急跑了过来,“詹爷,你没事吧,我听说这边着火了,就赶紧过来……”说到这里,阿来顿住,眉头拧了拧,“詹爷,你中毒了?”
吕詹点点头,“是一点迷药,休息下就没事。”
我这才反应过来,怪不得刚才扶着他的时候浑身无力,原来他中了迷药,不禁震惊,这爷孙两在玩什么把戏,孙儿虐待祖父,祖父向孙儿下药!若不是亏得我,那吕詹还真要藏身火海?搞不懂,不管怎么说,吕詹都是吕老爷子的亲孙子啊,弄死亲孙子,对吕老爷子能有什么好处?
休息了一会儿,吕詹有了力气,他叫了声我的名字,我走过去,他便拉住我的手。
“呃,”被他恰好拉住烫伤的手掌,我禁不住痛哼了起来。
他发现我的疼痛,神志像清醒许多,从靠姿马上转为正坐着,轻轻摊开我的手掌,看到我手心红肿,不移目,却朗声吩咐道:“快叫医生来!”
然后很是心痛的细细察看,我只是让他轻轻摩挲着,站在他跟前,并未出声,许久,才听他喃喃出声,像是痛恨自己似的:“我这是干了些什么事!”
、100第九十九章 无心之过
吕詹站了起来,看着我,皱着眉疼惜地说道:“都是我的错,现在咎由自取,受到的惩罚就是不许我再碰你的手了,”说道将我打横抱起向后院走去。
“詹爷,你的毒?”阿来慌忙问道。
我一听,也赶紧说道:“我没事,自己可以走!”
“别动,”他对我说道,然后微微扭头对阿来说道:“药效过了。”果然好体质,刚才还体虚无力,休息片刻就精力充沛了。
我被安顿在离主宅不远的一栋白瓷小洋楼里。刚被吕詹放下不久,吕家的家用医生们便来了。心想医生们肯定在抱怨最近吕家风水不好,隔三岔五的便让他们登门拜访,而且都是三更半夜。
一个年轻医生过来,查看了我的伤势,直摇着头。
“怎么样?”吕詹见状赶紧问道,“有没有动到筋骨?”
“筋骨倒是没有伤到,只是烫伤得严重,十天半月是不能沾水的,而且天气较热,怕感染,”医生解释道,说起便让护士拿过药箱,准备为我处理伤口。
“会不会留疤?”
“幸亏只是伤在手心,应该不会留疤,不过这段时间一定要小心注意!”
“呃,”刚才双手火辣辣的已经麻木得失去知觉,现在医生开始为我处理伤口,针刺般的疼痛传来,我不禁哼了一声。
“你忍着点,伤口进了太多杂物,先得把杂物清理出来,然后再用酒精消毒,擦上药膏……”医生好心地讲解着,像科普一般,然而此时我却听得头皮发麻,令我对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很是担心。
我死死地咬着唇,然而还是难免发出闷哼的声音,吕詹看我疼痛难耐,一面小心地坐在我身旁,揽过我,一面向正在处理我伤口的医生说:“动作轻些!”
那医生想是和吕家关系不一般,看了我们两眼,又低下头接着为我处理伤口,不紧不慢地说道:“你自己受伤时还没有那么紧张呢!”说着像想到什么似的,又抬过头顽味地调侃一句:“吕大当家的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不淡定了?”
听他话说得轻漫,我暗暗心惊,在上海滩能这样态度和吕詹说话的人不多,他们的关系肯定非同寻常。
“你少废话!专心些!”吕詹有些发怒了。
“呃,”手上又传来剧痛,我眉头紧紧的拧过,眼泪都要出来了。
“浅小姐对不住了,他平日得罪我太多,今天就拿你开涮了,”这个年轻人给我道歉,却并不认错,反而说得理所当然。
吕詹听他的话后更是气得双眼紧眯,恶狠狠地瞪着他,说道:“萧戟,你要报仇,只管冲着我来,”然后又看了看我,声调便软了下来,说道:“这次就算了吧?”
可是那人却并不害怕,反而说了一句:“你也有今天!”
吕詹不和他计较,却连连说道:“你轻些,轻些,”然后在一旁帮我吹着凉气,以缓解我的疼痛。
“你忍着点,这个方法痛,但效果好,”那医生换了副严肃的口吻叮嘱了一声,便沾上透明液体往我手上涂,一股刺鼻的气味传来,不用想,那是酒精,我的手顿时如千百只虫子撕咬一般,锥扎疼痛,阵阵灼辣袭来,我有想撞墙的冲动,一头伏到吕詹的肩头处,吓得他又赶紧对萧戟说道轻些。那语气一会儿愤怒,极为生气,一会儿又像服软般的央求,我听着又觉得有些好笑。
微微抬起头来,看见吕詹的侧脸,太阳穴上有青筋显现出来。看他紧张的样子,我顿时明白老爷子为什么故意要将我的手烫伤,如果能用这灼辣的伤痛换来他对我的信任和自己的一条性命,那毫无疑问,肯定是值得的。
日子一天天过,天气虽然仍然炎热,但枝头的上已经出现了少许枯黄色的叶子,被风一吹,还零星地飘落下来。我坐在窗户前,打量着自己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的双手,想到每日换药时吕詹紧张的神情,我不禁心上暗暗作痛,一个如此矛盾的人!
“闻竹,好些了吗?”怔忡中,一个娇滴的声音传来,我抬头一看,正是沈碧清笑语盈盈地朝这边走过来。
我赶紧从椅子上起来,“原来是阿姐,快点坐,”一面吩咐杜鹃上茶。心中却在想外人都道我下毒毒害顾佳丽的事还没有了结,她却仍敢来同我交往,面上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看来这女人粉饰太平的功夫也甚为了得。
“你这手好些了吗?”她拉了拉我缠着纱布的手,很是心疼的问道。
“好多了,这些日子不再疼痛了,只是换药的时候还不太好受,萧医生说明天就可以不用包纱布了,”我看着杜鹃将送来的茶水搁在沈碧清面前。
“萧戟?”她听我说到萧医生,问道。
“你知道他?”想到那日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