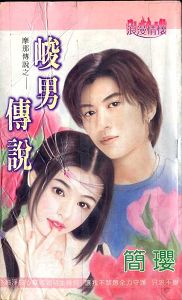小楼传说-第2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四岁的
便开始正式接客。因妈妈在她身上花的银子极多,I高于她。初时真真是卖笑不卖身,只与人诗词唱和,浅坐陪说几句,便算交差尽责了。
偏偏越是如此,身价越是拔高,来访之客,越是日夜不绝,文人们无论是否见过,总爱为她做几首诗,赞她才,品她貌,于是,不知不觉便名满江南,人称名妓。
只可惜,那样被世间男子环绕奉承讨好的繁华绮丽岁月,也不过数年。十八岁那一年,终究拖无可拖,终究要面对风尘女子必经的那一夜。
开苞的那一夜,恐怖得似一场永远做不尽的噩梦。
那个人的痴肥和苍老,那个人的鄙俗与疯狂,全都比不过他手里的银票更让妈妈感到真实。
那些曾为她吟唱的诗文,那些赞她冰清玉洁,霜华梅志的文字,全都虚幻如烟尘。
风尘中的女儿,再娇矜,再纵性,得快意时,也不过是那几年,几年之后,便是世人脚下泥尘,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娼妓。
还没满二十岁,她已经苍老了。
青春女儿多无尽,烟柳楼头有新人。
哪里的清倌人长得美,哪里新来了一位姑娘,原是某某候府坏了事,发卖出来的,正经的候门千金,金玉之体,听说还通文墨,擅音律……
流言从来不曾少过。新人从来不曾少过,江南之地,美女从来不曾少过。
还没满二十岁,门庭已是冷落稀。
妈妈冷眼中,姐妹冷语中,她拭尽了泪,抱起琵琶,歌之舞之欲语还休欲拒还迎。
苏眉第二次扬名时。不为才名,不为出身,不为清华,不为玉洁,而为媚态。
人说苏眉真妩媚,人说烟柳楼中妙人儿……
那些略显轻眺地词句。讲的不是那若干年前,身在风尘而不染尘的清洁女子,说的只是个极尽丑态,做尽媚姿,不过想挽住青春最后一点流光的可怜女人。
这样活下去,这样极力营造着繁华活下去,也并不知道,这么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前路。到底有什么?
那时,她见到了狄爷。
其实。初见的缘,极浅。极浅,浅得,日后再遇,要经过多次提醒,才能记起当初。
记得他似乎是一家大钱庄的幕后大老板,从外地前来巡视本地生意。钱庄上上下下,恭敬奉迎服侍,唯恐不周到。
挑最好的酒楼。点最好地酒菜,叫了全城最有名的歌姬舞女戏子献艺。
她是风尘娼妓。却是城中公认,舞技最好的女子。
她一日,她不过是在高台上,为了下方那个被簇拥着在中间的,面目模糊的贵人做了一舞。
没有事后的陪酒陪宴,没有夜晚地香帖请柬。一舞之后,不过是听到下面掌声一片,不过是事后,那钱庄掌柜,特意亲自送重金相酬,称是狄爷赞她舞得好。
当年的相遇,仅仅如此。
甚至,那不能称作是相遇。
她甚至不曾真正看清过他,又如何去记得他。
而数年之后,他却找到了已历经多个主人,辗转十余地的她。
二十一岁,知府大人闻艳名而赎她出楼,不为纳妾,不为收房,只为当做礼物,送给上司。后来,她被这位上司又送给了自己的上司,再后来,又被这位上司的上司,送给了一位候爷,再被这位候爷在宴席上因一个赌约,送给了一位将军,后来将军手头紧了,便将她名送实卖地给了一个富商。
每换一个主人,她都曾有过得宠的岁月,每换一个主人,都曾极喜爱她,呵宠她。
然而,她到底是个娼妓,连当妾都恐污了官宦之家的体面。到底还有许多许多更重要的理由,可以将她转手给其他人。
也曾有过主人分别时依依不舍,也曾有过离去时,主人执手叮咛,也曾有过,我实不舍得你,这原是为了你将来打算的所谓衷心之言。
而她,哭过,怨过,恨过,尝试自尽过,到最后便也看淡看轻了。分手时,可以对旧主人哭得肝肠寸断,转过身,再对新主人,笑得极尽媚姿。
她要的,只不过是活下去,只不过是再一次被送被卖之前,可以活得好一些。
又或者,要感激老天,让她到了这个年岁,还有被送被卖地价值。
就在她跟随富商的第二个月,狄九找到了她。
那日,天极高,云极淡,那人黑衣黑马,策骑而来,长鞭掀开她地桥帘,目光如电地望着她,声音里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喜欢:“当日观你一舞,怎生得忘,我终于找到你了。”
他与富商谈了什么,做了什么样的交易,她不知道,总之,最后,她跟着他走了。
这样地交换,这样的易主,她也习惯了,只是,这一次,有些不同。
狄爷和所有人都不同。
他把卖身契还给她,他给她置了庄园田产。他对她说,我不会常住你这,但有空时会常来,如果连续三个月,我都没有来,就是我死了,这里的一切,可保你安然渡日。
她有了自由,她有了产业,然而,一个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女人,若没有一个男人,帮忙支撑门户,这样的产业又如何能保全一世。
依附他,顺从他,讨好他,不过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不过是一种回报客人的尽职行为。
然而,他真的是不同地。
他从来没有打过她,没有骂过她,没有对她颐指气使。
他待她客气而温和。
他不会诸多诡异而疯狂的念头或要求,就是床弟之间,他地索求也并不多,方式也始终是温和的。
他常会有些名贵的东西送她,有时也陪她看看花,听她弹弹琴。
他一个月只会来几天,没来的时候,从不拘束她,只派人照顾她,保护她,却绝无监视限制的意思。
他不在,她自由自在,他来了,她也并不会感到拘束和不安。
然而,她始终不明白,当年一舞之缘,他为何寻她?
初时她也曾以为是迷恋,是又一个裙
。然而,很快,她知道,绝不是。
他看她的眼神,从无疯狂,从无热情,永远清明而无温度。
他待她的态度,太过客气温和,便也显得冷淡疏远了。
然而,他又与她极亲密。
床弟间接受她的服侍,日常生活,接受她最亲近的照料。
他来得很少,但只要来了,做什么都不避她。
翻看文书,批示文案,传送命令,从来不主动叫她回避。
以前也曾侍奉过大官,服侍过贵人,哪一次议事,不让闲杂人等退避,又有哪一次,她这个受宠的美姬,不在所谓闲杂人等之列呢。
然而,与他在一起,从没有这种被驱离,被当成外人,被防范的感觉。
这样地被尊重,被相信,是一种让人觉得极舒服的事。
即使她知道,他其实也未必是真的信他。
只是他会很注意,如果是不该当着别人面做的事,就自己先做好,不要真正当了面再来回避。
也许这只是小节,然而,这样的一些小节,有的时候,却真正可以让下属甘心一世忠诚。
她曾见过他与下属相处。赏罚明决而无人不服。做得对了,他一句淡淡激赏,便可令人热血沸腾,做得不好,他固然重责不宽,然而事后轻轻说一句:“下一次。别再让我失望。”便可叫人慨然起誓,绝不再犯。
她还知道,他是个武林高手。
他喜欢在月下舞剑,而她,即使不懂武,也会因那明月下灿烂地光华,飞跃的身姿而不忍转动目光。
她甚至见过,他和下属交手。
或者。那不叫交手,而叫指点。
印象中,好象从没有谁能在他手上撑过半柱香的时间,然而即使被他打得惨不忍睹,仍是一件激奋的快事。他每一次击败了对手,便会就下属的武功做出指点。虽然大多只是寥寥数语,并不着意,却总能让别人露出震动惊喜的表情,连失败的落寞也一扫而空。
有时,对武功好手他会微笑说:“怪不得他们几个服你,果真好身手。”即使是败给了他,听到这样的评语,也会感到光荣。
有时,对于落败太快功力稍浅地年轻下属,他会欣然说:“这么年轻刚出师不久。就能接我三招,真个不易。这样灵活聪明,你师父以前常常夸你吧?”
常常一句话。便可以叫一个本来沮丧的少年,呵呵傻笑全身都生起力量来。
然而,他这样能干,这样能得到下属的忠心,她却知道,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即使是在少数来这里与她共度的日子里,他也并不悠闲。有多少次半夜被传讯的人叫醒,有多少回。看到有人满头大汗满脸惊惶地冲进来。有多少次,看到别人喘息而颤抖着把那些文书递到他地手中。有多少回,听到有人失控地问:“怎么办?”
她知道,他似乎有很多难题,很多难关,很多压力。然而,每一次,他总是淡淡应付,总是随便三言两语,几个眼神,就能让那些惊惶失措的部下重又镇定下来
然而,她知道,他不是神。
所以,他会彻夜地翻阅文书,他会整夜地思考批示,他会被半夜从她的身边叫起来,上马去奔驰千百里,然后在数日后,带一身鲜血和风尘回来。
那样地忙碌,那样地奔波,那样地操劳,那样几乎没有宁日。
他总说,我闲时会来看看你。
然而,如果在她身边时都还只是闲时,那么忙时到底是什么样子,她几乎不能想象。
他已经不年轻了,然后,男人是不怕老的吧?所以风刀霜剑刻过的眉和眼,才有一种叫人心折的成熟和沧桑。
他还能拼,他还能打,他似乎还能应付一切难关,只除了,他难以安睡。
他睡眠即少且浅,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立刻醒过来。或者说,在和她在一起时,他似乎从来不曾睡过。每一次床弟温存之后,她总是在他之前就睡着了,而每一个夜半惊醒的时刻,他似乎从来都是清醒的。
也曾劝过他,多睡一会,多休息一些。他只是淡淡笑答,我素来睡得少,习惯了。
也曾寻了那安神宁气助眠的药来,细细地说了,小心地奉上。
而他只是呆了一呆,然后接过来,眉也不皱一下地喝下去,然后笑笑,轻轻说:“喝药没用的,我不过是睡不着,也不碍着什么,我地身子你不用操心了。”
他总是极有精神的,从来不显出疲态来,即使是一夜又一夜地睡不着,即使是一桩又一桩地事压下来,他也依旧好象不会累,不会倦一般。
然而,她知道,他不是铁打的身子。她知道,就算是真正武功绝世地人物,也经不起那样长长久久地不眠不休。
他从来不累,他从来安然自若地面对一切,可是她却总觉得,他就象一根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终有一日,会把自己给烧得尽了。
后来,那一天,他真的病了。
第五部(魔主篇下卷)
第一百一十一章 … 那夜烟华
那日他难得闲逸,带了她去湖上泛舟。
还记得江上风清日朗,还记得来往渔舟穿梭,看那江景,享那微风,她笨手笨脚学渔娘撒网,险险掉入水中,却跌入他的怀中,他信手挥洒间,就象凭空有无形的手擒捉,把那活蹦乱跳的鱼儿送到她手里,害得她又惊又慌且喜且笑。
那一日,他们竟从午后一直游玩到了日暮时分。
夕阳之下,远山近水,美得直可入画图,那些渔歌晚唱,芦苇荡舟,总可悄悄激起她那被苍凉世态渐渐冰冷的心湖。
纵然只是应酬,只是尽责,只是想要尽量活得好,那样的夕阳微风下,心中总还是有些温柔之意,感恩之情的。
悄悄偎入他的怀抱,低声地说着极亲近极甜美的话,望着那落日下越发看不尽的重重芦苇,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