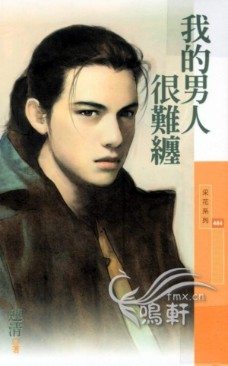我的房东叫别扭第二季-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彻底绝交!我再也不认识你,你也别跟别人说你认识我!狭路相逢就当陌生人!”
泡泡甩完这几句丧心病狂的狠话,转身就往楼上跑。跑了一步又返回我跟前,出其不意地狠狠踹了我小腿一脚,傲娇显摆地骂道:“你才是黑社会,人家是P大的哲学博士!”
我哀号俯身,揉着乌青的小腿,眼睁睁看着无良泡儿消失在楼洞的尽头。妈的,这年头,良药苦口有糖衣,忠言逆耳遭脚踢!
航母不是黑社会。航母是哲学博士。擦,我终于不得不承认,在现实面前,我就是一个料事如神经病。而现实这个贱人,明显比我病得更重
第七集 找削
若干年后,如果你有幸读到赵大咪的传记,你会发现,2010年的夏天是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垂垂老矣的赵大咪(如果她还能有命活到那时候)一边用帕金森的手擦着嘴角流下的米汤,一边回忆起这个颇有些世界末日前兆的夏天里烤死人的气温时,她一定会觉得不寒而栗。
悲剧最开始常爱以一副混淆视听的喜剧腔调拉开帷幕。
潭柘寺之后,赵赵氏真的把赴美试床当作头等重要的事情来办了。一天无数电话催我。我只好以泱泱大国签证难办为理由无力地拖上一拖。
然而,才只拖了一天,险恶的赵赵氏就迫不及待地出招了。她私下给律师彭大树打了个电话。然后大嘴巴彭大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跟她详解了旅游签证办理的种种。然后赵赵氏没怎么听懂,但她只弄明白了一点:我在诓她。而这正是她找彭大树的初衷。再然后,赵赵氏软硬兼施,巴掌与甜枣齐飞,终于让我不得不答应做她那个馊主意的执行者。
正在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看要脱裤子拉磨转圈丢人丢出亚洲丢向世界时,一代东瀛浪人册那宗师按照计划从浙江杀到了北京。数数日子,正是潭柘寺之后的第三天。
据他伯父所说,宗师这次来北京只是看病来的。当然,戏霸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台词,我估计现在连他自己也快分不清了。入戏太深,野心太大,不疯魔不成活。
本来宗师的到来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我早不住在房东那儿,更不需要从中斡旋他们没事找抽型的父子关系。然而我却仍然难以避免被宗师的驾临所波及。因为就在宗师莅临帝都的第二天,老赵伉俪就瞒着我跟他私下见了面。至于这老二位到底是荣耀地获邀登门还是没脸地不请自到,到现在还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疑案。
总之,当我后知后觉地从戏霸那里惊闻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时,形势已经有了谁也挡不住的巨变:赵赵氏再也不想着要我出国试床了,她甚至已经完全放弃了房东这棵高枝,开始预谋着把邪恶的黑手再度伸向唯一可用的那棵大树。
我实在被好奇心折磨得死去活来。宗师到底对我爸妈说了什么,能将赵赵氏的一片痴心妄想杀个片甲不留。是一上来就把我的家乡贬低得体无完肤,还是把我这个无耻黑心儿数落地禽兽不如,抑或是他惯用的散财童子拍卖神功,用一串接一串由可喜最终变得可怕的数字将老赵两口子砸得不知今夕何夕。
但按理说,不管他使用以上哪一招,就凭老赵对家乡的挚爱、赵赵氏只准自己诋毁闺女的护犊以及宗师三句话就要狂飙一下的册那暴脾气,他们都应该打到见血才对。但是据说,据唯一的旁观者戏霸所说,宾主双方是在和谐友爱的美好氛围中开始并结束了这次会晤的,还顺便吃了顿黄海空运海鲜。鉴于赵赵氏吃完回来当晚就拉了肚子,特将这次会面史称为“拉稀外交”。
我放下影后的尊严,恬着脸问戏霸,宗师到底说了什么让我爹妈死心的?戏霸只晓得用一脸震惊懵懂回馈我,戏假情真道:我也是后来才去的,精彩部分我全错过了,我只看了个谢幕。
不死心的、妄图自主研发的我跟半染俩人在家头碰头猜了两天三夜,猜得青烟直冒涕泪横流想象力枯竭几乎升天,假设推翻再假设再推翻,到老也没猜出宗师到底对我爹妈说了啥。哥德巴赫猜想,我给你找了个中国媳妇!
几天之后,世界杯来了。为了履行之前对老赵的承诺,更为了从他口中套出拉稀外交的实情,我开始自动自发自请自愿地陪老赵看世界杯。在无处不在的捅马蜂窝背景声中,我一边不遗余力地想将双方的球门分清,一边居心叵测地试图将亲爹灌醉,以便重现“拉稀外交”的精彩画面。然而,酒,一滴不剩,球,一场不落,我,一无所获。除了严重睡眠不足导致的黑眼圈和乌组拉酿成的持续性耳鸣。
南非世界杯开幕没几天,我就扛不住了。跟亲爹商量着不再每场比赛都跟了,只跟那些时间上比较有人性的场次。然而,还没等到小组赛结束,老赵两口子北京历史游的第二站八达岭长城还没成行,老家里就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将我的亲爹妈紧急召唤了回去。
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老赵,当时只能称之为小赵,和赵赵氏,巧的是当时也只能称之为小赵,俩人通过别人介绍相识打算结婚。然而,我的奶奶却因为无中生有吹毛求疵胡搅蛮缠的原因(此处成语皆由赵赵氏提供),不同意这门亲事。但男女小赵心意已决私定终身破釜沉舟,还是忤逆着我奶奶领了结婚证。而忤逆的下场,就是不仅没有得到男方家的祝福,更没有得到一毛钱的彩礼。新婚的二赵只能暂时寄居在我外婆家。为了能尽快从娘家搬出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要强的赵赵氏通过自己不要命地干活以及娘家的微薄资助,终于买下了两间小瓦房。
说不上是幸运还是不幸的是,这小瓦房还没住满一年,亲爹老赵就得到了升迁,由老家的小县城提调到它的上一级行政区划里去了。在那里,他们不多久就生下了万能的我,于是从此安营扎寨安身立命安居乐业,再也没有回去。那两间小瓦房也就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巢,二十几年来无人问津。
再次说不上是幸运还是不幸的是,随着城市化加速捣腾它的脚步,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小瓦房所在的那片老县城区即将要拆迁重新规划了。这也就意味着,原本蛛网密结的小瓦房一夜之间因为它的面积和地脚而变得身价倍增。然而还没等“中华第一拜金妇女”赵赵氏为这飞来横财手舞足蹈,她就获悉了一个晴天霹雳:我的三叔,也就是我奶奶最疼爱的小儿子,正在抢这两间小瓦房的所有权。
这不仅触犯了赵赵氏忍耐的底线,连我的亲爹他的亲哥老赵都不答应,二位连合计都没合计,得到消息的当天就退了宾馆订了返程票。当我在办公室接到亲妈电话时,这二位已经在北京某站台的某节卧铺车厢里嗑瓜子了。
既然能嗑瓜子,说明我亲爹妈从北京离开的时候心情还是颇为愉悦的,对两间小瓦房背后牵扯的二十几万钱款的归属也是毫不担心的。赵赵氏在电话里说了,就回去两天,把房子的事儿弄妥,让小三驴儿,也就是我三叔,知道知道什么叫“莫伸手,伸手必挨尅”,然后他们这对神雕侠侣再卷土重来,二度南下,祸祸帝都。
一贯知学好问的你妈贵姓在获悉赵赵氏给我三叔起的这个饱含敌意与诅咒的外号涉及到了它理论上的远房先祖后,很是不满,当即对我甩脸子抱怨道:驴招你惹你了,你们人类凭什么不尊重我们兽类?!
我把男宠抱在怀里安抚道: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我本人绝对是非常欣赏你这位理论上的远房先祖的。它不仅有着一幅与生俱来空前绝后的受惊脸,还拥有一把特立独行震古烁今的花腔嗓,更不要说它那让我怕到欲罢不能的倒钩脚与和敢爱敢恨逮谁呲谁的小暴脾气了。在五花八门的贵禽兽圈,它是我极为喜爱的个性派选手。
你妈贵姓不好伺候地别扭身子问:那你为什么还把它作为外号?
那是你丈母娘给起的。我撇清关系道:当然了,我认为这其中其实包含着对我三叔无尽的祝福。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当然这个所有里不包括那饱受我妈祝福的三叔。两间小瓦房的归属出现了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我的亲妈赵赵氏使用小瓦房的时间过短,短到还没有拿到房产证她就搬走了。鉴于这个家一直由从不高瞻远瞩的赵赵氏治理,所以小瓦房惨遭从家庭值钱物品的名单上删除。现在这小瓦房眼看要灰飞烟灭变黄金了,可我家却拿不出它的房产证。当然有不少人可以证明这房子是赵赵氏婚后独自购买的,正如有不少人已经出面“证明”我三叔才是实际上拥有这所房子所有权的人。
事情起源于一根线头,却越滚越大,最终滚成了色彩斑斓的一团乱麻。从里面随便扯一根就是几十年的历史。这条红的是我亲妈对奶奶的陈年旧恨,那条绿的是奶奶对三叔旷日持久的偏心,那条蓝的是三叔对我亲妈不赡养奶奶的愤恨。
赵赵氏的倔脾气被彻底激发,声称要跟我三叔方面死磕到底。同时,为了让自己的死磕显得高尚优雅,亲妈还声称这次死磕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天理公道以及心气尊严。
然而,三叔方面显然是有备而来,很多我完全不认识的父方亲戚被牵扯其中,他们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团伙,誓死要将这二十几万拆钱款收入囊中。从赵赵氏口中获悉了这个团伙的人员数字后,我彻底惊了,我三叔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拉起了两百多号子人的队伍。幸亏这只是民事纠纷,要搞成刑事的,这规模可是要被通缉的呀。
打官司,已经是板上钉钉避无可避的了。老赵两口子迅速地忙活了起来,调动了一切可以被调动的人力物力财力,誓死要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在如此全民总动员的大规模群磕中,我,作为老赵家唯一的嫡亲闺女,没有理由也毫不可能置身事外。事实上,赵赵氏在决定打官司的当晚,就给我发来了密电:紧急联系家养律师彭大树。
我在接受到密令的第一时间就表示了严正抗议。首先且不说这个彭大树作为律师的职业水准是否靠谱,把老赵一家的横财和尊严系于他嘴上是否自寻死路,也不说律师彭大树是否乐意趟这淌浑水的个人意愿,单就地理位置上来说,lawyer彭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出所料,我有理有据的抗议立即就被赵赵氏以无上庄严的法庭用语“滚犊子”给当场驳回。
我只好给姥爷彭打电话。电话很快就被那边以官方的“喂,你好”接起,显然,彭大树已经删了我的电话,要不就是压根就没存。我怕早有嫌隙的姥爷彭挂我电话,只好民间影后上身,假装自己只是一个打电话找律师咨询的路人甲。
“你好,律师,我姓罗,我想咨询点事情。”我以爆豆的语速简明扼要地把小瓦房事件讲述了一遍,最后以天真无邪的语气质问道:“你是否可以帮我打赢这场官司呢?”
姥爷彭耐心安静地听完了我的讲述,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赵大咪?!”
“我姓罗,你可以叫我萝卜。”我还妄图再挣吧两下;却让彭大树更加肯定了他的猜测:“赵大咪,你妈刚刚才给我打过电话。我必须说,在叙事的条理性上你要强过你妈。不过在危言耸听程度上,你败给了她。”
“虽败犹荣。”被亲妈出卖身份的我只好先把个人荣辱抛诸脑后。我清了清嗓子,谄媚但尽量不巴结地说:“彭大树,我特别能理解你出淤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