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跳楼,都看见那厮在铺救生气垫-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又心疼,又有些莫名的欣慰,她的儿子,已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一个学会隐忍和照顾家人情绪的男子汉了。
她笑了下,脸上全是慈爱的温柔,抬起手搭在他头顶,像儿时安慰大哭的他一样,在他额头轻轻的拍了拍,接起他之前的话:“有点担心你,就来看看。”
这动作贯穿他童年始终,那时只觉得他妈用心险恶,给一大棒子再喂颗枣,后来大了离家上学工作,要面子要里子,就不许母亲再摸他的头了。如今陡然重现,只觉心里暖融融,似乎照过一抹冬日的阳光。
他忍不住就想撒个娇,扯下太后的手拽在手里,母亲的手背已然有了岁月的刻痕,粗糙的倒刺在指尖卷起,指头上皲裂的皮肤破碎成一道道细口,摸上去颇有些扎手。
许沐心里一酸,这才发现她鬓角丛生的白发,不由就有些恍惚,他忙生忙死各种瞎忙,却一直没注意到父母的近况。如这般情况他绝不是一个人,似乎历史赋予为人父母的使命就是,辛勤抚育并目送他们远去,而远行的子女,又在异乡成了另一个生命的父母,继承延续这种命运。而鲜少有人回头去看,分别的路口,父母已身形佝偻。
他猛然惊心,常常被人夸赞乖巧孝顺的自己,是如此受之有愧,不是逢年过节两件衣服或鞋,就叫孝道,更为重要的是挂念,是关怀。
许沐紧了紧太后的手,嘟囔道:“瞎炒心吧你,昨晚是不是又没睡好?”
太后不以为意,哼了一声,给他一个“你还管起老娘我”的眼神,让他自己体会。
许离秀女士从儿子身边探出头,看向冯程他妈,笑道:“老姐,我来看看孩子,可以进来吗?”
冯母已经调整好表情和心态,勉强笑了下,点头说请进。
太后大步向前,许沐跟班似的撵在后头,冯必玉看着和蔼可亲的许阿姨,忽然有种自己和冯程都是她妈捡回来的错觉。
她心里有很浓重的不平衡,同样是当妈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同样是当孩子的,待遇怎么就这么天差地别,她深深的嫉妒起许沐来。
她此刻心思全在埋怨上头,所以想法难免失了偏颇,记不起她的好,为难却无限放大,可到底是因爱生恨,她有多爱她,就能对她有多失望。
太后走到冯程病床前,仔细看了看自己儿子喜欢的男人,眉眼非常周正,线条冷硬,闭着眼都看得出性格一定很沉稳,看着靠谱,不浮夸,她稍微放下心来。
他额角裹着纱布,一想起许沐在电话里哽咽,他是因为和母亲对峙而被误伤,太后心里的偏见就刷刷的退散,只要许沐高兴,这人真心对他好,总比找个女人貌合神离的过一生要好。
她刚在楼下看见她家许东篱了,他在绿化区,扶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在雾气里散步,走的很慢很慢。那人不是谢文林,看着还有些匪气,不知说了什么逗的许东篱笑了下,接着头一偏,嘴巴就在东篱脸上啜了一口,却不见他生气。
她当时就惊呆了,东篱大小就不爱和人亲近,姑婆姨嫂见他长得俊秀,想摸摸拍拍他,他都不动声色的躲,却容忍这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亲他——这足以说明,这男人在他心里的分量。
她出神不过两秒,许东篱和那男人目光如电的射过来,见是她怔了一瞬,隔着鹅卵石的小径,遥遥的叫了声姑妈。
他笑容清浅如常,眼里却多了些温情,那个头高大轮廓锋利的男人嫁鸡随鸡的叫她,笑的怪热情的,还招呼她过去坐什么的。
那瞬间,对许沐即将要走的路,她好像没那么彷徨了。
太后心疼儿子,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母亲,她无法感同身受冯母错手伤了儿子那抹自责和悲痛,却只需假设的想想自己砸了许沐,心就要疼的揪起来。
太后问孩子什么时候能醒,伤的怎么样,冯母将昨天李医生的答复转述后,声音尾端就开始发颤。
太后绕过去,安慰的拍拍她手臂,说不会有事的,冯母眼圈红红的,目光复杂的看她们母子。
太后知道她除了担忧,还有心结压在心头,就从包里抽出五十块钱,对着许沐道:“沐啊,你带必玉下去吃早饭,吃完带双份早点回来。”
作者有话要说:
、第六十七章
许沐看着他妈欲言又止,被太后目光横扫两次,拉着冯必玉头也不回的出去了,反手将门带上。
太后顺势将钱往包里胡乱一塞,转而拉着冯母在床边坐下了,临坐前她伸手将冯程腿边的被子往后拢了拢,以免坐到,冯母注意到了这个小动作。
太后将手掌压在冯母小臂上,稍微使劲捏了捏,安慰道:“老姐啊,你别怕,孩子会醒的,啊。”
从现在坐的角度,能看到她斜侧脸,这才能看出许沐有三分像她,许是女人间才有的默契,冯母被她一哄,眼泪唰就落了下来,砸在外套里沁进去,顷刻就成一团深色。
她不过是个早年丧夫的单身母亲,怕孩子进别人家看人脸色,遇着对眼的老伴也没敢为自己打算过,她撑起了一个家,拉扯大两个孩子,可多年含辛茹苦,身旁没个依靠,不可能不委屈,不可能不累。
这种深埋的疲倦,在这一刻终于悉数爆发,程徽的死,儿子的疏离,女儿的责问,深更半夜的扪心自问,以及冯程倒下那瞬间,不可置信的眼神和满头淋漓的血,一切化为魑魅,层叠密实的朝她压下来,这一刻,她终于崩溃了。
她一面抬手一面低头,将脸埋入手掌,肩膀簌簌的抖,是那种竭力憋住哭泣却失败的节奏,些许啜泣从嗓子里泄出来,像是街头从榨甘蔗的机器口,吐出的毫无水分的、干巴巴的渣滓,好像随时都会卡机,窒息,揪的人心跟着紧缩难受。
太后被她吓一跳,儿子作为生日礼物送的名牌包滑落了也顾不上,连忙半环住她,在她背上不停的拍,急道:“哭出来就都好了,老姐啊,咱不憋着,敞开嗓子嚎啊,憋着难受又没用,来,听妹子一句劝啊。”
冯母发出母兽濒死那种低沉压抑的哀嚎,中途因为来的太急,而打了个急促的嗝,手掌盖不住汹涌的泪水,飞快的汇成泪滴从指缝里落下,速度比冯程的点滴液还快。
太后看的心酸不已,只能不停的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能确定,一切是会好起来,还是变的更糟,可那时那刻,却也实在无话可说。
冯母这一嚎啕,竟然持续了将有半小时,嗓子哭哑了,她就打嗝,连嗝都打不出来的时候,她就默默的流泪,时间和激烈程度,和她的压抑成正比。
许太后生怕她一个不慎就短气,不住给她顺胸口,两个母亲怀着同样的愁绪,谁也没看见,在冯母放生恸哭中的一刻,冯程的右手,曾飞快的握紧过一瞬,像是要抓住什么,可眨眼又松开,缓缓散开了。
许沐和冯必玉出去半个小时,就是一根根挑面条,也该回来了,太后还没来得及和冯母谈心,一时也将这茬忘了。或许许沐这时候回来,她还会嫌他碍事。
冯母激烈的哭过,消耗太厉害,又没吃早饭,立刻就有些低血糖,头晕目眩的几乎坐不住,太后就将她扶到空床上半躺下,自己拽了椅子,给她倒了杯水,在她床前坐下了。
冯母憋住大哭后想要打嗝的欲望,眼睛通红的打量许沐他妈,乱糟糟的心里,遍布着无法理解。
这是个和自己年纪相当的女人,说不上多美,眼角翘起鱼尾纹,打扮也不算光鲜,没有玉镯子和珍珠耳环,可给人的感觉很端庄。
她面对自己和冯程,态度正常和蔼,仿佛冯程是个女的那么自然,冯母甚至怀疑,她到底知不知道许沐和冯程的事儿,可她还没开口,太后倒是先摊开了。
她微笑着,目光如水的看过来:“老姐,我不太清楚情况,问个话,要是你觉得我是故意让你难堪,你知道我绝不是那意思,成吗?”
冯母虚弱的点点头:“你说。”
“我家许沐是独生子,一直挺安分,我和他爸也就没怎么管过他,想着让他自由成长,他在我们面前还算听话,可背着我们,那就不知道是怎么和人相处的了。可能任性点,可能无礼些,要是无意间让你看见不好的一面了,你尽管跟我说,我让他改。”
冯母一愣,有些茫然,却忙道:“没没没,小许是个好孩子,很有礼貌,每次去我们小区,叔叔阿姨从楼下一路喊到楼上,连物业的大爷也跟人打招呼,特别随和,还老是带礼物过来,我,我…我最开始特别喜欢他。”
太后敏锐的捕捉“最开始”,迟疑一瞬,决定单刀直入,她姿态很温和,眉宇间却全是正经神色:“老姐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家许沐,配不上你家冯程。”
冯母不可置信的看了她两秒,突然痛苦的捂住了脸,嘶声摇头,道:“不是,不是配不配的上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配法。”
太后笑了下,反问:“事实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这么配了,而且中国古代,不就有挺多男皇后么。”
冯母身子一顿,过了会才幽幽的说:“大妹子,其实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你能这么,这么……平常心的对待这件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觉得无所谓,而我却完全无法释怀。”
太后表情一僵,眼里划过悲伤,她向后靠在椅背上,缓缓吐了口气,说:“怎么可能会觉得无所谓呢,那是我怀胎十月,一勺米粉一勺牛奶养大的亲儿子呀——”
冯母错愕的抬起头:“那你还……”
太后坚定的看入她眼睛:“因为比起受人指点,我更害怕失去他。”
冯母打了个冷战,这种心理目前没人比她更了解,她嘴唇颤抖,喃喃道:“我也怕啊,怕的半夜老是想起来给他打电话,可……每次我脑子里浮现出‘随他们去吧,爱咋咋地’这种念头,另一道声音就会尖锐的跳出来反对,说,你这是在害他,他误入歧途你没阻止他,以后他受了伤,不恨死你,我……我放不开呀。”
太后说,“你放不开,是因为失去的还不够多。而我们家失去了一个许东篱,至于小沐,只要他高兴,我和他爸——会尊重他的决定,”自此语气略微哽咽,却保持的很平稳。
冯母摇了下头,目光灼灼的看向她:“那要是他以后过得不好,恨你怎么办?”
太后稍微睁大些眼,有些震惊:“这就是你怕的要死的东西?怕他以后恨你?”
冯母点了下头,“你不怕吗?”
太后不自觉摸了下包身上的标记,说:“我不怕,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那是我儿子,我不敢打赌是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可至少排得上前三。决定是他做的,我也不是没劝过他,就是他日后后悔了,那也是他活该瞎了眼,他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来怪我,而且以他的性格,他也不会怪我。”
冯母呆了眼,心想自己到底,竟然从没相信过自己的儿子,又听许妈说:“老姐啊,你不是不相信他,你是根本没将他当成年人看待,或许在你瞳孔里,他是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可在心里,他还是那个小小的孩子,你不操心,他就没法过了。放手吧,他都快奔三了,而且你为什么就不能往好处想想,他们会过的很好的,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冯母恍恍惚惚的听进去了,周围死寂一样,她扬起目光看了看一动不动的冯程,心里凉的厉害,那种刀割似的阵痛都麻木了似的,良久,她听见自己有气无力的嗯了一声,浑身力气刹那流逝的飞快,连同一起有别的什么东西,也随之散了。
她隐约察觉到,那或许是,自己顽固的坚持,害人害己,眼皮沉的不住往下搭,梦魇般怎么也睁不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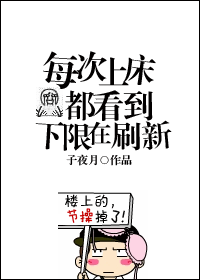

![[hp]每次逃难都会走错门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47/4768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