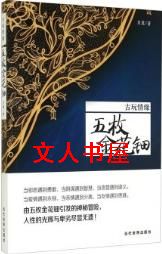花钿笄年-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就凭我庭于希三个字。”
“哈哈哈哈——”
“福建沿海,金门、厦门、湄洲、乌丘,我驻守四年,每一年,往返台湾十几趟。国军南撤,我在马公岛前沿,澎湖诸岛我都熟。台湾海峡,每一座灯塔,每一处暗礁,没人比我知道!”
庭于希的名声也不是向壁虚造,更要紧的是,军中无粮,火烧眉毛了。邓三麓心一活,嘴上也客气了:“庭兄弟想去,自然是好,可是你也知道,这抱冰公事么,没多少油水……”
“不是问题。只要船好,再有几个得力的人。”
“这个……”邓三麓眼珠儿一转,正募新兵,落选的不少,“好说好说,人和船,都是现成的。”
庭于希站在沙滩上,船是半新的轻型舰,还算结实,不显眼。应征入伍的小伙子们站了一排。他看一看一个眉眼机灵些的:“想不想跟我?”
“封锁线,玩儿命的!又没啥赚头……”他撇一撇嘴。
“你到务实。叫什么?”
“我啊,从小死了爹,衰!凑钱当个学徒吧,没出师,先克死了师傅,衰!想来入伍混口军粮,谁知长官们看不上,衰!总之什么都衰,我名字就叫阿衰!”
其余人都笑了。庭于希也笑着拍拍他:“年轻人眼光远一些,替公家跑,名声在外,以后还怕没钱赚么。”
阿衰是个聪明人,一点即透:“我娘给我算命,说我‘得意宜逢贵,前程去有缘’,说不定啊,碰见你这个大个子,能转转我的衰运。”
庭于希挑了几个精干的,洗甲板,撤番徽,重粉船壁。阿衰蹲在他身边:“嘿,有你的,指挥这么多人,倒像个将军。”
“抬举,不过混口饭吃。”
“大个子,你叫什么?”
“姓庭。”
“庭哥,大伙儿都累了,你这个当大哥的没个表示?”
庭于希见收拾得七七八八,一挥手:“歇一会儿,找个下处喝杯酒,我做东。”
一群人纷纷上岸,庭于希摸出几张钱,递给阿衰:“你们尽兴,我还有事。”
“这……喂,明天哪找你?”
“集结号响,码头见!”
苏浴梅在家等得焦心,看他回来,冷着脸伸袖替他擦擦汗:“走时怎么说的?”
“回家吃饭么,这不是回来了。”
“这么晚?”
“啊,饿着肚子呢。”
“你真是……怎么不在外面吃一点儿。”
“想吃你下的面。”
“都陀了,热了几次……”
他吸溜吸溜大口吃。
“饿成什么样……”
“高兴啊。”
“怎么了?”
“找到事了。”
如今马公岛一片混乱,渔耕不兴市面萧条,苏浴梅大出意料:“真的?”
“好差事。跑船,往南洋运货。”
“南洋……那么远,没什么危险吧?”
“往那边走,水路平。运的都是些杂货、水果,不担风险,薪水厚,卸了船还吃红。”
“这样好的事?”
“呃……一来么,老板看我身手好,二来,毕竟在这儿这么久,有些熟人。”
她似信非信的:“不是人家有个待嫁的女儿啊?”
他楞一下,大笑,又感慨:“只有你还把个跛子当成宝。”握一握她的手:“什么都好,就是赶得急,明天就上路。”
苏浴梅‘哦’一声,没多问,背身铺床:“那早点歇吧。”
他从身后揽住她的腰:“怎么了?我有事做,不高兴啊?”
“高兴,只是……” 她停一下手里的活儿,“两个多月没见你,才在家里住几天……”
“机会难得,赚了钱,咱们换大房子,雇佣人,就算不能跟以前一样……”他握起她的手来亲一亲,“起码不让你再做粗活。”
“只有我一个人,房子越大,心里越空。”
“不会的,早晚……还有孩子啊。”
第 45 章
古语说,兵者内以禁邪。沙场打滚的庭于希是有一些运气的,森罗密网的台海封锁下,他运回一船的军需。当然,一登岸,这些黄麦白米,马上换成了黄金白银。
邓三麓大喜,分给他应得的份例,百般劝说,希望可以长久合作。庭于希婉言而拒。
阿衰翻着厚厚的纸币,乐得只见眉毛不见眼:“好家伙,这么大的利!”
“用不了几次,就可以翻回来。”
“翻?你以前很风光啊?”
“呵,没有。谁不想望好呢。”
“那怎么不继续给他们干?”
“你知道,黑市里,大米多少钱一担?十元!几十倍的利。一经人手,盘剥大半。”
“哦,你想自己干!风险太大了,民船哪里是军舰能比?”
“风险越大,获利越丰。”
“就这么几个人?是军队是帮派,总要搭上谁。”
“放心,走这一趟,牌子亮了,不愁没人找咱们。趁着有本钱,带些私货。”
庭于希没料差,独闯封锁线的名声随他一起上岸,而且,不胫而走。到了下午,就有些帮派里的人物找到码头,明里暗里,用话试探。谈得拢,当即拍板。按船主的意思,当晚起锚,他想到家里,推了半日。
船泊在海边,庭于希和阿衰看着卸货。两人蹲在地上,捧着大碗喝汤面。
阿衰吃得满头大汗:“不如今天走,跑惯的人,闲不住。”
“我家里还有人,回去看一眼。”
“谁啊?”
“我老婆。”
“呵!看不出来。你这个岁数,也不是刚成家吧?又不是娇滴滴的新娘子,家里的黄脸婆有啥好看?”
他低头吃面:“你不懂。”
“我有什么不懂!”阿衰翻翻怪眼。不一会儿又恢复了快活:“今天晚上逍遥去!金门的姑娘真漂亮啊……”掂一掂手里的钱,涎着笑,“不知本地姑娘怎么样。”
“你……哎。”庭于希欲言又止,笑一笑,叹口气,继续扒拉碗。
“你要说什么啊?哎,你说啊!我最怕半截儿话!”
“没什么。”他笑着摇头,“找不到一个栓得住你的人,劝什么也是白劝。你‘逍遥’去,明早别误了船。”
两人在岔路分开。晚风清凉,催促着归人。庭于希加快了步,连那只跛足也似乎比平日顺畅。
矮篱门,他倚着栅栏,喊一声:“老婆——”
不一会就听到急促的脚步,苏浴梅看到他又黑又瘦却精神奕奕的脸,一腔的企望才落了实。
她挽着他往里走:“腿疼么?”
“阴天偶尔发酸,不碍事。”
“一会儿用热水敷一敷。”
他轻掐一把她的脸:“瘦了没有?”不等她答,一把将她横抱起,佯做吃力:“唔——掂一掂就知道。”
她忸怩着推他一把。
他哈哈大笑,一直将她抱进屋。满园枇杷也笑得金灿灿。
放她下来,他掏出一只口袋:“你看看。”
苏浴梅惊讶的翻着里面的钱。
“有空存起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她放在一边:“饿么?”
“饿。馋了多少天。”
路上不必说,一定是苦的。她轻轻摸一下他的脸:“我去买菜。”
“别去别去。”他握住她胳膊,“随便吃点什么,让我多看看你。”
摆上碗筷,她坐在他对面。他一壁吃,讲一路上的风土人情。
她只顾看他酣畅的吃相,心里有些疼:“明天我就去买鳜鱼、买青虾,还让你喝酒,好不好?”
“浴梅——”他撂了筷子,有些为难,“明天一早,就要出海。”
她愣在那,不说话,然后就默默收拾桌子。
他扳着她的下颚想转过她的脸,摸了满手的泪。
“浴梅?”
“那是个什么老板啊,才刚回来……”不是不体谅,情难自已,“谁没个妻儿老小,怎么这样不达理。”
“好了好了——”他搂着她轻轻拍,却说不出什么。战争不会无止境,台海也不会长久封下去,瞧准机会,毕其功于一役。心里的急,他没法说。
苏浴梅擦擦眼泪就止住,脱开他的怀抱:“我去给你打热水。”
等她端着盆回来,他已歪在床上睡着了。
她叹口气,卷起他裤腿,至膝盖,将热毛巾小心的敷上去。
第 46 章
时局动荡,粮价暴涨,政府征购,奸商囤积。几趟海路跑下来,庭于希已有了自己的三条船,私货占了八成,只顾着交情道义,才替别人捎一些。江湖朋友念着好处,沿路都肯照顾。他对下只有一句交待:“什么生意都能接,千万别碰四海帮。”
阿衰乍富,浑身装束换了一新,说话底气都足:“喂!真有面子,连军队的人物都认识。”
“什么?”
“你的电话,一个姓归的,好像是个官。”
“小归?”庭于希心里一喜,抢过话筒。
“好小子,怎么样?——唔,混得不错,要争气。——军统……哎,还真念着‘反攻复国’么——什么?”他眉头一挑,“真的?——好,你尽力,好,这样,保重。”
挂下电话,他有些失神。阿衰咬着葵花籽晃进来:“早知道你认识当官的,说几句话,我也不会入伍不成。”
“怎么?还想当兵?”
阿衰头摇成拨浪鼓:“说说罢了,跟着你一样大把赚钱,军队规矩多,我可受不了。”
“军队……”庭于希感叹,“进得容易脱身难……”
几个水手跑进来:“庭哥庭哥——”
“怎么了?”
“嫂子来看你。”
他忙出去。几个家伙犹在艳羡:“天仙似的……”
阿衰跟在庭于希身后,一路聒噪:“别说我失礼,这么久了,没先拜拜嫂子,今天这一见, 又是空着手……”
庭于希三步并两步的赶到外面,一手接过她提着的篮子:“你怎么来了?”
她见有人,就低声:“给你送点吃的。嗯……那位小兄弟,一起啊。”
阿衰的两只眼珠子差不多掉下来,话都说不利落:“啊,不不……不是,嫂子……客气了……”
庭于希笑着看他一眼,转向苏浴梅:“海风大,你进去擦把脸。”
她刚转进去,阿衰迫不及待:“想不到你这瘸子,这么犯桃花……啊,不不,不是……”他知道‘瘸子’犯忌,一脸歉疚,“我是说你命好。哎,哪里找到这么漂亮女人的?”
庭于希也不计较:“嗯……转过码头,向后两个鱼塘,在榕树林的岔路朝里拐……”
阿衰闭着眼苦思冥想:“岔路……那是清明寺啊,清明寺不都是和尚,还有姑子?那里的姑子漂亮啊?”
“哈哈哈哈——多烧香拜佛!这种福气,不是一辈子能修来的!”庭于希笑着在他后脑抽一记,进屋去了。
苏浴梅白过一眼。
“特意来送吃的啊?”他在她腰间一搂,“这里什么都有,不用担心。”
她看了眼聚在门口馋兮兮探头探脑的光棍们,只得伏在他耳畔:“想看看你……一走多少天,回来就不见影子。”
“就忙这一阵。”
“忙吧,我又不缠你。看你吃完就走。”她这样说,眼梢轻轻向他一带,低眉去盛汤。
他心里像有多少只小蝴蝶在扇翅,蝶粉粘得满是,痒痒的。几口将汤喝干,不知滋味:“我送你……陪你回去,再忙也不差这一半天。”
苏浴梅搭着他臂弯,走在海边略带湿气的泥地上,穿塍过肆,从宁寂到喧嚣,终归于宁寂。路人纷纷,纳罕,如花似玉的少妇傍着个风尘仆仆的跛子。'奇+书+网'有些市井轻薄之人竟挤眉弄眼,打起唿哨。苏浴梅只抱住他胳膊,脸也轻轻贴上去。
“明天就走么?”坐在家里,她问。
“嗯。“停一会儿他说,“大丈夫不能一日无权,小丈夫不能一日无钱。没钱没权,拿什么配你?”
她暗自叹息,那条腿,他不是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