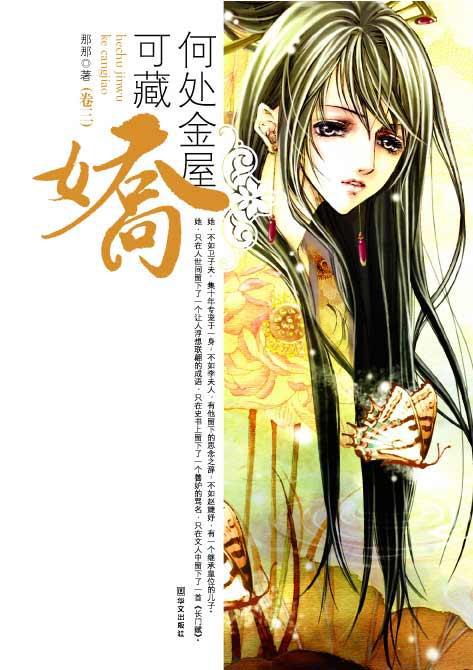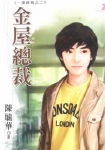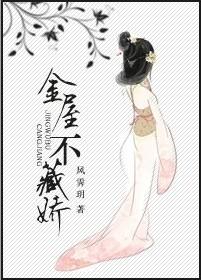金屋恨1-第8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莫隆额上便沁出汗来,反而镇静,禀道,“臣仔细检查了当日悦宁公主所骑之马,发现鞍侧下被人置了细针。悦宁公主身轻,初始时并没有触到,马便温驯。后来,拍到马鞍,牝马吃痛,这才惊奔。”
“你查了一日,只查出这些东西?”刘彻望着殿下跪着的人,笑的冷气森森,“你若是不想要这顶上人头,不妨明言,朕不介意成全。”
“臣不敢。”莫隆惊出一身,冷汗,忍不住看了看内殿的方向,重重珠幕阻隔了窥探的路。如今,躺在里面的那个女子,倒真是陛下心中地第一人呢。莫隆思忖。
“真相,是什么?”莫隆忆起那个年轻人的话语,语气幽微。
“当年姑姑的巫蛊一案,呈在台面上的样子,便是真相么?莫左监,你的顶头上司,张汤是这样教你的?”
“最重要的,是陛下地心意罢了。当年,陛下看重卫家,所以我陈家惜败。但如今,你自己睁大眼晴看清楚了。”
“风险,有时候也是机遇,端看人能不能抓住它。”
此次御架行上林苑,长信侯柳裔出征昆明,大司农桑弘羊仍在长安,飞月长公主刘陵是女眷。当陈娘娘昏迷,陈家在上林苑掌控局势的,竟是这位堂邑侯的庶子,初登朝堂的柬大夫陈熙。
莫隆将心一横,至少先在陛下面前有了交待,保住自己再言,他下了决断,禀道:
“御马监的人抵死不承认有放针。但那马鞍却是为了公主,特意从库房取出的软鞍。臣怀疑,动了手脚的不是马,而是这马鞍。”
“好,好,竟费偌大心机,只为谋害一个小小的公主。”怒到了极处,帝王的面色反而平静下来,“莫隆,”刘彻吩咐道,“你为朕仔细彻查,无论是什么人,都严惩不贷。”
“是,”莫隆低头应道。
“事发前,进出库房的有什么人?”
莫隆招来库房令,问道。
“启禀莫大人,”库房令战战兢兢道,“我库房上下,无人有加害公主之心,大人明察。”
“好了,”莫隆不耐烦道,“事发前一个时辰,库房可有异常情况?”
当日游舫上,悦宁公主说要骑马,不过是临时起意。如果是有人意图加害公主,只可能在短时间内作下手脚。
“并没有什么异常,”库房令想了想,道,“当时,太仆还遣人查过典马。后来,谏大夫遣人来为其夫人取枕席,因为谏大夫是陈娘娘子侄,所以我便放人进去了。”
“公孙太仆?”莫隆皱眉,周衰,官失而百职乱,秦兼天下,建帝号,立官职。汉因循不革,随时宜也。太仆,便是秦官,掌典马。而如今的太仆。便是卫皇后长姐之夫。公孙贺。
“来人,”莫隆吩咐道,“将当日奉太仆命检库房之人带来。”
然而,整个上林苑,再无此人踪影。
莫隆便冷笑,道,“请公孙太仆前来。”
“老夫的确遣人查过库房。”公孙贺淡淡道,“但凭此便可说,老夫有加害悦宁公主之心。莫左监,你是否太荒谬?”
“候爷军功赫赫。更是身世显赫,莫隆本不敢怀疑,”莫隆皮笑肉不笑的说了一句,“只是候爷派遣之人地下落,还请告知。”
“你……”公孙贺听出莫隆话里讽刺之意,勃然大怒,但终知不是发脾气地时候,冷笑道,“腿长在他身上。我怎么知道?”
莫隆皱眉,正要设法继续周旋,下属禀报道,“那日太仆所遣之人找到了。”不禁挑眉,问道,“在哪找到的?”
“有人暗中相助,引我们到上林苑,北琉璃阁后。发现此人正在被追杀,我们将其救回的。”
莫隆便目觑公孙贺,观其神色不变,不禁心中思量,到底是公孙贺掩饰的太好,还是真的与他无关?口中吩咐道,“带他上来。”
“当日,太仆大人遣你查点库房,可是?”莫隆问道。
“是。”堂下人浑身伤痕,望着公孙贺的眼神充满怨毒。
“那么,”莫隆声调转冷,“悦宁公主马鞍中的针可为你所置?”
“是。”
公孙贺情知此事不善,但听闻此语,依旧心中一凉,怒道,“长语,我自问待你不簿,你何如此构陷于我?”
“候爷,”长语转身,向公孙贺叩了一个首,“长语记得候爷恩德,所以不会构陷候爷。此事候爷地确不知情,吩咐我做的,是少爷。”
公孙贺脸色渐渐惨白,退后几步,竟似站不住似的,一瞬间苍老了数岁,叹道,“孽子。”
“候爷没事吧,”莫隆微笑吩咐道,“还不扶住候爷,”转脸冷笑道, “传公孙敬声。”
须臾,兵士押着公孙敬声上来。
“大胆,”莫隆斥道,“我虽吩咐你们将他带来,但他毕竟是卫皇后地外甥,怎么如此不礼遇?”
“启禀大人,”兵士禀道,“卑职并无意如此,只是这公孙敬声,神色仓皇,不肯前来,卑职不得已,方如此。”
莫隆便一笑,人言卫家第二代,除了冠军候霍去病,居皆庸才。尤其是公孙敬声,更是堪称纨垮子弟,果然如此,尚未受审却做如此态,岂非摆明了他涉案其中。
“你凭什么审我?”公孙敬声叫嚣道,“你知不知道,我是南峁侯公孙贺之子,卫皇后的外甥,”他欲摆出威势来,却连身边小吏都听出些色厉内荏地味道来,“姓莫的,你敢如此对我,不怕我皇后姨妈日后治你的罪么?”
“公孙少爷,”莫隆冷笑道,“皇后再大,大的过陛下么?别的不说,单是一个谋害皇嗣的罪名,便是十个公孙敬声,也是杠不起的。”
公孙敬声的脸一白,身为卫氏中人,他自然知道,元狩年后,卫皇后在未央宫,就只是一抹苍白的影子。
或者,在那个盛大地帝王身边,每一个人都只是一抹影子。只除了,除了那个据说如今尚卧榻不醒的女子,或者,还有那个意气飞扬的少年将军,自幼将他的光芒压尽,让舅舅和姨妈永远只看的到他的表弟,霍去病。连……
霍去病已经死了,他的心底忽然扬起了一抹快意,却立刻被理智压下去。母亲说,霍去病亡故,陛下对卫家地眷顾,便又少了一分。当年那么盛大的卫家,渐渐的,如履薄冰。
可是,如果,他隐秘的想,如果那个女子亦死了呢。是不是,所有对卫家的威胁,都会消失?
“廷尉府就是这样冤人的?”公孙敬声扬身冷笑道,“无论如何,我的姨妈是皇后,名正言顺的一国之母,容不得你们不尊敬。”
“廷尉府是不是冤人的,你很快就知道。”莫隆微笑道,“长语已经指证历历。你尚不肯招认。”他忽然声音一厉,“你要我用刑么?”
公孙敬声面色惨白,看着后堂转出的长语,声音惊俱,道,“你,你。”竟是再也接不下去了。
“少爷不曾料到,长语尚未死吧。”长话冷笑道,“长语本不愿供出少爷。无奈少爷见事大情急,竟欲杀我灭口。就别怪长语不义了。”
“爹。爹,”公孙敬声脸色发白,惊惧异常,“你救救孩儿。”
公孙贺闭了眼,明知希望渺茫,还是问道,“敬声,不是你做的,对吗?”
“我并没有料到会闹到如今地地步。”公孙敬声勉强道,“我只是看不过悦宁公主恃宠而娇,想给她个教训。我并不知道陈娘娘会亲自去救,更不知道陈娘娘有身孕地。甚至那针,也是磨平了尖的啊。”
“孽子,”公孙贺气得浑身发颤,“你知不知道。我公孙家百年基业,居将毁于你手。”
堂上,莫隆暂时舒了口气,案情审到这个地步,已经可以向陛下交差了。只是,他今日态度强硬,早已将卫家得罪殆尽。
唯今之计,他眸色一沉,唯有联合陈家,将卫氏彻底扳倒。
否则,日后,卫家算起总帐来,如何能饶的过他。况且,目前局势偏向陈家,陛下,更是对信合殿里的陈娘娘爱惜不已。
他自认并没有上司张汤对时势有着清晰的洞悉,但张汤日常对陈氏一族极是尊敬,他亦不得不考虑。
信合殿里,陛下吩咐道,“你为朕仔细彻查,无论是什么人,都严惩不贷。”
陛下心里,早有定见吧。
他思虑已定,吩咐道,“来人,将公孙敬声收押。”
“敬声,”公孙贺扬声唤道,却被莫隆微笑拦住,“候爷,公孙敬声乃是陛下吩咐的要犯,候爷还是不要再费心了吧。”
公孙贺瞪了他良久,终究悲凉一叹,蹒跚而去。
“谋害皇嗣,罪在不赦。”公孙敬声想着莫隆的话。
这一刻,他是极悔地。悔自己为何脑子一热,就错下大错。
事情,是怎样发展到这个地步的?
“公孙敬声,是谁指使你谋害皇嗣的。”
他身子一瑟,勉强醒神,道,“没有人,是我自己一时糊涂。”
那个声音在嗤笑,“你当别人都是傻子。你说看不惯悦宁公主恃宠而骄,你公孙敬声是外臣,又不是冠军候和悦宁公主交好,少见公主,如何能看不惯?”
他一滞。
“是你地父亲,太仆公孙贺,还是长平候卫青,或者是,”那个声音带着些微诱哄,“皇后卫子夫?”
“没有,没有。”他抱着自己的头,大声道。
“你谋害皇嗣,罪在不赦。唯有供出主谋,才有可能从轻发落吧。”那个声音叹道,“陛下虽然一向无情,对子女倒是疼惜地。陈娘娘此次怀的,很有可能是个皇子。陛下膝下只有四子,好端端一个皇子丧去,如何肯干休?”
他不想死的。
“公孙敬声,”那个声音又问,“是谁主使你的?”
“是——”他迟疑答道,“是皇二子,刘据。”
他昏昏睡去。一个人从牢后转出,问道,“大人,可以了么?”
莫隆抿嘴一笑,道,“本官这就将审讯结果通报陛下。”
他将公孙敬声的口供辑录成册,穿过广阔的上林苑,低首来到信合殿前。
“小心点呢,莫大人,”青衣内侍轻声道,“陈娘娘到现在还没有醒,陛下脾气甚为暴躁。”
莫隆微笑着递出一串五铢钱,道,“多谢公公提醒。”
“哎呀,不敢当。”内侍微笑道,却收了钱,径自去了。
信合殿外,阳光穿通云层,直射下来,闪起万点金光。照在人身上,有些暖暖的。莫隆却微微皱起眉,一丝忧虑在心底掠过。
不过是小产而已,陈娘娘,如何到如今尚未苏醒?
然而,殿内已经传来宣他入内的声音。
莫隆恭敬入内,禀道,“臣日夜审讯,终于录得逆犯公孙敬声口供,特呈御览。”
御曾总管杨得意轻轻走下殿,接过他手上的供册,转交给陛下。
信合殿内一片安静,唯有陛下翻动供册地声音。须臾,刘彻将供册掷在案上,冷笑道,“朕的好儿子啊,不思上进,却想着算计自己的姐姐。”
“杨得意,”他扬声吩咐道。
“奴婢在,”杨得意躬身应道。
“传令张汤,擒拿刘据,仔细审查。”
“陛下?”
“还不立刻去?”
杨得意惊然,只得应道,“是。”
殿下,莫隆依旧没有抬首,却隐秘的勾起唇角。
然而,连莫隆都不知道的是,在他来到信合殿前,数骑快马出了上林苑,加鞭向长安方向驰去。
站在上林苑角落的阁楼上,陈熙冷眼看着南峁候公孙贺的心腹下属策马奔驰,向长安方向而去。
“熙少爷,”身边侍从不解问道,“为什么不出面拦住他们呢?”
“我就是要让卫家知道。”陈熙好整以暇道,淡淡低首,看着脚上圆履,眸底闪过一丝灰色,“没有人可以伤害我的姑姑,卫家人既然敢做,就要付出代价。”
“谋害皇嗣实在不是小罪名。”见侍从一脸茫然之色,他微微一笑,道,“纵然她卫子夫是皇后,也杠不下来。卫家得到消息,必然有动作。而这动作,”他轻轻握拳,“就是我要看见的,也是卫家永世不得翻身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