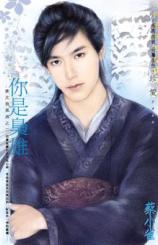我是贼婆你是王-第6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沈掬泉身形一定,沉默良久,最终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
我望着一室满溢的烛光,心有说不清楚的沉重。
镯子的来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翠荷坐在旁边等了我许久,见我睁眼,笑呵呵道“小夫人这一觉睡的真安稳一直到天亮。”
我点点头,左右看了看,貌似季宁烟并没有来过,心里生出些失落。
“对了,夜里侯爷带人捎信儿过来,说昨晚在宫里有事情所以昨儿夜里回不来了。”
我点点头,宫外有苏兰,宫里有梅妃,我想不多想都不行。
洗漱过后,我吃了点粥,一个人坐在窗前开始理那些没有尽头纠结的关系。
目前的一些列事情就像是被猫抓烂的线团,扑朔迷离,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似乎不怎么沾边儿,让人想的头脑发疼。
暨阳侯府的血案还有永暨侯府的刺客,这似乎跟金陵,跟科重半点关系都没有,可我想了又想,直觉告诉我这些事情之间一定有着什么隐秘的关联。
张之远和沈掬泉都说过阳尸和血虫都是科重当年的杰作,遗失了的半本“易玄经”有那些歪门邪道的制作方法,如果只是仅仅是血虫的话,还可以理解成墓室里的玄术,那是护墓所设,逻辑上可以解释的清楚。
可阳尸这一关就完全说不清道不明了,上次看到被解剖的阳尸心脏里面的那个符咒纸,那师徒两个也说了只是普通的“牵灵符”,可普通的符的玄术会那么凑巧的配合了时间和地点?
为何之前张之远说对于阳尸知之甚少也就只有在他的师祖的言传里才隐约可知一二,百年过去却无人见过这东西?突然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真的只是“库存”那么简单?那为何白马寺的地宫里守阵势的却只是尸体?并没有半个阳尸的影子?
还是说科重还有其他的墓穴存在?衣冠冢?没必要啊。
再进一步说这些“库存”的阳尸又是被谁解放出来的?什么目的?为何知道科重的衣冠冢?连带着那半本“易玄经”是不是也跟着落入他手?还是半本“易玄经”依旧在金陵地宫?或者流落坊间?
跟着刘二洞这么多年都知道这么个理儿,墓主所在的地宫里一定会把毕生的珍奇异宝堆放在那里,视死如视生。
从未见过科重这样的人,布阵,却不要护阵的。这岂不是天大的奇怪了?
薲的出现,她腹中的血虫原虫,那些血灵,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似乎在引导我们往一个思路上走,那就是,科重是玄术师,薲自然也是,两人年龄相仿,又各有一只一模一样的镯子,羊脂玉碑上的两个字,镯子的神奇功用,以及两人互为牵制的生忌与死咒,还有无用却并不能被忽略的轩辕修,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或者真是被我之前胡言乱语言中了,那不过是一出爱极生恨的戏码?可那些情爱真的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为何不去床上躺着?”我一顿,扭头,季宁烟一脸疲乏站在门口。
“我是胳膊伤了不是腿伤了,走几步不碍事儿。”我幽幽道,转过头,放眼望着窗外。
季宁烟笑呵呵的走过来,一只手搭在我的右肩膀上,极轻。“有心事?都写在你脸上呢,说说看。”
我用手拄着下巴,恹恹道“心事太多,不知从何讲起,于是嫌麻烦索性不讲了。”
“那我有心事,可以跟你说说吗?”他轻问,眼睛却不看我,跟我一样望着窗外。
“哦,如果您怕事多把你憋死了你就赶紧说吧。”
“皇上昨晚找我去是让我去调查暨阳侯府的血案一事。”
我一顿,抬头“如此?那么那个刺客?”转念“不对,暨阳侯不会蠢到如此地步吧,这不是傻到家了?还是?”
季宁烟眼色深深浅浅,低头看我“苦于找不到证据证明不是暨阳侯干的。”
“不是你就是暨阳侯,不是暨阳侯就是平阳侯,你们兄弟四个,还剩个才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子,总不会是他吧。”
“我怀疑是平阳侯”季宁烟定了定道。
我侧眼“为何跟我说这个?不怕我给你宣扬出去?”
季宁烟不笑,表情颇为严肃“除了你我再也行不着任何一个人了。”
我怔了怔,没有接话,其实我同季宁烟和沈掬泉之间的关系都不算单纯,一个因为让我盗墓招我进侯府的,一个因为“易玄经”的下落接近我和我做朋友的,如果非要说季宁烟到底哪里优于沈掬泉的话,除了时间就是他比沈掬泉更坦白一些。一开始就宣布了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就算是卑鄙,也是正大光明的卑鄙。
可就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事情发生到今天会有这么个让人跌破眼镜的发展趋势,虽然感情深刻了,可当初那些目的性却是如同伤口的结痂一样历历在目,我不计较,却让我感觉格外的别扭。
我看了看季宁烟“人有了弱点就多了份危险,我不愿被当成弱点,我只想活的轻松一点。”
“小十,等这件事情忙完,那个金陵地宫就再下去一次,这一次一定要把那煞和血虫解决了,拖了这么些时日在心上总是心病,时时想起来都会不舒服。”
我笑笑,不以为意“金陵不好下,骖沅更不好拿。”
季宁烟突然侧眼用双手扳过我身体,强迫我与他直视,这一扭,让我肩膀的伤口疼痛不已“小十,是不是在你心中,不管我为你做什么,你都会觉得我有自己的目的?是不是无论什么事情都充满了阴谋和算计?你对我到底有没有真情?而我对你的神情你可曾相信过?”
我直视他眼睛许久,直到眼眶酸胀,喉咙哽咽“事情都摆在眼前,你让我相信什么?蒙住眼睛以为爱比天大吗?以为用心去真爱一辈子那是最无私的爱情吗?以为人生只有弹指一挥间吗?以为深情就是接受无法厮守的唯一理由吗?”
我笑得凄凉“季宁烟,让我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一次,不会。那些统统都是不成立的,没有什么比天大,人生要一天一天的过下去,只有用心去真爱身体却是背叛那不是真的爱,而无法厮守那便不是深情,不管你我的苦衷有多少,都丝毫不能改变这一切,正因为我那么清楚所以我从不让你为我牺牲什么,因为我更懂得一个道理,求来的付出只不过是勉强的敷衍,熬不过每一个天黑天亮,我是没读过书,可有些道理我却比谁都要深刻。”
“如此,就只能二选一了是吗?”他手劲儿放松,缓慢的抬起自己的身子。一行泪落下,划过脸庞,痕迹如此清晰。
“错,季宁烟,无需二选一那么费力气,凭着你直觉去走吧,选择如果太过艰难,你就让你的心按照自己的直觉去走吧,我虽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可我不要施舍,你的牺牲我未必就稀罕。”
我们彼此都沉默,早上的阳光从窗射进房间,装了满满一屋子的光亮,我们沐浴其中,可我却觉得我的心一片阴暗。
舍得是人最大的领悟吗?可我却觉得舍得并非是自主选择,绝大部分时候那是迫不得已罢了。
过了许久,季宁烟幽幽道“这事儿一过,先去办你的事情,骖沅的事情就再说,就算我得不到,我也不会让其他人得到,大不了就谁都别想得不到。”
他缓缓踱步去门口,推门的时候定了下来,头也没回,只听他声音沉沉“等你好些了我们先去玉楼找那个老板,这镯子跟那半本‘易玄经’定是脱不了干系,我们就从他下手查。
还有就是,小十,如果你心里有自己的看法,那我希望你能否往前迈一步看看?有时候我觉得就算你已经磨掉那一身的棱角改头换面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者心不在我这里,那我也要留你在我身边,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离开。
可我又不想要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我要你的感情,要你的心,你的全部。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多少次,你都不知道我回想起墓室里面你抱着我时候我跟你的那些话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也许那种心情也只有我才懂,可我无法把自己一层层剥开给你看,我怕…我怕,那对于你来说,只是一文不值。”
门被推开,阳光满满的堆了进来,季宁烟那一身紫袍被照得光艳刺眼,我不像别过眼,生生的看着那些耀眼,刺得眼球做疼,泪又留下来。
我有贼婆的狡诈和自私,唯恐先爱上对方便痛失城池,万劫不复。季宁烟也有着侯爷的精明和高高在上的尊严,只敢爱,却不敢言,想真爱,却只能衡量得失,这不是碰巧,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三天后,肩膀的伤口已经开始结痂,沈掬泉再未出现过一次,而我与季宁烟之间的关系格外别扭,话并不多。他偶尔来,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尴尬的沉默着。
等到并无太大妨碍的时候,我跟着季宁烟再次去了玉楼,老板见我们来,还是笑容可掬的迎上来“呦,贵人到啊,快里面请,我们里面聊”
等我们都坐下了,老板谄媚的点头哈腰,又是奉茶又是上点心,季宁烟端起茶碗并不喝,闻了闻,又缓缓放下,淡淡道“这次来只是想跟老板问句真话,前段日子我们乃的那只雪尊可否真的是老板的传家之宝?此话当真?”
那老板一定,大概以为我们是来退货的,一溜烟儿说了四五个“当然”
季宁烟又接着问“如果是真,那我只在问老板一句话既可,请老板无比告知实情,如若不然,将来出了漏子,这事情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老板一听这话说的不轻,一双小三角眼左右晃悠了一圈“贵人请问,小的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请您放心。”
季宁烟撩眼看他“这雪尊究竟是如何落入你祖上之手的?”
老板身子一定,转念笑嘻嘻的道“这都多少辈儿过去了,我们做重重孙的小的咋能知道的那么清楚,只是从小的的爹那里接过来的,遇上您这懂行的贵人,况且令夫人也喜欢,小的就做了成人之美的赔本生意了不是。”
我用手轻敲桌面,那老板掉过眼扭头看我。
我开口“你甭蒙我们,能来你这问,说明我们早就查过你祖上十八代了,算是世代小富一个,一不穷困潦倒,二不着急用钱,你却突然卖祖传的东西这说得过去吗?
当初是以为你胡说八道,可现在是觉得你形迹可疑,事情闹这么大,你想撇的一干二净?门也没有。”我手一重,那桌面被我拍的一响,站在地中央的老板给吓得一耸肩,轮圆了眼睛
“小的句句是实,如有半句虚假,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我听得不耐烦,朝他挥手“得,得,这誓我也发过,你少给我扯那些没用的。”调过眼看了看季宁烟“知道他是谁不?”
老板蹙眉,不知所以。
“平阳侯府的侯爷”
老板闻言“咕咚”一声跪倒在地“草民有眼不识泰山,有失远迎,侯爷息怒。”
季宁烟朝我看过来,无奈的摇了摇头“刘大福,本侯对你之前那些来路不明的珠宝就不予追究了,不过这雪尊的事情本侯一定是一查到底,这涉及到暨阳侯府血案之事,你可知事情大小?”
暨阳侯府的血案可是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惊天大事,店老板自然也听闻过,再闻季宁烟这么一说,生怕自己跟着粘连了什么关系,磕头虫似得“草民愿用六斤四两的向上人头向侯爷保证,这雪尊绝对是珍品,的的确确是祖传下来的好东西。”
“哦”季宁烟淡语问“那为何本侯调查到的皇家饰品会成为你家的祖传?你家历代可有宫中做事的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