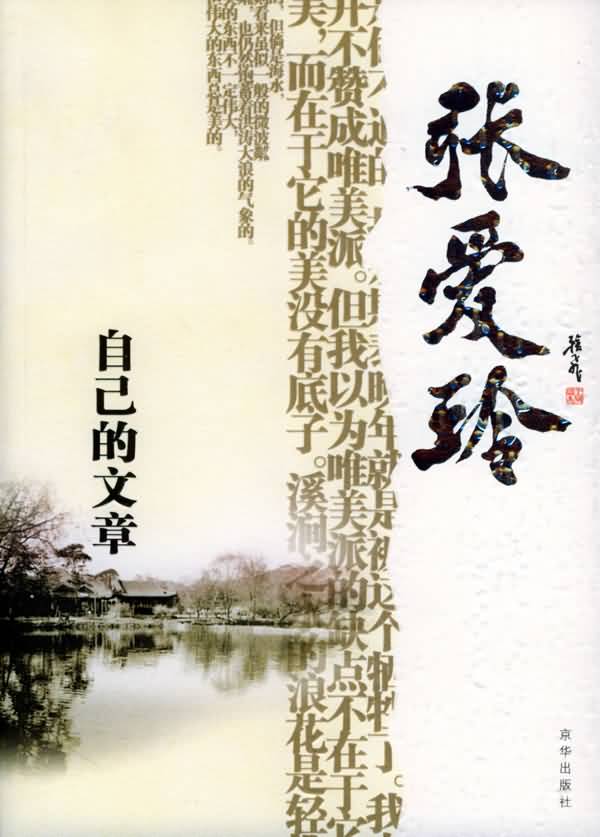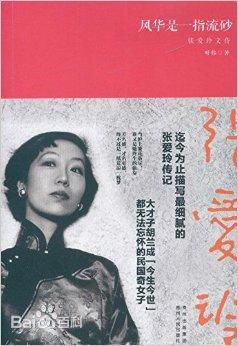张爱玲经典散文集-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搪前挂下了中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女佣告诉我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吧?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项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宇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我选择的,而且我画小人也喜欢绘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婉婶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兴,眼泪也干了,很不好意思。
《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策。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接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妨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同搬走了,父亲移家到一所弄堂房于里。(我父亲对“衣食住”向来都不考究,单只注意到“行”,惟有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调张,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摸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被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磕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楼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家里虽然看到我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来,也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了。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借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人睡,所以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 她打我!
“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蹬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他走了之后,何干向我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这时候才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哭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她开口我父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捕房,因为太丢我们家的面子“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自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①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①Beverley Nichols,通译贝弗利。尼科尔期(1899),英国作家。著有小说《序曲》、《自我》、《无情的时刻》,自传《二十五周岁》、《父亲的形象》等。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
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何干怕我逃走,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我还是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龟》①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我这里没有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是更深人静的时候,惊动两只鹅,叫将起来,如何是好?
① 《九尾鱼》是近代作家张春帆(漱六山房)所著的狎邪小说。
花园里养着吸狐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邀遏丧气的花。
正在筹划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闻,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
一等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