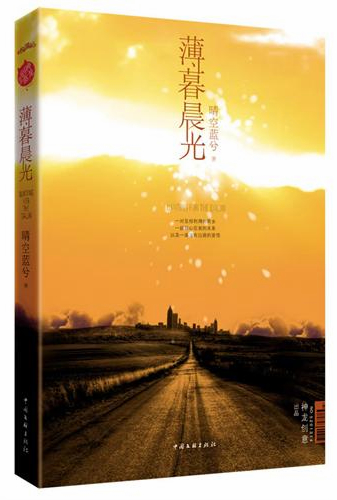晨光搁浅-那焉-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八点多,我实在被自己的念头折腾的烦了,便裹上大衣,又朝医院走去,其实我刚刚一直都在想,找什么理由好,什么借口好,可一直没个头绪,想不出,索性直接去了。
走到医院外的花店,灵光一闪,便急匆匆跑进,买了篮水果与一大捧花,又仔细叫花店老板写卡片。
“写什么?”老板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甚是亲和。
“唔……就写,蓝田设计公司苏经理。”我嘿嘿一笑,回答道。
推开病房门时,我觉得名正言顺多了,就算范阿姨在,也没关系,不过里面就宗晨一人,正安静躺着在看书。
白炽灯很亮,衬的他的皮肤更白,毫无血色的模样,我看的有些揪心。
听到声音,他抬起头来,微微眯着眼,神态慵懒,带着几丝病态,纱布大概换过了,脑袋看起来像个粽子。
我冲他笑,一点也不心虚:“小和尚,我代表苏经理特来慰问……”
“哦?”他的笑意褪去,微微蹙眉,“那……谢谢她了。”
我搬了个凳子坐到病床前,稍稍离了些距离,又左右看了会,压低声音问:“范阿姨呢?”
“她身体不好,我让她先去休息了,这边有护士照顾,没什么事的。”他望着我,顿了顿问道,“你怎么做贼似的?”
“哪有……”我将花摆好,又将水果篮拎起,放到他跟前,“喏,想吃哪个,我给你剥好。”
◆第29章
那之后的几天,我都会偷偷摸摸过去看望宗晨。
他说要吃鸭血粉丝,我第二日一大早便乘车去南京给他买来,又拜托酒店弄热,结果他只吃下几小口便不要了,最后还是被我自己给解决了。
每次离开前,他总会说出一样名堂来,让我明天带去,而每次去时,范阿姨也总没在。
他恢复的速度有些慢,只不过总是在好的,前额的发长出来,硬硬的,冒出头来,用手去摸,像是老爸的胡须。
每天都来,护士也认识我了,我想,范阿姨其实也知道的。
宗晨神色温和,话也渐渐多了起来,不过大多时候总是我在讲话,他安静沉默的在听,有时笑着,有时只是在听。
我只挑那些轻松的话题,不带任何矛盾的,可以一笑了之的。
“那一次,你知道不,我好震撼……你竟然滑的那样好,后来你说你还曾参加过比赛,我还不相信……其实我现在也不信,真的?”
宗晨歪过头,看了我一眼,“真的。不过是小学时候……”
……
“你一开始是不是觉得我很烦?”
“……恩。”
“那后来干吗不走?”
“……我,习惯了。”
“……”
诸如此类的,像是两个朋友,互相说着以前的糗事,谁都没有提及任何边缘的禁忌,我忽然觉得这样也很好,像是朋友一样的,交往。
“呐,你还记不记得?我有次生日……一直等你,你却没来……”我半个身子靠着病床,将脑袋搁在栏杆上,笑嘻嘻的问他。
“恩,你爬进我家那回。”
“你还记得啊……还好你家在二楼,不过那样也很吃力啦,管楼的阿姨看见了,我就说是你忘记带钥匙了,让我帮忙去拿。”
“她还对我说,一个男孩还要女生爬窗户拿钥匙,真丢脸……”
我哈哈的笑起来,宗晨也笑了,浅浅的笑意,挂在唇角,真好看。
“我回来,看见你裹着被子在睡觉,是真的吓一跳。”
我又笑,“谁叫你放我鸽子。”
“那感觉挺好的,”他说,眼底带着温和的笑意,“看见你在的感觉,挺好的。”
气氛忽然异样起来,我低垂着眼,不再说话。
“浅浅……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明天,买本书念给我听,行吗?”
“恩。”
第二天,宗晨想要出去走走,不过被护士拦下了,说是外面太冷,伤口未愈合,容易感染,他很无奈的只在病房转了几个圈。
我乐颠颠的,幸灾乐祸:“这下知道禁足的滋味了吧,想当初不知是谁硬将我关在家里,不完成作业就不准出去,哼哼……”
“……”他苦笑,“记恨记这么牢。”
有个成语,易如反掌。我觉得有些东西的改变很是玄妙,有时候,你头破血流的争来争去还是一场空,可有时候,就像是翻个手掌那样容易。
我和宗晨,这样心平气和的相处,似乎还是头一次,以至于我总觉得像是走在云端里。
但我明白,因为美好,所以短暂,我和他,都在珍惜。
这一晚,我在宗晨的病房呆了很久,值班护士几次三番过来视察,见此也没再说什么了,只是嘱咐他要早点休息,明日最后一次复查。
微光浮游,尘埃在白炽灯下清晰再现,如某个电影场景,空气里弥漫着属于医院特有的味道,宗晨闭着眼靠在床头,慵懒倦怠。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低低的,轻轻的声音漾在稍显空旷的病房,窗外的夜色逼近,似乎只剩下这小半块地方未被吞没,我翻完最后几页薄黄的纸张,轻呼口气,纸张窸窣的声音,带着剧终的苍凉与惆怅。
“宗晨……”我轻声叫他。
他似乎是睡着了,只有安静而沉稳的呼吸声,脸色看起来好了许多,紧闭的唇抿成条线,
头上包着白色纱布,这个样子的他,像是电视剧里受伤的士兵。
我开了床头的灯,调暗,暖黄的色,像是喝完果汁后白瓷杯里留下的那一层,温馨古朴,又将书合上放好,静静坐在那看他。
那本折磨着我的未知,急欲想了解的原委,不知何时已化成轻飘飘的空气,消失了,我不再想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怎么样……那些过去变得不再重要,就像是已经赶不上的车,开走了便是开走了,结果已如此,那原因也不重要了。
我小心翼翼的撩开他的病服,那道伤疤的安静的覆着前胸,像是栖息在树身的昆虫,经过若干年代后,成为琥珀一样的存在,融为一体。
我用指尖触碰,像是摸着粗糙的树皮,纹路起伏,不知埋藏了怎样的往事,承受过多大的惨烈。
他的身体忽然一动,眉头微微蹙起,原是有泪掉上那疤痕,顺着肌理滑下,像是要拭擦掉那痕迹,我忙用纸巾擦掉,又将衣服翻下,盖回被子。
我将床头灯也关了,于是这最后一处有着亮光的地方,也被夜色吞没。
有透过窗的微弱光线,曲折着进来,失去原先的方向留在地板上,影影绰绰的,我想起刚刚念完的那个消逝了的苍凉传奇,忽然觉得这月色也无端的生出些怅然来。
“宗晨……晚安。”我弯身,与他轻柔的道别,他受伤的前额与我的唇只差毫厘,蜻蜓点水般的一触后,却退缩起来,身体僵硬着无法继续,像是播放到□的歌曲陡然按下暂停,不,大概是停止键。
我的勇气,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黑暗中,却不知哪里伸出的触角,脖子被一双手臂环住,带着潮湿而柔软的气息,我顿时跌入一个梦境,不知是我的还是他的梦。
“别走……”他的声音涩然而急促,像是隐忍许久的情绪终得到释放,“浅浅,别走……”
或者,劫后余生的人都脆弱如斯,恐惧寂寞黑暗孤独,再也无法独自承受。
“好。”我声线暗哑,像是变了质的浓酒,微颤,“我不走。”
那一层清浅的月光,拢着如水的金色,彻底滑进了房间。
他的眉微微蹙起,双眼紧闭,像是遭遇了什么噩梦,手臂先是挂着我的脖子,大概是确认不会离开了,又松松的垂下,搭在被子边缘。
我又轻轻的叫了他一声,“宗晨?”
他只从鼻子哼出一个模糊音节来,便翻了个身,继续沉睡。
我忽然不知该做什么好了,像是有一块硬梆梆的布,堵着我的心。
他只从鼻子哼出一个模糊音节来,便翻了个身,继续沉睡。
我忽然不知该做什么好了,像是有一块硬梆梆的布,堵着我的心。
我就这样趴在他的床前睡着了,空调呼呼吹着,我很快入梦。
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和衣,躺在本该躺着宗晨的宽大病床上,霸占病人待遇的感觉着实有些不好,于是我立马蹦跶着跳起来。
这时天刚亮,有淡淡的光透过窗户,我轻手轻脚的走过去,忽然很想袭击还沉睡着的某人,想看他被吵架时略微恼怒的模样。
另一张专供家属休息的床上,宗晨蜷着身子躺着,大概因为床小,身体弓的像是一只虾,裹着纱布的脑袋埋在枕头边,侧脸英俊而苍白,带着清浅的呼吸声。
有碎金子一样的晨光,落在他的侧脸上,像是触电一样,我蓦地停住正要朝他脸上蹂躏的手。
他的眉眼间带着休憩时特有的慵懒,微翘的唇还挂着一抹不易察觉的笑,睫毛敛住下眼皮,真的……很好看。
若是时间就此停住会怎样,就这样一直下去会怎样,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也没有人可以穿越光速,所以时间继续流逝。
我出门的时候,碰见了门口的范阿姨,我不知道她是刚刚经过,还是特意在外等着,估计后者可能性较大。
我像是要被审讯的犯人面对警察,忽然惴惴不安起来。
出乎意料的,范阿姨只是望了望我,然后问了句:“听小晨说,前几天的鸭血粉丝,是你特地赶去南京买来的?”
我微微一怔,宗晨他怎么知道,竟也没与我说起过,我点了点头,说“是。”
她一只手抚着轮椅上的把手,那已经被磨出一道明显的痕迹,许久才眯着眼,莫名说了句:“小浅,难为你了,只是……再去为阿姨买一次,行吗?”
这时的天,带着清晨特有的冷冽气息,我像是走在冰柜里的冰棍,虽然裹着大衣,冷意依旧直溜溜的往衣角细缝里钻。
街头等了很久,才见一辆出租过来,到了车站,正赶上五十分的车。
车开了,只坐了不到一半的乘客,我闭上眼,睡意很快袭来。
经过一条漫长的隧道,有着沉闷的空气与暗黄的光线,朦胧而模糊,不过在这样的甬道里,车子却要加倍小心行驶,出口处有亮成一圈的光晕。
视线陡然转暗又变亮,我睁开眼,忽然想起,自己曾有过的那段暗涩灰沉的年岁,就像是这样,人生轨迹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