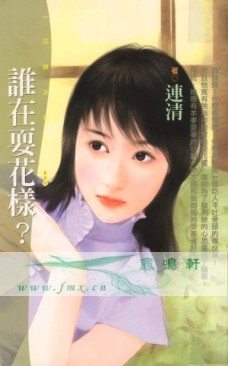花样年华:海上女星罗曼史-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叫许飞琼。
许飞琼很快成了舞厅头牌,不管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还是《美酒加咖啡》,只要她一上场,场面上就气氛热烈,红男绿女如群魔乱舞。许多面带**笑的男人会上来“咸猪手”,这是做舞女必修的一课,她躲让着,一直退到角落,一双温情脉脉的眼睛电着她。
他姓褚,一位斯斯文文的记者,在酒后拥抱了她,那份温暖满怀满抱,她的心像一块坚冰,慢慢被融化。她其实一直在拒绝、排斥,即便在舞池里飞旋,她的心房也是关闭的。这个褚记者如春风似春雨,或者说他的到来是春风化雨。少女像酒后微醺浅醉,醉倒在他的怀中。他在她耳畔喃喃地说:“跟我到上海去,海上纸醉金迷金银成山,那里才是我们要生活的地方,我帮你找份工作,我们再成一个家,今生今世再不要分开。”她一直犹豫着,不肯正面回答他,也是有点怕,还有点放不下病中的父亲和憔悴的母亲。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下班回家,刚刚走到院门口,就听到家中有人吵吵嚷嚷,陌生人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不还钱我要报警了。”母亲一个劲哭着恳求债主再宽恕几日。那个穿熟罗对襟褂的胖男人说:“其实你们家有偿还能力,可你们就是赖着不还,瞧瞧你们家如花似玉的女儿,听说是欢场头牌,再不还钱,我就拿她抵债。”舒绣文听得汗毛根根直竖,当晚不敢回家,跑到褚记者那里。褚记者心里暗笑:此乃天助我也,白捡个大美人。他当即说:“为了不让你进火坑,我们的事宜早不宜迟,这就起身赴上海。”舒绣文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这这这,这不是私奔吗?我母亲都不知道。”褚记者说:“事到如今,你还管得了那么多?逃出虎口再说,回头写封信告诉你娘,再寄一笔钱给她,也算对得起她的养育之恩。上海是什么地方啊,那里的银元金币像树叶,你这样的大美人去了,只管弯腰捡钱。”
舒绣文眼一闭,就把命运交给了这个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小男人。
从狐步舞开始
小男人不是大男人,小男人就是小白脸,小白脸长了一肚子花花肠子,还小肚鸡肠,跟着这样的小白脸,舒绣文不会有好日子过。果然,到上海不久,褚记者另有家室,也是俗到家的老套路,舒绣文不会寻死上吊。虽说气得鼻血如注,也只好捏住鼻梁将脑袋瓜子往后一仰,将鼻血倒灌回去。凡美女总会遇上人渣,这是规律。就当走夜路一脚踩到牛屎上,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命不好,到河边洗掉牛屎粑粑,重新上路。几天后,舒绣文花红热闹地出现在同样花红热闹的老上海霞飞路上,她做了俄国餐厅的女招待。
是红花总会有绿叶陪衬,是月亮一块云彩哪里挡得住?即便做些端茶上菜的小事,舒绣文也很快就引人注目。来俄国餐厅吃饭的,绝非贩夫走卒,电影人王云卫、顾文宗发现了她。小姑娘一口京片子说得可好听,当时女明星陈玉梅是天一制片公司女老板,正托人帮她物色一个国语老师。说出来舒绣文喜出望外,进入陈玉梅家,就算是一只脚踏进了影视圈。不多久,陈玉梅公司缺一个演丫头的,不说话,就送一杯白开水。第一次站在水银灯下,舒绣文紧张得一身是汗,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轮到她上场,偏偏没看见脚下的电线,绊了一跤跌了个人仰马翻。陈玉梅老公邵先生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从哪里找来的小蠢货,你知道这个进口胶片多少钱一尺?你给我浪费了多少尺?蠢货。”一连骂了七八句,舒绣文气疯了,一时倒灌的鼻血冲了脑,当场甩手走人。一边走一边想:本姑娘就是要做成大明星,压你陈玉梅三头四头五六头,到时候看我大牌气死你。
老上海霞飞路上走了几趟,舒绣文发现,以舞女身份在歌舞升平的上海滩混碗饭吃不算难,她报名到集美歌舞团做了舞女,艳舞热舞什么舞都跳,包括贴面舞**。油头粉面的男人见识多了,又加入五月花剧社和艺华公司,那是老上海电影的黄金岁月,像舒绣文这样一身是戏的漂亮舞女,想不走红都困难,她演了一连串的小角色,不管是筱文艳,还是马香兰,凡角色在她眼里从无大小,一律入戏十分用心去演,渐渐有了名气,薪水如春江涨水,一路涨到每月六十元。生活安定,爱情敲门,舒绣文在重庆认识了吴家少爷吴绍苇。
吴绍苇是山东人,当时在重庆读大学,吴家开钱庄,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商大户,本指望吴绍苇学成归来继承家业。但是造化弄人,吴绍苇偏偏喜爱舞文弄墨唱念做打,在学校里排演文明戏,请一些导演来指导。王云卫相中这个年轻人一表人才,极力撮合他与舒绣文这对才子佳人。吴绍苇自然知道舒绣文,他对这位来自银幕上的美人既迷恋又崇拜,能娶这样的梦中情人,那是他一生的福祉。两个人不久情定终身,可是来自山东老家的消息却出人意料。母亲在电话中声色俱厉,像他们家这样的名门望族,门当户对非富即贵,怎么可能娶一个戏子为妻?女掌门放出如此狠话,大少爷也不示弱:舒绣文我娶定了,不需要你们同意,大不了,我们此生不回山东。小夫妻很快成就鱼水之欢,小日子也过得风生水起,但是来自山东的巨大阴影如同乌云,时不时给小家带来一场狂风暴雨。
抗战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春天,舒绣文携夫回到上海,在昆仑公司投拍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她成功出演了刁钻恶毒、骄横跋扈的“汉奸夫人”王丽珍。这个角色不但开启了她最辉煌的演艺时代,也成为一个艺术经典,在后代无数影迷与影人之中,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小戏子,就这样熬成了大明星。
我就是个戏子
《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后,舒绣文也曾红极一时炙手可热,但那时只是演技上的。一九四九年后,在政治上她才迎来属于她的火红时代:很快入了党,当舒绣文与陶金在经典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文联、剧协、妇联、友协等一大批社会团体中拥有一大堆头衔。而吴绍苇仍然只是个电影厂的小制片,每天的工作就是跑跑腿买买道具什么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一路萎缩下去,在单位是个溜边的角色,可有可无,与舒绣文生活在一起,两人有了巨大的反差。到了一九五七年,一个暴雨如注的夏日,舒绣文被市政府的专车送了回来,她悄悄走进吴绍苇的亭子间卧室,这对貌合神离的夫妻已经分居三年。看到舒绣文进来,吴绍苇有点吃惊,他知道他一直回避的问题再无法回避,他从床上坐起来,等待舒绣文开口。
舒绣文说:“我马上要调到北京人艺去。”吴绍苇并不吃惊,淡淡地说:“好,你去吧。”舒绣文突然冒出一句:“我,希望你也去。”吴绍苇断然拒绝:“我不去,我不去,我去北京能做什么?做你的陪衬人吗?”他并没有直接发怒,但是他也曲折、隐晦地表达了这些年来对舒绣文的不满:好出风头、抛头露面、结交权贵、彻底革命。舒绣文看到他如此态度十分不满:“你为什么不去?你为什么要做我的陪衬人?没人逼你,也没人强迫你,是你这些年不求上进,不求进步,我还嫌弃你拖我后腿。”吴绍苇彻底激怒了:“我拖你后腿,好啊,这才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想当初我家大富大贵,我母亲还嫌弃你,极力阻止我们结婚。现在你时来运转,嫌弃我了,嫌弃我拖你后腿了,你走吧,我也不想天天仰着脖子看着你,太累。”
夫妻俩大吵一场,舒绣文心里五味杂陈,临走时两个人又谈了一次,吴绍苇还亲手做了两道上海菜:金针菇烧烤麸和腌笃鲜。两个人面对面心平气和地坐着,舒绣文突然湿了眼眶,哽咽着说:“十几年夫妻做下来,我还是诚心劝告你,跟我去北京。”吴绍苇说:“你这样说我很感动,我不阻拦你,你也别阻拦我,你给我一年时间考虑考虑,然后我再答复你。”舒绣文只好点头,也只有点头。
舒绣文来到北京,主演了《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关汉卿》中的朱帘秀和《伊索》中的克丽娅,再度走红。即便红得发紫,她仍然没有忘记当年在重庆爱过的那个喜欢文明戏的文艺青年,是他顶住家庭压力,爱上她这个还没有成大名的小戏子,她想起来就十分感动,提笔写信到上海。吴绍苇不给她写一个字,舒绣文彻底绝望,准备来上海找他。他却过来了,是一个刮大风的晚上,院子里全是落叶。舒绣文半夜坐车回家,不是黄包车而是高级小轿车。院门口站着一个疲惫的老男人,是吴绍苇。恍惚间舒绣文以为她还是当年的小舞女,她迎上前,笑眯眯地说:“你来啦?”她开门带他进来,正在泡茶,吴绍苇说:“你别泡了,泡了也是浪费。”舒绣文觉得来者不善,愣了片刻,吴绍苇从包里拿出两袋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放在桌上:“这是你最爱吃的,我住在旅馆,明天,我们一起去离婚。”舒绣文脸色发青,说:“你是这样想的?那你想好了。”吴绍苇说:“我想好了,我也不瞒你,我在上海找好了对象,就等着和你离婚,我只想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舒绣文哭了,无声地流着泪,吴绍苇想劝他,她却哭得越发不可收拾,哭完后她平静下来,对吴绍苇说:“我就是个戏子,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
几年后,舒绣文患肝病去世,走的那年才五十六岁。吴绍苇在上海,没来送她。
19。放下你的鞭子
王莹
放下你的鞭子
王莹:放下你的鞭子花样年华····叫宝姑的童养媳
王莹出演电影剧照王莹她的乳名叫宝姑,生于安徽芜湖一个小职员之家,父亲喻友仁在南京任英商亚细亚洋行稽查,十天半月难得回家一次。宝姑和在圣雅阁女校当老师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母女情深,她后来随了母姓,并在多年之后取名王莹。
母亲在学校里教音乐,家里有钢琴、手风琴,宝姑从小生活在音乐中,听到优美动人的音乐就翩翩起舞,母女俩生活在富足而安静的小城芜湖,父亲的缺失似乎并没有留下太多遗憾。宝姑八岁那年,灾难来了,母亲病故,父亲娶了个后妈,后妈刁蛮凶悍,对王莹十分苛刻,将她远远地送到郊外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后妈要去南京和父亲团聚,嫌宝姑妨碍他们生活,私下里将宝姑卖到南京城南糖坊廊薛家,给薛家老二薛少白做童养媳。
童养媳的生活很悲惨,宝姑和家佣住在一起,吃饭一定要在灶间,不允许上桌,而且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扫地抹桌倒马桶,所有下人做的家务活她全包了,还动不动挨打受骂。那一年宝姑只有十三岁,十三岁的宝姑什么苦都能吃得下,但是没有书看让她生不如死。有一天她在青砖铺就的廊檐下看到薛家少爷薛少白,薛少白正在读一本上海出版的杂志《礼拜天》,宝姑很想看。平时没事时,也有女佣隔着雕花窗户指着薛少白告诉他:“那个就是你的男人”。听到这样的话宝姑总是耳热心跳,她觉得这都是假的,因为她从来没有和薛少白说过话,甚至两人都没有正眼看过,但是这本杂志让她对薛少白涌起强烈的好奇心,或者说她对那本杂志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她太渴望读书,然后提笔写作,这是她心中一个隐秘的梦想。卖到薛家做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