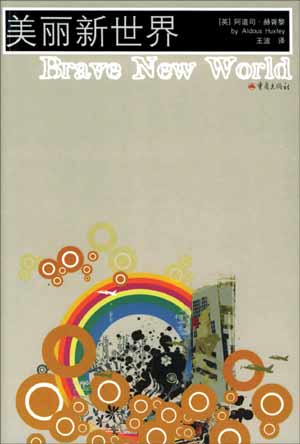世界三部曲之一国色-第6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代里到过的地方,或被历史逼迫他们通过的绝境,哪有什么海阔天空?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心灵压抑,和当时创造历史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阿果把车停在一丛寂静的松柏树下,树丛中隐隐闪现出一座黑黝黝的独家院落。院落侧面墙已经倒塌,倒塌的地方正在修建。一盏灯光从倾斜的房梁上射出来,默默地把小院的晚景,留在周围一片通明的灯火中。阿果告诉我,那是当年的红军作战指挥部。朱德曾经在这里指挥红军后来的一场场追歼国军川军民团的战斗。我大吃一惊。可以进去看看吗?阿果说,不必了,现在进去什么也看不到。正在拆迁,不久,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唉,真遗憾!我说,能不能把车开到外面去,高一点,宽阔一点的地方,看看咱们这个县城最美的晚景?他说,好,城东,崭新的刚刚修建起来的康巴大桥。
奇遇(2)
康巴大桥,雄壮威武,像一条飞腾的彩虹和蛟龙,横跨滔滔大渡河,连接起从内地通往雪域高原的通道。华灯齐放,站在高高的桥头望去,散落在黑黝黝的凤凰山和海子山峡谷中的整个泸定县城,尽收眼底。这是我第一次在夜色中观看这座英雄的高原县城,看不见它的房屋结构和街道走向,但那条弯弓般穿过峡谷底部的河流,带着两岸楼房瓦屋的暗影和无尽闪烁的灯火,急匆匆蜿蜒而来,注入康巴大桥底部远去。那时,我还没有听到大渡河的吼声。在灯光点点的河湾里,有一排整齐的高楼。高楼里射出规则的日光灯光,在寂静的远山中显得那么耀眼。戴耳环的小伙子告诉我,那是沙洲坝,处于大渡河的南岸,是过去的一个天主教堂。当年毛泽东在教堂里待了一两个小时,讲了话,就徒步沿着南岸的小路走上了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泸定桥。当年,杨成武就是在那个天主教堂里,动员讲话,组织鼓舞先头部队夺桥的勇士。只是现在,天主教堂已经无法寻觅。灯光那里,是县城唯一的一所重点中学。此刻,我也没有听到读书的声音从那里传来。当年生死存亡激战的喧嚣,已经掩盖了所有后来的声音。从那排明亮的灯光望过去,有一排长长的灯影,在高朗的天幕下横跨泸定县城,把上下半城的万家灯火分为两半。那排灯影下,有汽车流萤似的穿梭来往。
“那就是泸定桥?”
我问。
“不是。”
阿果说。
泸定桥上不可能有灯光。我们只能看到桥两头的桥头堡,现在也隐隐约约有点点灯光闪烁。但我心中的泸定桥,还笼罩在高原县城的夜幕中,没有揭开神秘的面纱。往上,我似乎看到遥远的天空下面,还有一串灯影和暗影。我问,远方那排细小的灯影下面是什么?他说,仍然是一座桥,可是,那座桥自修起来之后,没有使用过,也许是为了以后某个时间会派上渡河的用场。灯光闪烁,缀满夜空。大渡河两岸,远远的,我看到了一座座桥的灯影,而我真正要想看到的泸定桥,还是灯影中的一条若有若无的曲线。就是那座决定红军生死命运的铁索桥,当年为什么就只有那几根铁索才能通过?而现在一座座大桥飞驰而过,横跨大河,有的甚至那么费力地修建起来,没有用处废在那里,变成了一座以桥为图腾的高原县城精神的象征?是不是因为当初没有铁索之外的任何通道,吃尽了苦头,于是,就在这条汹涌的河流上修建更多的桥梁,来显示我们自己,不会在任何被隔绝的道路上无法摆脱困境,那样一种征服的欲望和决心?
第一次面对大渡河,听到它那独特的语言和汹涌的涛声,看到它那神奇汹汹的面容,是在我随便找了一家宾馆住下来以后。那时,天色已晚。散发着柏油水泥混合气味的新城区大马路上,空无一人。偶尔一辆出租车,在晶亮的路灯下疾驶而过。走在宽敞洁净的马路旁,一堆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的石头砖块杂物,山包一样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在垃圾堆旁的路灯下伫立良久,似乎不知什么地方,有均匀而激烈的流水激荡声,隐隐传来。咕咕……哗哗……,一阵阵沉闷清脆、响亮零乱的奏鸣。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站在山包岩石后面,眼前出现了宽阔的大片大片的水面。果然,似平静,又是那样汹涌着向前流去。似乎水面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卷起大渡河的涛声。对面北岸,是若隐若现的海子山的剪影。一河流水,如一锅乱粥,卷不断的波纹,数不尽的涛声,转瞬即逝的水面,给我留下大渡河静默夜晚匆忙而喧哗的身影。离我站的那片悬崖下好几百米远,变幻着水形的河面上,一条曲线隐约镶嵌在两山峡谷寂静的夜空中,我想,那可能就是承载过多少人苦难和命运的泸定铁索桥。
沿着旧城河岸,没入晃动的人流,我慢慢走向南岸的桥头堡。顺着梧桐树荫下的一排精致小楼,远远望去,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昏黄的路灯下,一座画栋飞檐、雕刻精美的桥头建筑,出现在我眼前。那就是当年红军冒着硝烟烈火冲过来飞夺的桥头阵地。桥头堡对面是一地零乱的砖头瓦块,街面旧房瓦屋已经撤去。远远近近堆放着商贩们的货物。那是来自深山里的核桃、板栗、石榴、苹果,还有大捆的药材高耸其间。我没有对那些货物发生兴趣。望着古老青色砖木结构的桥头墙壁,那时,坚固的铁栅门已经紧锁,只留下一条可以侧身挤进的门缝。侧面砖墙上的售票窗口也已关闭,上面写着过桥的价格,每人十元。我正犹豫,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打量着我,并告诉我现在已经停止卖票。如果要过到桥对面,可以从门缝里钻进去。我往后退了几步,当年鏖战的硝烟隐约升起。怎么办呢?既来之,则安之。我想只能用这种独特无奈的方式,瞻望心中神圣的铁索桥。请先辈们原谅我的不敬,晚辈遇到的困难,看来只有这样由我来独自处理。我慢慢走过去,手握冰冷的铁门,侧过身子,蹩了进去,突然觉得掉进了一片空旷的精神旷野之中。没有硝烟的桥头,两边大半人高的石头座基,坚固硬朗,上面拉着的正是那一根根冰冷的铁索。铁索和底座基石都已磨得溜光。铁索外面河面上架起的,正是铺上结实木板的铁索桥。踏上铁索桥的木板,便会感到一阵摇晃。我从遥远新城区柏油路旁的悬崖后,看到的那片广阔的沸腾着咆哮着的河水,此刻,正从桥下匆忙喧哗,急躁汹涌地穿过。也许,我已经感受到了大渡河在群山峡谷中多年养成的性格。顺着铁索桥望过去,长长的百米开外的河岸上,挺立在隐约海子山脚下的是和南岸同样形状的桥头堡。当年,红军从对面攀缘铁索一路攻打过来。夜色迷迷。来自冰山大川的大渡河上游飒爽的晚风,撩起我额前的头发,虽然时值深秋,也有凉意从我心灵深处油然升起。手握粗硬的环环相扣的铁索,寒意陡然。当时守在这头的仅仅是地方武装民团。天空高朗,两山静默。铁索悠悠,唯有那倔犟而汹涌的河水,带着它独特的性格奔涌而去。下游,还有更宽更长,有时也许更狭窄的激流,需要它去穿越。时光飞逝,当年的战斗场面犹存。我那《国色Ⅰ号》油画系列,仅凭历史资料和语文课本给我的灵感,给了我军外内艺术界、美术界的荣誉和地位,可是,真到了这里,飞夺泸定桥的原址和旧址,站在铁索桥的晚风中,我突然感到,我并没有画出什么,也不大可能真正“画”出什么。历史与人民之间,历史、人民与它的军队、军人之间,究竟在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文化与生命联系?手扶铁索,踩着木板,脚下似有水声汹涌而上,直捣心窝。我的脚步,有点晃荡,努力往前试了几步,桥下的水流飞逝而去,听起来心惊胆战。当年的勇士怎样穿过铁索,又怎样在枪林弹雨中掉进河水,怎样被那锅沸腾的激流卷走的呢?哪股激流,哪根铁索,哪朵浪花,哪片天光云影,在泸定桥驻足,激起了当年伟大领袖诗人“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意和灵感?望望天空,高原的秋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对岸没有当年匆忙而顽强的身影,偶尔有夜行的车影,沿河岸的马路,在静默的黑黝黝的山脚下,游萤一样飞逝。
奇遇(3)
我深深叹了口气,带着还没有穿越铁索桥的遗憾,慢慢转过身,回到了桥头。桥头右侧,一排精致的茶楼,挑着绿色的旗幡。当年沿街低矮的瓦屋,已完全撤去。桥东头街面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整齐的梧桐树丛中,一排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古色古香。商铺饭馆旅馆,紧密相连。崭新的玻璃门缝里,透出香气四溢的山珍味。城门下游数百米河岸,是新开发的商业区,经营茶楼、小吃、歌舞厅、网吧和洗浴城,一排红灯笼,在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映照下,伸向下游远处。歌声飞扬,彩灯闪烁,构成大渡河岸生机勃勃的晚景。漫步在整洁的河岸长廊,看到茶楼、鱼馆、小吃火锅,差不多都已满座。烧烤的火炉,摆放着腊肉、香肠、青菜和河里的鱼虾,散发出诱人的清香。红色歌城的招牌,在夜空下亮得惹眼。响亮的歌声,强烈的音乐,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似乎面前那河滔滔的流水喧嚣,都被歌声掩盖。歌舞厅门前,无一例外地坐着一群群矮矮的小小的浓妆艳抹的姑娘,虽然打扮得不十分洋气,妆化得有点拙劣,但也极强烈地表达出山里新生代的姑娘们,走进现代生活的热情和追求的信心。突然,一群姑娘,看样子十四五岁,从响着嘹亮音响的房间冲出来,围在河沿走廊上和歌舞厅老板吵架。姑娘背后,站立一群穿着打扮怪异的男人,他们似乎为了什么要命的事情而争夺着什么。我远远望了她们一眼,那些山药蛋似的姑娘,虽然个子不高,但穿得很露,眼影浓浓,嘴唇涂得很红,吵架时亮红的嘴唇翻得又急又快。浓眼影后的眸子里,流露出撩人甚至逼人的目光。急迫而不满,亮闪着仇恨。通过她们大胆露出的胸部、脖子和粉嫩的腮,我发觉她们实在很小很嫩很年轻。而眼光,怎么看起来像凶恶的雏鸟?她们争吵着,劝说着,叽叽喳喳,闹成一团。我想,那么小的姑娘,哪来那么多那么深的仇恨,要堵在如此美妙的河边夜晚中吵闹骂人?我绕过她们,在一排腊肠鱼虾烤摊前走过。走着走着,下面河湾里,那排更亮,也更冷清的长廊,交相辉映着淡蓝粉红鹅黄的霓虹灯光。那是洗浴城。将近八点,也许还没开张,也还没到达服务的高峰时刻,显得十分寂寞神秘。洗浴城究竟有没有一个响冠全球的红色名字,红军,或者长征,我不得而知。我蹩足在通往洗浴城的长廊上行走,突然,十里开外的尽头,柔和灯光下,一位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姑娘,从灯影中闪出来,手扶河沿整齐的栏杆,望着我,似乎在招手、在微笑。我停下脚步,侧身望着面前奔腾湍急的河水。姑娘似乎对水面没有兴趣,还用婀娜的身影,微笑招手。我横了心,想走过去看看究竟。突然,姑娘的身影从光影里消失,我不知道,她那被柔媚灯光和咆哮大渡河的水声,装饰过的婀娜身影,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我顺着长廊,不紧不慢地走过去,顺着河边,顺着灯光,那一扇扇装饰得明亮整洁的房间里,有怪怪地来自山里的药香味飘出来,刚才那位少数民族姑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