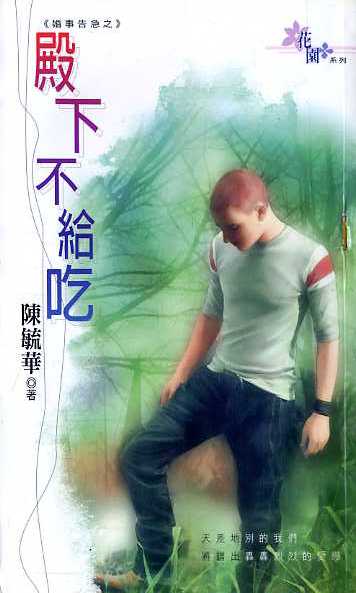殿下骑着竹马来-第5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件事议定之后不多久,就到了除夕了。
爆竹声中除旧岁,春风送暖入屠苏。
正月初一,宫中备下宴席庆贺新年,从季涟最小的妹妹泠开始到季涟张太后,一个一个的饮屠苏酒,以示祛疾辟邪;接着是上元花灯节,长安城里各处都是一派繁荣景象。
开春后,平城府传来急报,阿史那摄图定突厥各部仪制,以玄色为底,白鸿为记,统一军帜。
山西巡抚孙思训已有六十余岁,在边关驻守多年,一向以坚壁清野、铁桶防守而著称,在符靖和符鸢到达平城之后,更是如虎添翼,把整饬军纪和操练骑兵作为第一要务,颜柳去了之后,也常和几人一同出去巡查边关地形。符葵心到了阳宁之后,竟然安分不动了很久。季涟接到从滇藏送来的档案里说符葵心最喜带着一小队精练人马出去扫荡突袭,而且打完就跑,不给人追击的时间,现在居然也照着兵部拟定的大方案坚守不出,倒是难得。
四月,庆寿长公主淑下嫁太傅之孙史桓,史桓的祖父史崇乃是四朝元老了,为人宽厚,谁也不得罪,也不参与各派党争,但在朝臣中的影响力尚在。家中屡得禁中赏赐,子侄也都领些各部闲职,虽不出色倒也安稳,这样的人家,倒是极适合尚主的。玦儿年前就照着这样的准则选定了范围,然后让季涟过目,请得张太后和江淑瑶的示下后定下的人选,钟太嫔也颇为满意,她原本就知道女儿是不可能嫁给什么王公贵戚的,只求不被薄待也就心足了。
出嫁之前,嫁妆箱奁俱是玦儿从上到下一手打点,比永昌帝的几个女儿出嫁时的嫁资还要厚重许多,季涟又加封史崇为文成伯。归宁时,又进淑为越国大长公主,遥受封地,之后钟太嫔自是对玦儿感激。
皇家的喜宴尚未完结,边关已燃起烽火狼烟。
阿史那摄图在四月末率二十万突厥铁骑,急攻平城府。
到五月,玦儿仍没有一丝有孕的迹象,季涟一面忧心平城的战事,一面又为着这个焦急。玦儿向高嬷嬷请教了无数的偏方秘法,仍无济于事,季涟只好暗地里请太医院的太医来诊治,经了七八个太医,只得出一个玦儿早产体弱,先天不足,又忧思过甚的结论,开了好些方子进补。
季涟想着宫里的事情本就多,玦儿之上还有张太后和江淑瑶,自是事事操劳,又常常不眠不休的陪着自己,忧思过甚四个字必是从此而起,心中更加不安,于是变着法的找空陪着她。玦儿自得了太医的诊断,心中便常惴惴,知道季涟此刻是无比的想要一个孩子,坐实了储君的位置,内安才好攘外。季涟见她如此,只好一意的劝她,说自己并不急,况且二人现在都还年轻,养好了身子多等几年也是无妨,又密令前来诊治过的太医严守口风,否则严惩不贷。
六月,阿史那摄图在围攻平城月余不果后,突然挥兵西向,围攻北庭。
季涟看着北庭三日一折五日一折的加急战报,心情烦躁不安,玦儿陪在一旁,也不知如何劝慰他,只想着不能出主意,能陪着他也是好的。季涟虽平日里看起来脾气甚好,奇Qisuu。сom书在臣子们面前更是刻意收敛,回到长生殿却不免牢骚,玦儿先前常打趣他,闹得他有气又不好发,每每无可奈何的样子;现在却是事事顺着他的意,好让他把全副心思都放在北线军务上。
没几日玦儿又收到孙家送来的信,季涟看玦儿看信后脸色怅然,便问道:“家里可有什么事?”
玦儿叹道:“我爹——在苏州的小妾生了一个儿子,真不知道是该替爹高兴还是替娘伤心。弟弟在家里也不肯好好念书,学什么都是两天就丢开了,娘心里不好受得很。”
季涟问道:“你爹呢?还在苏州?要不——你写信劝劝你爹,免得你爹和娘老是这样子”,他心里本就事多烦杂,又看到玦儿为家事烦忧,不由得长叹了一声。
玦儿撇了嘴道:“才不写呢,他的信我可一次都没回过,谁让他这样待我娘的,我在家的时候,发誓赌咒跟说顺口溜似的,转头就忘了。我娘一日不理他,我也不理他!”
季涟知道此时不可再帮她爹说好话,不然根据经验矛头迟早转向他,只是他想着玦儿他爹也不至于就犯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让妻女这样怒目相向。男人三妻四妾本是常事,照往常玦儿所说,杜蕙玉嫁过来时,也是有几个陪房丫头的,玦儿幼时进宫后不久收房了一个,只是未过明路,苏州的那个,据说是孙璞未及报备就先在苏州讨下了,这才惹得杜蕙玉翻脸……
玦儿看着季涟无可奈何的样子,笑道:“我知道你在替我爹抱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有多羡慕他呢。”
季涟想着她有小半年不曾这样抢白自己了,只好陪着笑道:“你别一棒子打死天下人,我一向是守身如玉坚贞不屈的。”
宫里的陈娥卫女倒确实是有许多,只是季涟每日里除了祭典朝议等事别的时候都是呆在长生殿的,轻易也没个什么机会去尝个鲜;再者这尝鲜的风险实在太高,玦儿平时自是什么事都依着他,吃什么穿什么从上到下的替他打点好,在这一点上却是原则坚定,就为了尝尝不同的味道就得罪于她,倒实在是不值得;再则万一不小心在哪儿撒下点种子,那他以后想要立玦儿生下的儿子做储君,难度顿时增高几分……在这种种原因之下,他便觉得还是自己老老实实目不斜视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玦儿听他这样的话没有一百遍也有九十九遍了,自不去理会他,只是发愁家里的弟弟顽劣不堪,小小年纪就学得挥金如土的毛病,不知如何管教。
季涟并不曾管教过幼弟,自己还没有孩子,自然更加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劝道:“你家里既没有人管他,何不把他接到长安来,我找个人去教教他,你也能时时去看他,这样可好?”他估摸着朝廷里的那些言官,三天两头的把他批的狗血淋头,他还打不得骂不得——不信这样的人,管不好一个毛头小子!
玦儿摇头道:“还嫌现在不够招摇么,在杭州好歹大家都看我爹几分薄面,他作出什么上不得台面的事情,还有人替他打点一二。要是到了长安,只怕咱们天天替他善后都来不及。”
季涟疑道:“他再怎么也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能做出什么事来?”
玦儿气道:“才十二岁呢,就跟着人家去勾栏院——这还是好的,反正他去了也还只是听听曲;要不就是跟些不三不四的人整天跟游街一般,好像自己是开善堂的,动不动就要资助别人一二,也不管别人是缺银子还是讹他。爹原先请了无数教书先生在家里教他,每一个能看得住他的;等他过了十岁,爹说让他到杭州城我家几个铺子走动走动,若是念不好书,学着怎么经营守住一份祖业也是好的——他倒好,三天两头的往外头撒银子,一点都不知道那也是辛辛苦苦挣回来的。”
季涟想着豪门富户,一向是容易出这样的败家子的,只是他到底是玦儿的弟弟,难免爱屋及乌,觉得兴许是少年顽劣,只要严加管束便好:“既是喜欢败家,让你爹娘这上头管住他不就好了?”
玦儿摇头道:“你以为这法子没用过呢,去年听说就用过这法子,关着他在家,不给他银子用。他总能想着法子偷偷跑出去,弄不好还撞出一身伤,家里也不敢关了;不给他银子用吧,他在街上兴头起来了,能把自己的衣裳、身上的扳指、佩饰全都给当了换银子——到头来还要管家去一个一个当铺的寻回来,倒是费神,你又总不能让他光着身子出门吧!”
季涟听着便笑起来:“我以为只有你小时候调皮,原来你弟弟比你还能耐”,看着玦儿脸色不善,忙道:“好了好了,我说笑的,兴许再过两年,等他再大些,自然收心了呢。”
玦儿心中只是抑郁,她和季涟一般,都未教养过孩子,除了心底里发愁,倒确实无他法可想,便向季涟道:“这事我一时半会儿也急不来,你还是忙你的事情去吧,免得误了正事。”
提起正事,季涟的脸色就垮了下来,翻着白眼叹气,北庭、阳宁和平城乃是京城往北的三道屏障。阿史那摄图先前久攻平城未遂,已知平城守卫的孙思训和符靖非轻与之辈,只好转向同为西边壁垒的北庭和阳宁,虽然阿史那摄图在草原上横行十六年未尝败绩,但是此时面对平城如铁桶一般的防卫,为了抓紧时机一鼓作气,也只得转攻北庭了,况且北庭一向守备较弱,自然成了阿史那摄图此时的首选。
前线送来的战报自然是不容乐观的,北庭将士死守大半月,突厥骑兵虽尚未攻下北庭,但北庭守兵已损伤大半,向朝廷求援,朝廷却无法派出增援的部队——平城那里无法抽派人手,而处于北庭后方的阳宁,早已派出了一半的援军,其他的部队若前往北庭,一旦北庭失守,则突厥骑兵到达阳宁时已无兵可守,便可长驱直入,直抵长安城下。
玦儿见季涟脸色阴沉,站起身来,揽过他的头问道:“北边——情况不好么?”
季涟闭上眼,搂着她的腰,低声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半个月过得比以往半年还艰难……不知道北庭还能守住几天,可每天看见那些臣子们,我还得给他们打气,跟他们说天朝将士同仇敌忾,定能将蛮夷驱出国门之外……可是,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史那摄图,怎么来的这样快,原以为能拖得两三年,谁知道他说来就来——上天为何对我如此不公!”
玦儿俏皮笑道:“圣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阿史那摄图,可不就是上天派来考验陛下的么~”
季涟看着玦儿这样轻松的模样,有些哭笑不得:“你是真不知前线有多危急,还有心思说这样的玩笑话——现在的情势,只怕北庭就要守不住了,再到阳宁那里,就算我御驾亲征,也没有什么把握。”
玦儿笑道:“你每天这样唉声叹气的,我怎么不知道前线危急,可历朝历代,只有那烽火戏诸侯的周幽,才会被犬戎长驱直入;而那些励精图治的君王,即使如西楚朝那般有几次甘泉之警,也只是最后成就帝王伟业的一个过程而已。我相信你不是前面那一种,所以才有此信心啊。”
季涟仍有些不自信的问道:“真是如此么……也许是上天惩罚我呢。”
玦儿笑问:“你又没做错什么事,上天作甚么要惩罚你——莫非你是做了什么对不住我的事情,所以心虚了?”
季涟欲言又止的,闷了半天才笑道:“也许上天见不得我和你这般好吧。”
玦儿又和他历数前朝往事,道:“……便是那屠尽所有兄弟逼父亲退位的文宗,登基后行仁政减徭役,一样赢得四方臣服,可见君王只要谨记圣人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明言,便能使国富民强,即便有兵临城下之危,也定能转危为安的。”
季涟这才缓了缓神色,半晌才道:“皇爷爷和父皇,对我期望甚重,我总怕有什么做得不好了,丢了祖宗颜面——我在你心里,真能和这么多尧舜之君相比么?那怎么乌台那些御史,天天把我骂得死去活来?”
玦儿笑道:“要是满朝的御史每日都对你歌功颂德,那才是不妙呢,那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那个什么人不就如此么?他倒是听不到有人骂他,最后却被放逐了呢。”
“周厉王。”
“哦,是嘛,你看你知道的这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