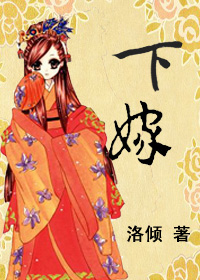下嫁(GL)-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欠债还钱确实天经地义,她又没说不还,只是时间罢了,宣瑾冷声道:“哀家不觉得亏欠景王。”
在水轻灵听来却是另一回事,夏炽陌为宣瑾所做之事,她可是一路看过来,若是有人如此对她,她就算立即毙命,此生也值了,更觉太后薄情寡义,就算不接受,至少感动一下,也不枉主子痴心一片,左右无人,又身处宫外,水轻灵再顾不得那些繁文缛节,此刻的宣瑾,在她眼里,哪还是高高在上的太后,就是一个拒绝景王感情的女人,怒道:“我真替王爷寒心,竟然爱上你这样的薄情女人!”
“放肆!”宣瑾虽是好性子,但是毕竟是太后,哪容人如此挑衅她的威严。
水轻灵说完后才知失了轻重,不过说都说了,索性心一横,再多帮夏炽陌说两句公道话,就算是被太后责罚,也值了,便道:“奴婢还有几句话,说完后,任由娘娘处置。”
宣瑾也想知道夏炽陌到底为她做了什么,让水轻灵如此维护,自己也回想了一番,夏炽陌除了在朝堂上听了她的一些建议外,并没有为她做过其他,反倒是如登徒子一般三番四次轻薄于她。
宣瑾道:“你且说来听听,你若瞎编乱造,别怪哀家降你个以下犯上之罪。”
水轻灵毫不畏惧,很多事都是她亲身经历,怎么可能假的了,直接道:“娘娘还记不记的那年,还是太子的皇上染上恶疾,连宫里的太医都束手无策,后来被一个民间神医医治好。”
宣瑾自然记得,若不是神医来得及时,凛儿差点性命不保:“这事与景王何干?”莫不是夏炽陌请来的?当时情急,她只顾着让神医救人,至于神医从哪里来,倒是没问,只听说好像是哪个太医的至交好友,后来凛儿病情稳定,想要赏赐神医时,神医已飘然远去。
水轻灵道:“那个神医有个怪癖,救贫不救富,王爷跋山涉水找过去,神医却怎么也不肯出山,后来还是王爷放□份,穿上粗布衣服,在他药庐里整整待了三天,洗衣做饭,端茶倒水,我当时就陪在王爷身边,王爷却不让我做,而用自己的诚心打动了神医,神医这才答应出手救人。”
这些宣瑾还真的不知,喃喃道:“原来是他。”就说先帝一直主张的是用他所练丹药救凛儿,被她断然拒绝,又怎么会为凛儿请神医。
水轻灵又道:“娘娘是否还记得您差点被罢黜的那一回?”
宣瑾自然也记得,先帝连圣旨都下了,她在冷宫里待了一个月后,先帝竟神奇的将圣旨收回,弄了一出闹剧,难道又是因夏炽陌之故?
水轻灵道:“当时王爷正在边关打仗,听说娘娘被废,连夜赶回京城,王爷跟皇上说,她这次为大楚打下三个城池,不求奖励,只求恢复娘娘的中宫位置,若如不然,她就将三个城池物归原主,先帝不得已,只能答应。”
宣瑾对这些又是一无所知,当时还道是朝中大臣给先帝施压,先帝才不得不收回成命。
水轻灵又说了其他很多事,而这些事,宣瑾都只知表面,不知背后,她没想到,夏炽陌竟然为她做过这么多事,而她却一无所知,震惊可想而知。
水轻灵最后道:“娘娘听完这些,还觉得王爷只是一时兴起贪念您的美色吗?”
宣瑾久久不能言语,原来夏炽陌口口声声说喜欢了她十年,竟是真的!只是她从未对夏炽陌做过些什么,夏炽陌对她的这份感情到底从何而来?
作者有话要说:作者姑娘是个颜控重症患者,总觉得喜欢一个人,总是从颜开始,感觉好肤浅,捂脸~——————对了,交代一下,本文的篇幅可能有点长,大概四十万字左右~另:谢谢姑娘们的霸王票,和所有留言支持本文的姑娘们
☆、第二十一章
夏炽陌带着夏瑜凛满载而归,就见宣瑾独自一人坐在溪边,那背影,夏炽陌再熟悉不过,单薄孤单,让人心疼。
夏瑜凛还处在极度兴奋之下,虽然没打到老虎,但是夏炽陌射了一头大野猪,还有很多山鸡兔子,夏炽陌例无虚发的射术,让夏瑜凛越发崇拜,当然最让夏瑜凛激动的还是夏炽陌抓了他的手,亲自射死一只獐子,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后,告诉母后他有多厉害,远远的看到宣瑾就要大叫,却被夏炽陌一把捂了嘴。
夏炽陌把夏瑜凛交给吟霜,让吟霜挑几只野味烤了,自己则走向宣瑾。
宣瑾听到后面有声音,没回头就已知来人是谁,淡淡道:“回来了,皇上可安好?”
夏炽陌走到她身侧坐下,还顺势搂了她,在她侧颊上亲了一口,然后假意埋怨道:“就知道关心你儿子,怎么不问问我好不好?”
宣瑾看了她一眼,夏炽陌还是那副举止轻佻的可恶模样,跟水轻灵口中描绘的痴情人半分不符,轻轻摇了一下头,又收回视线。
夏炽陌已习惯她的爱理不理,也不在意,道:“凛儿好的很,男孩子就该流血流汗,你整日把他护得如此周全,对他半分好处没有。”
宣瑾如何不知这个道理,只是在这宫里锋芒太露可不是什么好事,她倒是好奇夏炽陌的态度,如此教导凛儿,就不怕有一天凛儿翅膀硬了,凌驾于他?跟夏炽陌这种聪明人说话,无需绕弯子,便直言不讳道:“你不怕养虎为患?”
夏炽陌不答反问:“如果有一天你儿子要杀我,你会怎么办?”
这么问,就是已料到会有那样的一天,那为何还如此做?宣瑾越发猜不透此人,很想冷酷无情的说袖手旁观,只是她真能做到袖手旁观吗?摇头道:“我不知道。”
夏炽陌有些心伤,不死心的问:“连一句求情的话都不会说?”
宣瑾道:“只怕到时凛儿未必肯听我的话。”
夏炽陌笑:“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为什么?”宣瑾不解,“你明明可以不这么做。”她自然不希望凛儿成为一个平庸无能的皇帝,只是凛儿想专政,就必须扫清一切阻碍,而夏炽陌就是他最大的障碍,自古无情帝王家,父子尚且相残,何况叔侄,就算夏炽陌曾有拥护之功,又有教导之恩,都敌不过大权在握的诱惑,除非夏炽陌心甘情愿将大权拱手相让,否则必定兵戎相见,只是这么多年的心血付诸流水,夏炽陌会舍得?
“因为他是你儿子。”夏炽陌说完就站了起来,舒展开双臂,问宣瑾,“喜欢这里吗?”
宣瑾正琢磨着夏炽陌前一句话的深意,随意应了一声:“嗯。”
“等凛儿大了,天下定了,你我隐居这里可好?”
宣瑾还要点头,突然会意过来,她自是愿意,只是和夏炽陌一起,不免扫了兴致,再想到她是太后,怎么可能还有出宫的机会,归隐田园不过是痴梦一场罢了,就不置可否的笑了笑。
夏炽陌见她没否认,就权当她答应了,然后开始憧憬:“要在这里定居,先要建一个庄园,里面挖个荷花塘,这样夏天可以摘莲子,秋天可以采莲藕,还要建一个花园,长些奇花异草,种一片竹林,养一些奇珍异兽,再从宫中要几个御医和御厨……”
宣瑾实在忍不住,打断了她的滔滔不绝:“这还叫隐居?你干脆把你的景王府搬过来算了。”果然是锦衣玉食惯了的主。
没想到夏炽陌甚是认可,击掌道:“这倒是个好主意!”
一行人又逗留了小半日才原路返回,徐升急得望眼欲穿,可算把他们给盼回来了,朝中大臣倒是好应付,容太妃差点没要了他的老命,若不是景王留了块令牌给他,恐怕容太妃能直闯太后营帐。
宣瑾用了晚膳,让吟雪去传容盈月。
容盈月刚踏进门就寒暄:“妹妹的身子好些了没?”手上还托了碗参汤,倒是一副探病模样。
宣瑾让她坐了,淡淡道:“有劳太妃挂怀,哀家已无大碍。”
容盈月一口一个妹妹好不亲热,偏偏宣瑾直呼她太妃,拉开她们的距离,容盈月怎能不识相,改口笑道:“那臣妾就放心了。”再见宣瑾脸色红润,哪有半分病象,又道,“这碗参汤是臣妾亲自熬的,是臣妾的一片心意,还望娘娘不要嫌弃才好。”
“太妃有心了。”宣瑾让吟霜接了,问,“哀家听徐公公说,太妃急着找哀家,不知有何要事?”
容盈月哪有什么要事,皇上太后景王同时病倒不见人,徐升还拦着不让探病,实在太过蹊跷,她才想一探究竟,现在宣瑾问起,自然早想好缘由,先是面露难色,然后才颇为不好意思的道:“这事原想回宫再跟娘娘说,又怕娘娘政务繁忙,顾不上臣妾这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所以才乘着在外的机会,先跟娘娘说了。”
宣瑾蛮以为她急着见自己是瞧热闹,没想到还真有事求,便道:“太妃但说无妨。”
容盈月这才道:“臣妾的娘家离这里只有三十里地,家里除了年迈的双亲,还有一个胞妹,已到了出嫁年纪,臣妾的父亲书信给臣妾,希望臣妾能给妹妹说户好人家,臣妾就想把妹妹接来,随臣妾一道进京,再帮她在京城随便挑户人家嫁了,也算是了了老父的心愿。”
宣瑾听出她的意思,容盈月是想把她的亲妹妹接过来,这原是小事一桩,但是偏偏这时候说出来,宣瑾不由得多了一个心,何况先前她才跟自己的兄长说了一回亲,想让琉璃跟高珩结亲,目的自然是为了拉拢高珩,而容盈月看似无意的举动,似乎并没那么简单,容盈月凭着姿色和手段能受宠这些年,她一母同胞的妹妹恐怕也不是省油的灯,既然容盈月已提了出来,这么小的事,也不好拒绝,只放心里防着就好,宣瑾便应了。
容盈月喜道:“多谢娘娘,臣妾这就让人去接。”
天色已晚,容盈月这么迫不及待的去接人,更显得不同寻常,宣瑾思索了一下,突然想到一个可能,若是容盈月的妹妹真跟容盈月一样,学得一身媚术,勾引一个人,倒是很合适。
打发了容盈月,宣瑾怕夏炽陌来扰她,也不急着安置,让吟雪拿来笔墨纸砚,把白天看到的景色,凭着记忆尽数落在纸上,画好后,盯着出神,想起夏炽陌的话,若真能在这样的地方隐居,确实是件美事。
夏炽陌进来时,一眼就见到了这副山水图,美则美矣,却觉得少了什么,随即就想起,她的画功亦不弱,也不经宣瑾同意,就拿起桌上的笔,寥寥几笔,勾勒出两个人形,虽然只是背影,但是不用猜都知道她画得是谁。
夏炽陌搁下笔,满意的点头:“这还差不多。”
宣瑾却道:“吟霜,把这幅画扔了吧。”
吟霜就要上前,夏炽陌连忙先一步把画卷了,放进怀中,嗔怪道:“瑾儿真是多心,一幅画而已。”
宣瑾只好作罢,陪着夏炽陌闲坐着。
夏炽陌只要看着宣瑾就心满意足,哪怕宣瑾对她爱理不理,她也高兴,一直逗留了很晚才回去。
第二天正式上山祭宗庙,礼仪繁琐,直到天黑才算结束,这才进行了一部分,还要祭两天才算结束。
小皇帝听了夏炽陌的话,只第一天哭恼了一回,就没再缠着宣瑾,倒是夏炽陌,白天还对着夏家列祖列宗说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晚上就以小叔的身份在大嫂房中厮混,丝毫不知避讳,群臣都敢怒不敢言,就连夏炽陌的亲信在私下都颇有微词,指责夏炽陌有失大体。
容盈月斜靠在榻上冷哼:“偷偷摸摸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