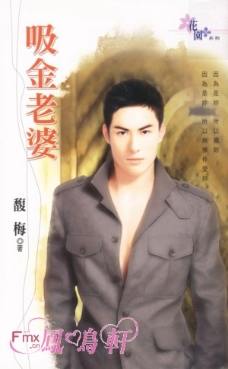第二次呼吸-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电子书】…立志要做最新最全的txt文本格式电子书下载站!
Dixi et animam meam servavi。( 我的灵魂因呼唤他的名字而得到救赎。)
——冯象《木腿正义》
那天钟垣提醒我说,白椴要回来了。
我有点儿愣。
我太怕失去他,所以写下这篇文字。
为见证他在我生命中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并希望这不是一个结束。
内容标签:青梅竹马 三教九流 黑帮情仇
搜索关键字:主角:夏念非,白椴 ┃ 配角:钟垣,张源,郭一臣 ┃ 其它:医生,黑帮
第一部
序
凌晨六点半,我终于交完班,把一个刚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病人交到外科副主任手上。交班时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的形象异常蹉跎与猥琐;我们副主任仿佛是害怕我继续呆在医院污染环境一般,真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夏你快点回去休息吧,看你这兔子眼红的。
我弱柳扶风般地拐回医师休息室,中途出卖色相向一个不认识但有些面熟的护士妹妹要了份病号早餐;然后我在休息室里找了个角落蹲下,准备缓一缓之后再回家。我拿起牛奶正要喝,休息室的门突然从外面被打开,脑外的钟垣探头探脑地溜了进来。
我一怔,机械地点了点头:“钟老师早,你值班?”
钟垣点点头,随性在我身边坐下,问也没问一声,直接抓起我饭盒里的馒头往嘴里塞。我明显嫌恶地看他一眼,他咧嘴一笑:“咱俩谁跟谁啊,对不?”
我哼了声,懒得理他,兀自慢慢地喝着我的牛奶。这两年我总是极力避免于这个男人单独相处,这样沉默而缓慢的气氛往往让我想起一些飘渺的过往,想起那些惆怅的人和事,在当初是怎样刻骨铭心地放在我的眉间心上。
而钟垣却好像完全没有那种伤感。他大口大口地吃完我的馒头以后,突然一个抬头,直直看向我:“听说了么,说是白椴他们那批出国的下个月就要回来了。”
我右手不自觉地一抖。
钟垣喜笑颜开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他一回来准是你们科的顶梁柱,你得加把劲啊。”我还来不及反应,钟垣的手机就惊雷一般响了起来,估计又是急诊。他骂骂咧咧地迈出门去,临走时回头一笑:“念非,谢谢你的馒头哈,一会儿我就靠那个得撑仨小时。”
“你饿死在手术台上正好。”我白他一眼,目送他委委屈屈地喃喃而去;我抬眼看向窗外,黎明正在这个死寂的冬日悄悄降临。他就要回来了,我默默对自己说道。
1 石棚巷筒子楼
我的母亲夏薇薇在17岁时就生了我,并且自作主张地给我取了个文艺无比的名字——夏念非。八几年是个民风还比较保守,但凡有男女青年当众拥抱就会被视为异类的奇异年代。我妈年轻时漂亮得宛若天仙,她16岁早恋,据说被一个小白脸搞大了肚子,怀我怀到快五个月时才被家里人发现,我爷爷抡着笤帚险些把我妈的腿打断。我妈发疯似地护着我,哭了一场,当天晚上偷偷从家里拿了几百块钱,给老家留了张大义凛然的便条,带着几件单衣就出逃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很好奇,我妈从老夏家出逃的那个夜晚我的亲生父亲到底在什么地方。在我生命的头十几年里,我的生父对我来说一直是个极度透明的存在,我那无所不能的妈妈甚至曾经试图让我相信我是她一个人从肚子里捣鼓出来的。生我的那年初春我妈挺着大肚子在南方一个叫凫州的城市里帮别人洗了半年多的盘子,再后来,我就在她生活最为窘迫的时候出生了。虽然对那时候的事我完全没有记忆,但我妈每每跟我提起那段峥嵘岁月却总会落泪,觉得亏待了我。我在出生的前几年里几乎没在自己的床上睡过一晚上的觉,所幸我生来便身体健壮,没灾没病,整天吃稀饭馒头也能长得白白胖胖;后来我妈一想到这茬就会说,我们家念非命贱得很,真是白白浪费了这么个好名字。
我妈刚到凫州的时候带着我住在城南石棚巷一个有着二十多年历史的破筒子楼里,天井在楼中央,从下往上看时天空里花花绿绿的全是各家人换洗的衣服裤衩;楼里每层都是五六家人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洗澡得自己去提水,一二三四排着来。当时我们楼里有七八个差不多大的小毛孩,每天幼儿园一放学就挽起袖子打水仗,玩到六点一起挤在小卖铺里软磨硬泡地让老板娘给我们放凫州少儿台的唐老鸭。我们那群孩子的小头目是张源,还有个跟班叫郭一臣,事到如今我已经快忘记张源当年长什么样子。只记得这小子从小就一副人人欠他二万五的表情,在一群野孩子中的领袖地位坚不可摧。
张源他们家跟我们家住对门,平日里我们母子两挺受他们家照顾。张源的爸妈都算得上是奇人。张源他妈是个纺织工人,嗓门洪亮,膀大腰圆,一口气可以把煤气罐从一楼扛到四楼,是远近闻名的母夜叉。相反张源他爸倒是斯斯文文的,人长得温文,说话也轻柔,一双手又白又长,在家从来不干重活,站在张源妈身边反倒有一股子小鸟依人的风情。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几乎不和楼里其他住户讲话,就是跟张源他爸妈能说几句。有一次我一大早起来出门上厕所,路过我们家晒衣服的栏杆时闻到老大一股骚味儿,转头一看,我妈晒的衣服上居然粘粘嗒嗒地不知被谁泼了屎尿。我义愤填膺地把我妈叫起来看,谁知道我妈一来就哭上了。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张源他妈出来了,见了这情景赶紧把我妈牵住,然后自己倚着天井栏杆不知道骂谁,声震全楼。我对这一事件的记忆实在太过模糊,现在想来那时候似乎真的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而我对此却全无感知,一直到后来我认识白椴。
我和白椴严格地说来应该是青梅竹马,可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最初一段记忆却确实称不上美好。
作为军区大院的高干子弟,白椴似乎生来就与我的生活格格不入。白椴小时候住在离我们筒子楼半条街远的家属院里,家门口有卫兵走来走去,气派非常,与我们歪歪斜斜的筒子楼有着鲜明的对比。白椴和张源一样比我稍大几岁,我认识他时他已经上小学了,而且是军区大院里那一帮小屁孩的头儿。记忆中白椴总是穿着天蓝色的长袖小外套,双手拢着大黄蜂袖套,脚上是铮亮的小黑皮鞋,手里还老拿着糖,一副富家子弟的派头,十分引人注目。白椴从小就漂亮得没天理,头发跟眼睛都是亮闪闪的,鼻子又直又挺,两片嘴唇薄薄的笑起来十分好看。只不过我那时候不太懂得欣赏他的美貌,吸引我的总会是他手上稀奇古怪的零食,还有我们那个年代很稀罕的变形金刚。
那时候跟在白椴身边的小孩子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大概就是刘肇青,沈伟和董希他们几个。出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们军区大院的小孩跟我们筒子楼的小孩从来都看对方不顺眼,打架斗殴的事情没少干过,到了白椴跟张源这一代更是登峰造极。有阵子我们筒子楼帮除了打水仗以外最大的乐趣就是往军区大院里扔水袋或者扔石子儿,有时候还撒了尿装塑料袋里往里扔,也不管是不是扔在那帮孩子的地盘上,只要听到有人中了招开始骂就得意洋洋地一哄而散。那时候白椴他们的手段也挺低级,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用硬币往锡箔纸上印出花样,再把锡箔纸折成钢镚儿的样子扔在地上。我们这帮穷孩子每每看到这些假钢镚儿都会上当去捡,而这时候大院那几个孩子就会欢天喜地地拍着手从路边上蹦出来看我们的笑话。这时候我们一般会恼羞成怒地扭在一起打,起先还是小啰啰闹事,打得凶了就会惊动到两边的老大亲自出场。我记得那时候张源跟白椴两人每次出场都整得跟黑社会似的,张源的脑袋总是歪向一边,开打之前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扯红领巾的动作,让我们这些没红领巾可戴的孩子羡慕得不得了;而白椴小时候漂亮归漂亮,打起架来也贼狠,还兴舞枪弄棍的,从他爸那儿弄来个日本军刀刀鞘当武器,有一次愣举着刀鞘追张源追了两条街。
筒子楼和军区大院两大孩子帮的关系降至冰点是在我五岁半的时候。那年夏天我们两帮孩子挺有一阵儿没闹事了,有一回大伙一起扛着游泳圈跟着张源去游泳,走到半截的时候碰上白椴也带着刘肇青他们几个往游泳池走。张源跟白椴对上眼时两人不约而同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们两帮孩子也就跟着彼此“哼”了一声,一路别别扭扭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去了。
买了票进了游泳池,我们几个把游泳圈往池子边上一堆就先进更衣室里换裤衩去了。我当时也没留神白椴那群人在干什么,从更衣室里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我的游泳圈没了,张源他们几个的游泳圈都还好好地堆在池子边上,唯独我那个印着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充气圈不见了。我当时就没有了游泳的兴致,哭兮兮地让张源帮我找游泳圈。张源一听二话不说就跳进池子里找白椴,气势汹汹的:“白椴!你把夏念非的游泳圈藏哪儿去了?”
白椴泡在水里爱理不理:“说什么呢,谁爱藏你们的游泳圈啊?”
“我们的游泳圈,刚刚还放在池子边上呢,一转眼就没了,除了你们还会有谁?”张源不依不饶。
“不知道!”白椴往边上挪了挪,打起一阵水花,“自己的东西自己不看好,丢了还赖别人?”说完还特别附送一大白眼。
“真的不是你拿的?”张源有点将信将疑。正在这时候,我们这边的郭一臣眼尖看到了刘肇青他们,当下就吼出来:“刘胖子!你们干吗呢你们!”
我一回头,正见着刘肇青和沈伟躲在更衣室后边起劲儿地踩着我的游泳圈,边踩还边笑,本来鼓鼓的充气圈子被这两人糟蹋得只剩一层皮;游泳圈上的花纹也不好看了,白雪公主的脸早就变了形。我当时一股热血上窜,蹭蹭从池子里爬起来,冲到比我高一个头的刘肇青面前,使劲一推:“干什么呢你!凭什么踩我游泳圈?!”
刘肇青被我推得后退了一下,马上又横过来:“我就是要踩,怎么地?”
我看了眼地上的游泳圈,抡胳膊就往刘肇青脸上揍。我那时候太小,手上也没劲,其实根本没把他怎么着,但这个动作无疑是个开战的信号,使得郭一臣带着这边所有的孩子一下子都围过来了。张源和白椴当时还泡在水里,一看架势不对也跟着爬上来了。这两人挤过来的时候正赶上我被在体能上有压倒性优势的刘肇青按在地上使劲打,然后筒子楼小分队的几个先锋扑在刘肇青身上抓的抓咬的咬——总之,我被压在一堆人的最底层完全不能反抗,全身最活泛的也就是嘴。我当时骂了刘肇青些什么我也记不清,不过碍于年龄的原因,估计也恶毒不到哪儿去;但那些话却足以激怒刘肇青,我记得他一边甩开身上的几只胳膊一边揍我的脸:“得意个啥,你还不就是一野种!”
2 离开
2
刘肇青这话一放出来,我很敏锐的察觉到郭一臣他们的行动一下子就停了下来。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所谓“野种”是个什么概念,心里估摸着大概就是个骂人的话,于是我不甘示弱地朝他吐口水:“去你妈!你才是个野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