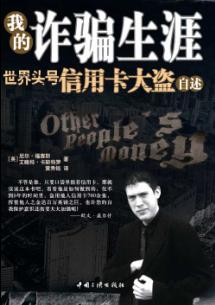法医生涯四十年-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德·埃文思,于午夜零时五分,从她的营房出来,准备到通信室值夜班。以后看见她活着的唯一的人就是杀死她的凶手。
她参加了美国兵营的一次舞会,后来和一个朋友玛格丽特·琼斯下士一起回营房。那晚很黑。“要我送你到办公室吗?”琼斯提议。“不必啦,谢谢!”很可能这就是她活着时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琼斯下士进入妇女盥洗盟间开了灯。有一个穿着皇家空军制服的男人在里头。当格林诺誓长问她时,她回忆当时的对话很清楚:
“你在这里干什么7”
“我迷路了。这是一号基地吗?”
“不,这是妇女辅助空军基地。出去!”
“你能给我带路吗?我喝了酒,看不见路。”他蹒跚地站起来,又倒在门边。
她带他出去,并指路给他。
“我能谢谢你吗?”他开始向她走过来。
“不,走你的路!”
这就是威妮弗雷德·埃文思换上西装裤后上夜班要走的路。一号基地离这里不够一英里远。
格林诺将调查集中在一号基地。很快他就听说有人看见一个空军士兵在凌晨1点多钟摄手摄脚地在黑暗中上床。早上5点30分他就起床,将他的军衣擦干净并且熨平,还刮掉鞋上的泥巴。这时间做这种不寻常的活动足以引起注意。
他原是伦敦体育运动俱乐部的阿瑟·海斯,37岁,已婚,有一个小家庭。他立即被安排到辨认行列中去。他不知道琼斯下士正在辨认着这个行列的人员。
“就是他!”她毫不犹豫地说。
当格林诺询问海斯时,他承认在妇女辅助空军队盥洗间和琼斯下土偶然碰见过。但没有承认别的事情,并说他那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间不到12点半。一个象他那样喝醉酒的人,走一英里路是要花20分钟的时间。
格林诺注意到他手上有一些刮痕,可能被荆棘刮破的。他的鞋上仍有泥巴。格林诺将鞋子带来给我。我发现和泥巴混在的还有砖粉。在那条发生凶杀案的沟里也有碎砖和砖粉。
格林诺还将海斯的皇家空军军衣和长裤带给我。两件服装看起来好象新近用海绵揩拭过和刷过。长裤明显被熨过。尽管这样,两个袖口还是有泥斑,军衣和长裤上有许多淡红色和棕色斑痕,作人血的确诊试验结果阳性,不幸的是浸出液未能测知血型。
我在海斯的衣服上还发现10根头发,其中4根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而与被害人埃文思的头发相同。海斯的衣刷上有一根头发也是这样。我警告格林诺说这些科学证据还远远不能下结论,还警告他不要太依赖泥土和砖粉的证据。“这些证据太一般”。
但格林诺认为他掌握了事实,而且检察官也同意。海斯似乎有点诧异。
当格林诺逮捕海斯时,他眼看着地板坐了四、五分钟。然后他说:“我在想我能否看看你们把我和这个案子联系起来的证据。你不能告诉我吗?”
“不,”格林诺说,“现在不能。”
在贝克里斯的单人牢房里,有人听见海斯在自言自语:“我不知道他们得到什么线索?他们肯定有了一些。”然后对一个守卫说:“警长从我的头上取走了6根头发。如果其中的任何一根在她的衣服上发现,我将如何证明不是他将它放在她的衣服上呢?”如果有什么证据指控他的话,“那就是警察捏造出来的。”
这个案子正好相反。根本就不是警察将海斯的毛发移放到被杀死的姑娘衣服上,而是格林诺去到芝喀什尔郡海斯的家里,从他老婆那里收集到的。经过检查我发现这些毛发与威妮弗雷德·埃文思尸体上取得的完全一致。当然,当无助于该案的处理而抛弃毛发证据时,检察长会根据通常的程序将理由告知被告。
在审判之前,海斯的指挥官收到一封匿名信:“能否请你将这封信交给飞行员的律师吗?该飞行员是被错误地指控谋杀了威妮弗雷德·埃文思。我要说是我杀死那个姑娘。我和她约定半夜在那条路——即你们发现她的尸体的那条路—一下会面。我到时还不见她。等了一段时间,我决定到空军妇女辅助队基地去。在我刚到时,我就听见有声音。我紧靠篱巴站着。听到有脚步声,是个飞行员。我想他没有看见我。然后又看见我认识的威妮弗雷德·埃文思。她说我不应该到这里来找她。一个妇女辅助空军队员朋友曾提议和她一起走,因为走在前面的飞行员酒醉迷路……”
写这封信的人为什么会知道海斯酒醉迷路呢?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一点:玛格丽特·琼斯下士和伦敦体育运动俱乐部的阿瑟·海斯——在监狱中等候受审的人。
这封信是用黑体大写字母写的。警长切里尔没有发现上面有指纹,但他报告说,字迹和从海斯衣物的一个修补标签上的字迹“相符”。尽管发出这封信时海斯已在诺利芝城监狱,但并没有妨碍它作为指控海斯的另一个证据的价值。这个证据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有力的。
1945年1月举行的审判,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日子。曾经在盖氏医院工作的我的老朋友埃利克·比德尔在审判刚开始时因一次交通事故丧命。我在等待出庭作证时,法庭宣读了他的死亡证明书。我发觉要使我冷静地专心作证是非常困难的。
这场审判对于海斯来说,无疑更糟糕,他被处绞刑。
在我们到贝克莱斯后一个月左右,从一辆路过的车上抛出—个垂死的人,差不多掷到我们头上。他是被车撞倒后给卡车拖走的,后来才知道汽车是笔直地朝他开去,作为谋杀的手段。
受害者是一个退休的海军船长,56岁,名叫拉尔夫·贝尼。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事情走过伦敦商业区。突然有个青年从一部汽车里跳出来,用一把斧头砸烂一间珠宝商店的窗户,抢走了一盘戒指和珍珠项圈后,又跳进车里,立即开车走了。这时是午餐时分,街道上很热闹。有几个大胆的人试图拦住车子,但驾车者加大油门行驶,他们只好跑开。贝尼船长是很勇敢的,但也几乎是愚笨的。他跳到路中间,伸开双臂,想阻住汽车,但驾车者笔直地向他开来。贝尼被撞倒,车轮子从他的胸部碾过去,使他躺在路上动弹不得。人们还来不及去救他,驾车者因为看见前面的路不通,就往后倒开,快速倒开几米远,再一次从贝尼船长身上碾过去。当调转车头往前开时,车子钩住了贝尼的衣服而被拖走了。
另一部汽车沿着朗伯大街追过去,追到伦敦大桥。“救命啦!救命啦!”被拖着不断碰撞地面的船长大声呼叫。过了大桥,拐了个弯来到图里大街靠近火车终点站。经过这样可怕地被拖了一英里多路后,贝尼船长被抛到路边石栏上。几分钟后他被送到盖氏医院,几小时内,他就死了。车轮碾过时,使他的肋骨骨折,双肺被挤压并被折断的肋骨刺穿。由于拖拉和撞击地面,周身都有伤。
汽车开跑了,后来被抛弃在爱尔兰政厅附近。伦敦商业区警察很快就追查到驾车者和打碎橱窗的抢劫犯。两个人都是伦敦南区被称为“象孩子”罪犯集团的成员。驾车人罗纳德·赫德利26岁,被判为杀死只尼船长的凶手,处以绞刑。他的同伙汤玛斯·詹金斯判处监禁8年。
汤玛斯的弟弟查理斯·詹金斯两年后参加了抢劫夏洛特大街一间珠宝商店的行动。当他和两个同伙正在逃跑时,一个骑摩托车的具有贝尼船长那种公共道德的人,阿历克·安弟奎斯试图拦住他们。尽管他费尽力气还是被他们开枪打死。致命的一枪是由克里斯托弗·杰拉史蒂开的。但查理斯·詹金斯也握住一支上了子弹的枪,两人都被判处绞刑。以后,人们就制造了一枚贝尼奖章,专门奖给勇敢的人,以此来纪念那位勇猛无畏的海军英雄。
在这摩托车凶杀案后几个月,我受理了一件奇怪的自行车“强奸”案。
一天黄昏,我被叫去检查一具女尸,死者年龄约55岁,被发现死在赫弗特夏边界上一条乡村沟渠里。她穿的大衣和女上衣卷到腰背部,扎口短裤拉了下来,但没有拉脱。她的阴户撕裂,两侧都有挫伤。面部受到严重的挤压伤。
警察一发现这具尸体,就考虑这是强奸杀人案。但综合看来并不是真正的强奸案。衣服没有撕破,没有搏斗征象,没有性交证据,没有勒扼或其他伤痕。生殖器的挤压伤是那么严重,我认为是比男性生殖器重得多的东西插入明户造成的。但是为什么她的大衣和上衣会被推向上,衬裤却被放下来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她是在酒店参加了一个集会后回家,谅必是在漆黑的路上蹲下来解小便。
我估计她大约死了20小时,也即前天晚上11点半钟。在死前不久喝了啤酒。路很荒凉,天是那么漆黑。当她蹲下来——或者我认为更可能是解完小便准备起身时——一辆自行车朝她冲过来,前轮插进了她的阴户,手把或车灯撞到她的脸。她的脑部受了挫伤,这证明使脸部损伤的暴力必定很大,而且可能将她撞昏。后头部较小的损伤可因撞到时仰面朝天倒下去所致。血液流进喉头。她被拖到草地边后逐渐衰竭死亡。
刑事侦案局的调查证实了这一推论。查到了骑自行车者,是一个16岁的青年。这个悲剧发生后他惊慌失措地离开这个妇女。她不是死于头部损伤,而因吸进血液室息致死。
战争时期,我受理的最后一个案例是在扑茨茅斯港造船厂海潮中发观的无名男尸。死后在水中浸泡已有6至8周。显然他是溺死的。但双手却被绳子捆绑在身旁。“我们认为像是被杀的。”刑事侦察局的警察相当响亮地说,好象他们所说的是十分明显的事一样。
“照我看来不是。”我说我没有看见外表有损伤,也无绳子缠住脖子或扼勒痕。
“但是,他被捆成像是准备要烤的鸡一样。”负责该案的探长说。
我从绳子松开端逐渐追朔到起始端,一个绳套缠着两腿。每个绳结都向上拉紧。“我认为是他自己的手和牙齿打的结。”我说。用手电筒照亮死者的口腔,看见牙齿缝中卡着一小股绳子。
警察调查证实这是自杀。这个男人是个游泳能手,他想保证自杀成功,就这样做了。
(伍新尧 郭景元)
10。钻石织纹的鞭子
战争结束时,我原来的秘书,快乐年青的金发女郎莫利·李费伯里离开我,结婚了。她的继任者是25岁的珍妮·邓恩。她有吸引人的黄铜色头发,富于同情心,深爱我的事业。在我们结婚之前,她为我工作了10年。我的前妻一年前死于多发性硬化症,在我们结婚的那天,珍妮动人地微笑着讲,“最初的十年是最坏的。”而这是真的。她成了我配合得异常好的伙伴。我们两人以后共同工作了20年,直到她后来在50多岁时因患癌症而不幸早死。
由于这两位姑娘,使我工作有了一个特点,我从来没有为哪个案件的准备和出庭感到焦虑。我知道:我的“现场记录”,到达和离开现场的时间,伦敦警察所的医生、警察官员和科学实验室人员的名单,我作报告的确切措辞、绘图、照相、标本——在我步入法庭时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准备得井井有条。在那些年代,她们俩虽然年轻,但都十分关注我不被律师所驳倒。在那么不寻常的时间,在极端不方便的工作条件(常常在很脏或使人感到厌恶的地方)下同我一起工作。有一次,我们处理一件凶杀案,珍妮还同我在一个男公厕里呆了一个多小时。我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