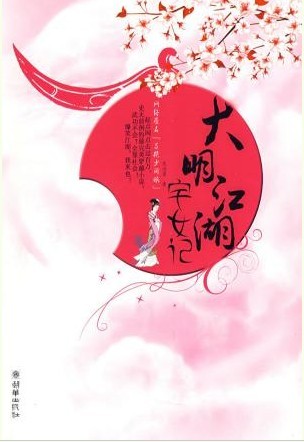深海夜未眠-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乐铖白很友善地与一众马屁党交流着:“我在医院时也天天想着你们。”
“真好,你回来了,年底还有一场比赛,正赶得上训练。”
“那就一起加油吧。”他喝了一口瓶中的水,漫不经心地应和着,神情看上去显然有些焦躁。那人察言观色:“乐副队,你是不是在等什么人?”
也不知这一句话是怎么触到了乐铖白的痛处,他竟然收起了先前的笑容,冷淡地把水随手抛到一边:“开场吧。”
许合子没料到他们的中场休息这样短暂,一时站在草坪外几十米远的地方,犹豫着要不要上前打断。
还是等下一场休息吧,许合子想。无论如何,要她在大庭广众下和乐铖白这种人开口说话,在旁人眼里,最终都会演变为一场有嫌疑的告白。然而没等许合子找个地方好好坐下,棒球场上跑过的一个男生忽然在乐铖白身后“咦”了一声:“乐副队,那不是那天和我们一起去医院的女孩吗?”
“是她,她叫什么来着……许合子?”另一个队员也看到了。
乐铖白正挥动棒球的手一僵,生生地扭过姿势往草坪上瞥了一眼。还真是她!
“喂,许合……”他想叫她往边上坐一些,这里已经是危险区。然而,乐铖白显然忘记了自己手上也正挥着一只棒球……
额角的剧痛让视野忽然变得一片黑暗,被白球衫的少年一球击来时,许合子似乎听见了他在叫着自己的名字。
疼,真是疼啊……她忍不住轻轻地嘶一声,倒吸一口凉气。
许合子整个人向前扑去。扑倒前似乎有人飞快地朝她奔来,雪白的球鞋踩在枯黄的草坪上,簌簌作响。
“许合子!许合子!”有人拍着她的脸。
许合子觉得自己像在拍武侠剧,深仇刻骨,一朝报复,她被他一球击中,正是江湖中所谓的“恩怨两清”。
也许是想到这个令人感到稍稍欣慰,许合子在完全失去意识前长长地松了口气;“我们……我们两清了?”
醒来时雨声潺潺。
许合子以为仍在梦中,睁开眼呆呆望了一眼天花板又闭了回去。
一直坐在病床前的乐铖白连忙捏了一把她的脸:“喂,醒了别装死。”
好疼!许合子再次睁开眼。这次,一张大脸无限靠近地映入眼帘。
“许合子,许合子。”他喊着她的名字。
许合子轻轻开口,有点迟疑:“乐铖白?”
“看来没被打傻。”他长舒一口气,看着她躺在病床上虚弱的模样,头上还绑着绷带,看上去多少有些楚楚可怜。转过脸,没有对上她的视线,他有些别扭地开口:“昨天……对不起了。”
昨天?她又吃了一惊,原来自己已经躺了一整天。
那许简珍呢?这些天许简珍都会回家,夜里打开门,没发现摆在桌上的饭菜,一定会生气。她有些不安地想要坐起身,却被乐铖白立刻制止住:“你想做什么?”
“我……我想上个厕所。”话到嘴边,她改口。
他的脸“腾”一下红了起来,似乎这是十分尴尬的话题,按住她肩膀的手却不肯放:“你等一等,我去给你找护工来。”
“没事。我是被砸了脑袋,又不是骨折。”她翻开被子就想下床,谁知他猛地扑了上来,两臂撑在病床上。
这回换成许合子结巴了:“你,你想做什么?”
出去倒热水的护工正好推门而进。
乐铖白立刻放开手,直起身子,看起来是要走出病房的样子。走了没几步,手托在门把上,却是微微一顿;“许合子,不管你相不相信,那一球……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她脸红着。
他“哦”了一声:“你知道?”
“既然这样——”他转回身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一字一顿:“就让你那个一脸穷酸相的妈妈,别老缠住我爸狮子大开口地要钱。”
几天后许合子和许简珍委婉地提起。她小心斟酌的口气如同在商量一件重要的大事,而那难堪却无法掩饰。
这几天,许简珍难得地尽了一个母亲的本分,连带着似乎脾气也好了不少。一边听着女儿许合子的话,一边不声不响地整理着手中的一束花。末了,才轻轻应一声:“知道了。”
许合子对她的这种态度感到担忧。
犹豫了一会儿,她小声地在许简珍的背后开口:“妈,其实那个乐铖白之前骨折住过院。”许简珍“哦”了一声。她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他那次骨折都是我害的。”
许简珍修剪着花枝的手终于停住:“怎么回事?”
许合子撇开了中间的许多细节,只说是自己冲地时不小心,又忘记了提醒他。许简珍听了,倒是很不以为然:“这事也能算到你头上?”
“反正……我们各一次,就算扯平吧。”她沮丧地劝阻着许简珍。而许简珍随手扔掉了小剪子,坐到了女儿的病床边,头一次心平气和地问了她一个问题。
“合子,在你心里,妈妈是个怎样的女人?”
许合子沉默着,没有说话。
许简珍倒是笑了一声,那笑声像是有点悲凉:“也是,虽然你是我一点点养大的。可是算起来,我们之间的交流并不多。”
这一刻的许简珍,眉间有难掩的疲态,就像全天下失败的母亲那样。
许合子仍然不吭声。
许简珍眼中的最后一点希望,就像快要燃尽的火苗那样,一点点地消逝,只余一片哀凄的冷灰。“连亲生女儿都没办法说是一个好女人……真是活得像一个笑话。”
“妈——”许合子动了动嘴唇。
许简珍却仿佛被刺激一般,从床边跳了起来;“钱!钱!钱!你们一个个都说我往钱眼里钻,连我亲生女儿也嫌弃我爱钱,丢了她的脸!你知道把一个孩子带大有多困难吗!吃饭、看病、租房,哪样不要钱?就连你现在住在医院,睡在这间病房,躺在这张床上,每分每秒也要花销!要是那姓乐的不赔钱,我一分钟也没能力支撑你再住下去,我就得把你背回家……许合子,我许简珍凭良心没有对不起你。”
那画着精致妆容,穿着得体衣裙的女人像是忽然发了疯,如同一个泼妇般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彻底崩溃了。
许合子忽然感到一阵深深的悲哀。
发泄过后,许简珍转身进入了卫生间拧开水龙头。
十四岁的许合子躺在病床上,听着哗哗的水声,意识到,人生是一个多么苍白而巨大的词汇。在这两个字面前,是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路,被时光夺取美貌的女人,渐渐明白了自尊是怎么一回事的小女孩,还有贫穷的命运……这一切,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通又无力的存在。
这次之后许合子再也没有在母亲许简珍面前提过类似的话,而许简珍和乐父到底是如何交流的,她也没有再追问过。
时间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流转着……
许合子额角的伤并不严重,住了几天的院后,很快地就回到了学校,投入紧张的期末复习中。
没有人注意到回校的许合子。
只有前座的于北北十分想念这个一向沉默少言却又守口如瓶的好朋友:“许合子,你总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会在医院继续住下去。”
许合子额角的伤并没有好全,仍缠着一小圈的绷带,看上去就像一个带伤上阵的伤兵。
乐铖白和一群狐朋狗友靠在走廊上高声谈笑时,那漫不经心的视线偶尔会投落在上厕所归来的许合子身上。她仍然像一只兔子似的,见了他就下意识地往外蹿半米远。
乐铖白就不明白了,挥球棒误伤了人的是他,没好气地一再嘲讽人的也是他,可她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只是避开了一切和他可能说话的场合。
那么,在这只“兔子”眼里,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依权仗势的有钱人家少爷,还是结群成党的学校混混头子?
年少的乐铖白忽然觉得十分的不爽。
化学竞赛的培训是在期末考之后开始。
因此,当期末考的最后一场铃声响起,周围人交了卷后开始一边收拾着书包一边大声谈笑时,许合子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为寒假的来临而激动。
最后一场考试是下午四点半结束,冬季天黑得早,还没到饭点,窗外已是暮云沉沉。有人看了一眼窗外压得很低的天色,“哧啦”一声推开窗:“这天看着像是要下雪。”
“不会吧?这可是今年第一场雪。”有女生立刻惊呼。
许合子正挨着那被半拉开的窗户坐着,缝隙中呼呼的北风涌进。这座城市的冬天干燥而洁净,就像画中的暮霭,带着一种无可救药的庄严。
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许合子把围巾往上拉了拉,围住了大半个脸,只露出一双乌黑的眼珠子,额头和耳朵又被绒帽和耳套遮住,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型的年画娃娃。
乐铖白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就拎起了那只单肩包,站到许合子桌前,高大的身影几乎挡住了原本就暗淡的夕光:“考试后去办公室集合,没忘记吧?”
许合子连忙点头。
乐铖白看上去还算满意的样子:“那就好。”顿了一顿,“我在走廊上等你。”
他今天穿了一身海军排扣风衣,卡其色靴子,唯一抢眼些的倒是一条浅色的羊绒围巾,花纹繁复看不出名堂。因为生得好看,走到哪里都十分惹眼。这让和他一路并肩而走的许合子感觉到压力巨大。
大约是两人从没走得这么近过,乐铖白也有一些尴尬,不动声色地遮掩住。
“许合子。”
“嗯?”
“帽子掉了。”他不动声色地说。
许合子回头一看,头上的绒帽不知什么时候被风吹得掉在了地上,怪不得忽然感觉头皮一冷呢。可是……奇怪,这人的眼睛不是一直看着前方的路吗?
办公室里蒋竺真似乎已等了很久,看到一快一慢走来的两人,波澜不惊的眼神从两人的脸上掠过,又淡淡地收了回去。
乐铖白看了她一眼,嗤笑了一声,不知是在笑什么。
平心而论,许合子对自己的同桌是十分崇拜和羡慕的,虽然她并不太和自己讲话。
这个无论肌肤还是性格都像冰雪一般的女孩身上,似乎始终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你很少能看见她在那些如云聚散的追求者身上浪费时间,即使对方表现出情比金坚的坚定。蒋竺真的时间,永远只会花在对未来的一步步谋划中。
从小练芭蕾磨平了脚尖,为了保持完美即使在零下的冬天也坚持穿裙子,因为太用功练琴而弄伤的手指……在许合子看来,蒋竺真完全是和自己活在不同世界的人。
这样的人,在宗教中往往被称为信徒。虔诚的信徒,为了自己的信仰,会从年少时开始积累积蓄,然后在生命中空出很长一段时间。从家中出发,三步一叩,五步一拜,直到抵达心中的圣城。沿途风刀霜剑,不过付诸淡淡一笑。可是蒋竺真又信仰着什么呢?”
化学老师见其他人也到齐了,开始和大家谈了谈寒假的安排和明年开春的竞赛。竞赛会在一所声名赫赫的高校中举行。
许合子完全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能进这所学府一睹风采,其他班中选出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