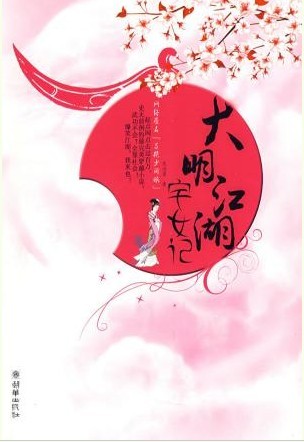深海夜未眠-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哦。”她的声音很淡,淡得仿佛是月光下的湖水,“大概是不想被人发现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或者下一秒你被人送进医院,而我却坐在审讯室接受笔录。因为不想那样的事发生,只好委屈你了,乐先生。”
这次,没等他提醒,她已经眼疾手快地扯下了他的领带,在他几乎虚脱的时刻从背后绑住他的双手。男人的体重压在了她瘦弱的身躯上,许合子咬着牙,一点点扳过他的肩,将他慢慢扶正。从始至终,乐铖白一声未吭,只是静静地望着她。
终于将他安置好,她累得顾不上喘气,额角沁出大颗的汗珠,顺势滑坐在了墙角:“借你的肩膀靠一靠。”
一直未说话的乐铖白淡淡开口:“好。”
她于是心安理得地将头倚在他的肩上。
一个面色苍白如鬼,一个气息不匀长发微乱,这时倘若有人推门进来,就会看见一对衣冠不整的男女。乐铖白的手被绑着,一动也不能动的时候,全身的触觉却格外灵敏起来。她的长发蹭到了他的下巴,轻轻的,柔柔的,让人心里有一些萌动。他于是艰难地转过头,静静地看了一眼倚靠着自己的女人。
她的面容很干净,没有妆迹,出了汗也只是稍显晕红。这等待的时间太难挨,大约因为无聊,她出着神,手指无意识地一遍遍抚平裙上的褶皱。
她在想着什么,在为着谁出神,那始终拧起的眉角为什么会这般柔和?
渐渐地,他的一颗心,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安静下来,静得像一汪湖泊。而许合子,是被漫不经心掷入湖底的一枚石子。
“阶有巨池,野藕已花。”
外头相邻的水库有水声拍石飞溅,山中寂静,无端地,许合子脑中突然跳出这一句话。
偏偏给他听到了:“什么?”
“阶有巨池,野藕已花。”她想了想,“是《聊斋》里的故事,宁采臣第一次见到聂小倩时的兰若寺。”
“哦,是那个被漂亮女人迷昏了头的穷书生吗,连是人是鬼也不分了,还想着过一辈子。”乐铖白轻蔑地笑了一声。
她倒是好脾气,丝毫没被他激怒,反而认真地问他一个问题:“如果,聂小倩永远不说出自己是鬼,宁采臣会如何?”
没等乐铖白回答,她自己就把话接了下去:“大概……会把她当作尘世中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吧,忍不住被她吸引,想要和她在一起。就像很多故事最后都会有的结局一样,相守到老。可是,她却从没告诉过他,自己身上最大的秘密。”
“这才是大多数人的爱情,乐先生。”她的笑容有一点苍白,“为什么要去要求被喜欢的那个人成为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她这样出现在他面前,已经是一个梦。就那样安安静静地把梦做下去,不好吗?”
“欺骗就是欺骗。”他冷淡地打断她,“一个女鬼用好皮相勾引了凡夫俗子,最后被识破面目,有什么值得可怜?”乐铖白眯起眼,目光清冷,“还是——要让那个蠢男人被骗一辈子?”
“我知道了。”她不知想起什么,却是一笑,“我在乐先生的眼里,一定是一个非常卑贱的女人,卑贱得像一颗尘埃,卑贱到没有说话的权力。”
“你——”乐铖白听出话中的讽刺。
大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钥匙转拧的轻响,惊动了房里的两人。
许合子回过神,想要跑出去看一看,却被他艰难地捉住脚踝:“把领带解开。”
“你……”她犹豫。
“已经没事了。”他的脸色苍白得吓人,微微喘了一口气,把话又重复了一遍,“领带……解开。”
“不行。”她冷静地拒绝,“我没法相信一个药物上瘾的人在发病时说的话。”
“许合子!”
“再等一等吧,我出去探一探风声。”她回头看了他一眼,开门而出。通廊正对着微掩的大门,开门的女人一仰头就见到了许合子。
余媚提着裙角飞快地跑上楼,皱眉看她一眼:“乐总呢?”顿了顿,“你怎么还在这里?”
许合子正要开口,一个声音却自她背后清冷地响起:“他们已经出去了。”
乐铖白!她难以置信地缓缓转过身,这人不知什么时候已挣开了绑住双手的领带,扶着墙慢慢走到了房外,甚至勉强将不小心松开了的衬衣扣子扣上了。
走廊上嵌着壁灯,大朵纯金丝线勾绘的花纹在地毯上洒下一片皎亮的光辉,与大厅中悬挂的巨大水晶吊灯遥相辉映。在这样的一片金碧中,他的眼角微翘,神色疏离,除却微微渗出汗的额角出卖了身体状况,全然看不出异常。
余媚与他们逆着光相对,看了一眼许合子,有些犹豫:“这位是……”
“你带错了人。”乐铖白毫不客气地打断,瞥了一眼站在一旁的许合子,“至于她是谁……我也不知道。”
余媚有些尴尬地朝她笑了一笑:“这可真是不好意思了。”
“不用,这位乐先生已经和我道过歉。”她索性把戏做足,“现在我能出去了吗?”
“等等。”一把挽住她胳膊的男人,分明是冷淡的脸色,眼底却仿佛涌动着暗潮,“还是和我们一起出去吧。”
“那好,我在前面给你们带路,小心些,但愿这空当没人过来。”
余媚说到做到,先行走在楼梯边,头也不回地叮嘱:“安保室被我临时切了电闸,可是山上有应急系统,最多两分钟。两分钟后一切监控都会恢复正常。”
许合子正在发怔,耳边忽然听到一声低语:“扶着我。”她抬眼朝他望去,对方始终是万年不变的冰瓷脸。
她反应过来:“步子虚,踩不住?”
他没有说话,似是默应。她只好从背后紧紧搭住他的手,又怕前头的余媚不知什么时候转过头,露了马脚。
“没力气走路,又是哪来的力气挣开手上捆的领带?”
“因为太简单。”
“嗯?”
“这么简单的活扣都打不开,难道是猪吗?”他惜字如金,脸上的嘲讽之色却无法掩饰。
许合子于是低下头,轻轻地说一句什么。
“什么?”乐铖白俯近,似乎想听清楚,却在一瞬间被她扣住手腕,险些掉下台阶。
“被人牵着走的,难道是猪吗?有手有脚却没办法站起来的,难道是猪吗?总是不停地在穷人面前炫耀金钱,却连一丝感情也不会有的——难道是猪吗?”她静静地看着他,“为什么活扣会这样简单,因为被绑的是猪嘛——乐先生。”
他一时难以置信地眯起眼。
前面的大门已应声打开,余媚站在门外的月光中:“乐总,快出来吧。”
她于是轻轻推了他一把,相触的指尖在一瞬分离,那被月亮一瞬照亮的皎洁的面容,迅速地隐退到了潮水般围扑的黑暗中。
“乐总。”灯光璀璨处有人走上前。
钟远山看了一眼自家老板始终漫不经心地敷衍着旁人的态度,顺着他时不时投向某处的视线望去,顿时明了于心,咳嗽一声,装作随意地开口:“哦,许小姐怎么还在这?”
乐铖白这才收回视线,冷淡地朝他扫了一眼。
钟远山决定献媚到底:“看样子,许小姐一定是在等她的朋友了。”
谁知乐铖白无动于衷,并没有热切地追问下去。于是钟远山硬着头皮说下去:“傍晚时她还是搭着我的车上来的。我们在跨海大桥上遇见,堵着车,许小姐一个人赤着脚走在路边,手里还拎着鞋,乍一看挺引人注目。我看见了她,就把她叫住,想问问她去哪。谁知一问才知道她也来这边,说是给参加酒会的朋友送一份文件。”
“这事你怎么没提过?”乐铖白低头品了一口红酒,漫不经心地问。
钟远山面有难色:“我的车刚停在门口,她就客客气气下了车,连多说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乐铖白不以为意地低哼一声,确实是这个女人的风格。
“不过——”钟远山望着站在一片浮动的金色光影中那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年轻女人,“酒会不知什么时候才散场,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她的朋友。从这里下去,如果一个人,也太危险了。夜里根本叫不到计程车。”
钟远山实在低估了许合子,他正说着,一直低头看表的女人,似乎打了个电话,然后很快地收起手机,朝着大门边走去。
“等等,她……她不是要从这里走下去吧?”
乐铖白似乎也怔了一怔,把红酒杯随手递给了一旁的助手:“我离开一会。”
“乐……乐铖白?”
一直向山下走着的许合子忽然被身后的汽车喇叭声吓了一跳,转过身,用手背遮住那刺目的光。谁知对方却把车缓缓地开过来,不偏不倚地停在了她身边。
“上车。”对方的口气一点儿也不温柔。
可许合子还是十分客气地退后一步:“不,不了。谢谢。”
也许是不胜酒力,也许夜里的风吹得格外温柔,他一向冷淡的眉宇间终于出现了危险的征兆:“我会吃了你吗?”
“不……”
“我看上去像拐卖女人的人贩?”
“不……”
“那么又是为什么,许合子?”
“我已经叫了出租车。”她的拒绝看上去十分虚弱,“就……就在山下等着。”
“我也只是顺路载你下山罢了。”他渐渐不耐烦起来。
许合子看了一眼路灯照耀下似乎永无尽头的山路,又看了一眼那好看的侧脸半隐半现在路灯阴影下的男人,终于硬着头皮打开车门坐了上去:“谢谢。”
夜风从半降下的窗口呼呼涌进,一直凝望着山下黑暗的乐铖白忽然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曾经认识吗?”
许合子猛然抬头看他。
“你看上去……似乎对我并不陌生的样子。”
她沉默。
他却忽然抿起唇角:“为什么总是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还是沉默。
而他仍旧未曾转头去看她的脸:“是刻意?还是无心?”
在他的一连串逼问中,山脚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然而等许合子发现时,乐铖白驾着车早已如离弦的箭一般开出老远。看样子他是存心没打算让她搭所谓的出租车。
距离他提出上一个问题已过去了许久,车渐渐上了跨海大桥,从海的这一头开往了另一头的城区,遥远的灯光衬得车内的他们仿佛浮世中颠簸的蝼蚁一般。
许合子终于艰涩地开口:“我们从不认识。我也没有想过要进入你的视线。”
“哦?”他似乎不以为然地笑了一笑,随手按下了播放键。
那盒被录成磁带在无数个兜风的深夜放了不知多少遍的录音,就这样响起在两人耳边。
“是。我们之间曾经深爱过,他爱着我,我爱着他。”
“后来有一天,两个人之中忽然有一人不再爱了。我离他而去,和别人在一起。他的心里却仍然惦记着我,每分每秒。”
许合子的眼睛忽然睁大,仿佛难以置信。她僵硬的背向后靠去,抓着衣角的手握得很紧。
那是自己的声音,千真万确。充满嘲讽,却又如此无力。
下一秒,他已脚踩刹车,捧住她躲闪的头,按住她颤抖的肩膀,狠狠地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