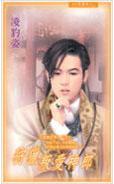续萧十一郎-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这句话才说完,已有十数条人影蝙蝠般一齐向那两个老人扑了过去,却正是那些父兄尊长被逍遥侯杀了的世家子弟。
这些少年人个个年少气盛,平日里就飞横跋扈,骄纵狂妄,没有人敢招惹,此刻心伤父兄尊长之死,报仇心切,一听是逍遥侯的人,就不顾一切扑了上去。
铁山大师忍不住闭上眼睛,惨然道:“完了……”
那两个老人本来走在沈璧君的前面,但忽然间就到了沈璧君的后面。
大家只看到那两个老人衣袂飘飞,手臂似乎挥了两下,那些世家子弟就一齐仰面倒了下去。
倒下去的时候,眉心已有一股夹杂着红色和白色的液体冲将出来。
没有人看清这两个老人是怎么杀了这些世家子弟的,但每个人都看见这些世家子弟已没有一个还是活的。
大家都吃惊地瞪着连城璧,仿佛连城璧脸上长了一朵喇叭花一样。
连城璧勉强笑道:“诸位前辈为什么这样看着在下?莫非在下说错了什么话了么?”
铁山大师道:“公子这是在说笑么?”
连城璧奇怪了起来,道:“说笑?大师以为在下这是在说笑?大师怎会以为在下是在说笑呢?”
铁山大师道:“公子明明知道这两位前辈不是逍遥侯的人,却为何还要这样说?平白送掉了十条性命?”
连城璧更奇怪,怔怔道:“这两位前辈不是逍遥侯的人?大师为什么认为这两位前辈不是逍遥侯的人?”
铁肩大师叹了口气,苦笑着道:“倘若这两位前辈是逍遥侯的人,就算是有十座无瑕山庄也早已被铲平了,哪里还有老衲等人的命在。”
枯木道长道:“莫说是十个无瑕山庄,就算是十个苏州城也早已被铲平了,那里还能保得住沈姑娘?”
连城璧陡然怔住,不由自主脱口道:“但在下两年前曾在逍遥侯的玩偶山庄见过这两位前辈……”
他这句话说到这里,突然闭上了嘴,目中忍不住掠过一丝惊慌之色。
铁山大师微笑道:“也许公子是看错了,这两位前辈也许是逍遥侯的师长也说不定。”
那些世家子弟死的时候,沈璧君突然停了下来,眼睛一直都在冷冷盯着连城璧,一直都想说话,此刻再也忍不住大声道:“他并没有看错,这两位前辈确实是玩偶山庄中人。”
唐大先生不动声色,故意问道:“这两位前辈神功盖世,倘若是玩偶山庄的人,为什么没有帮着逍遥侯将铁肩大师、枯木道长等杀死?为什么没有将姑娘劫走?”
沈璧君压抑住心中的激动,一字一字道:“因为各位大师前辈这一年来对付的根本就不是逍遥侯。逍遥侯早在两年前就已死了!小女子还曾亲手将他的人头刈了下来。”
唐大先生淡淡道:“那大家这一年来对付的是谁呢?”
沈璧君目光扫了连城璧一下,垂目道:“不知道。”
连城璧脸上就仿佛突然戴上了一个厚厚的木头面具,冷冷道:“你只有在有人撑腰的时候,才敢诋毁我么?……”
他这句话才说到这里,突然又闭上了嘴,目中忍不住又掠过一丝惊慌之色。
铁山大师微笑着道:“姑娘怎能这样诋毁连公子?连公子为了姑娘调动整个武林同道的力量,同逍遥侯明争暗斗足足数十次之多,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
铁肩大师望了铁山大师一眼,突然道:“敝师兄所言不错,老衲在这里跟逍遥侯打了数十次的仗,深谙逍遥侯的恶毒手段,像连公子这样的仁义君子,是万万做不出那种事来的。”
枯木道长望了铁肩大师一眼,也道:“连公子仁侠仗义,德行昭昭,人所共知,姑娘或许是弄错了。”
连城璧冷冷道:“这世上的恶毒女人多得很,虽然看起来很温良,很娴淑,但你还没有碰到她,她就开始像疯狗一样乱咬人。”
沈璧君冷冷看着连城璧,突然转过身走出了无瑕山庄。
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停步,再也没有回头。
只听铁山大师道:“阿弥陀佛……”
第十章 长亭
8
竹叶青盛在绿瓷杯里,看来就像是一大块透明的翡翠。
新月弯弯,就仿佛是风四娘的眉毛。
风四娘脸红红的,也不知是因为酒意,还是因为太过兴奋,太过激动。
她眼睛怔怔望着窗外蛾眉般的新月,怔怔地想着心事。
她白天已见过了沈璧君。
沈璧君虽然不肯让她陪着进无瑕山庄,但她却还是很担心沈璧君的安危,所以她就在无瑕山庄外的路口边等着。
沈璧君和那两个老人从无瑕山庄出来的时候,正巧被她撞上。
现在她非但已知道逍遥侯早在两年前就已死了,而且也已知道这两年搅得整个武林征战杀伐的人就是连城璧。
沈璧君能得到那两个老人的守护,她当然替沈璧君高兴。
但她真正兴奋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萧十一郎极有可能现在还没有死!
虽然沈璧君并没有亲口告诉她,但却已无异告诉了她。
因为沈璧君亲口告诉了她逍遥侯的死讯。
“逍遥侯早在两年前就已死在了他跟萧十一郎决斗的那片山崖下的沼泽中,他死的时候口里、眼里、鼻里、嘴里,全都塞满了烂泥臭水。我生怕他未死,还曾经将他的头一刀刈下来。奇Qīsuū。сom书他咽喉里、食道里也都是泥水,逍遥侯竟是被沼泽活活淹死的。”
沈璧君既然确切知道逍遥侯的生死,想必也该知道萧十一郎的生死。倘若萧十一郎真的已死了,沈璧君又岂能弃萧十一郎而独生?
这个推论虽然并不是最后的结论,但却绝对有道理。
那么,萧十一郎现在又在哪里呢?
夜已深沉,门外各种声音早已消寂。
远处传来零落的更鼓声,听来是那么单调,敲得风四娘心都乱了。
风四娘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转了几圈,只觉心情越来越烦,越来越乱,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她想睡觉,但她连一点睡意也没有。她想再喝几杯,可是已没有了那种心情。她刚想去掩起窗子……
晚风中突然飘来一阵歌声。歌声凄凉而又悲壮,听起来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陌生。
萧十一郎!
难道竟是萧十一郎?
除了萧十一郎自己,还有谁会唱萧十一郎这首曲子?
风四娘只觉心里一阵热意上涌,再也顾不得别的,手一按,人已箭一般蹿出窗外,向歌声传来的方向飞掠了过去。
长街静寂,一阵阵夜风卷起地上的纸片,旋转飞舞。
但整条长街却连半个人影都没有,连歌声都消失了,只听那单调的更鼓声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越来越隐约,越来越远。
风四娘怔怔站在街心,夜风从她身上掠过,从她脸上拂过,却吹不散她心中的沮丧和落寞。
“风四娘呀风四娘,萧十一郎早就死了,早就已死了,你居然还在做梦,还在自欺,你真是太可笑了。但萧十一郎真的已死了么?我明明听到了他的歌声,难道这只不过是幻觉么?”
她只觉疲倦极了,全身再也提不起劲来,只想回去再喝几杯,一觉睡到明天。明天也许什么事都没有改变。
一个人之所以不会永远被幻想迷惑,也许就因为永远有个“明天”。
看到她屋子窗内的灯光,她心里竟莫名其妙升起一个奇怪的想法。
“萧十一郎会不会就在屋子里,又躺在我的床上,用枕头盖住脸,将双脚高高地跷起,露出他鞋底上那两个大洞,却喝光了我酒樽里的竹叶青?”
她忍不住又觉得自己很好笑,这个时候居然还是不肯放弃幻想。
但她心中还是保留了一丝希冀。
萧十一郎也许真的就在这间屋子里。
风四娘只觉心跳加快,咽喉发干,费了很大的劲才将房子的门慢慢推开,眼睛不由自主向床上望去。
她脸上不由自主露出失望之色,心也渐渐地沉了下去。
她床上空荡荡的,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这屋子里显然并没有人来过。
原来这一切只不过是风四娘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风四娘苦笑着,慢慢走进屋子里,走到桌子前,顺手端起桌子上的酒樽,正想将樽里的竹叶青往嘴里倒。
可是她却突然呆住。
因为酒樽里的竹叶青不知何时竟赫然不见了!
她清清楚楚记得那杯竹叶青方才明明还在酒樽里,她明明没有喝下去,可是现在怎地会突然不见了?
风四娘的心突然又剧烈地跳了起来。
萧十一郎!
难道竟真的是萧十一郎?
风四娘又惊又疑,目光四下里搜索着,然后她就发现桌子上不知何时竟赫然多了两行字!
字是用刀刻出来的,怪模怪样的,但风四娘却全身都骤然热了起来,一股热血冲到了头顶,她连手指都仿佛已颤抖了起来。
看到这两行字,风四娘再无怀疑。
原来萧十一郎竟真的还没有死!
“出城西行二十里长亭,有竹叶青,有清炖狗肉,有萧十一郎,为你饯行。”
冷月,夜凉如水。
田间水塘里的青蛙正鼓着嗓子大声地吼叫着。
秋虫唧唧,交织着蛙鸣声,就仿佛是这世上最最美妙的音乐。
天地间仿佛早已忘怀了争斗和残杀。
风四娘赶过来的时候,那长亭里檐角下正高高挂着一盏气死风灯。
灯下是一张小小的石桌子,桌子上用一只小火炉炖着一大盆狗肉,火炉两边温着两坛上品竹叶青。
风四娘人还未到,就先有一股浓浓的肉香和醇醇的酒香飘过来,香气氤氲,薰人欲醉。
可是亭子里却连一个人也没有,连个人影也没有。
风四娘骤然怔住,惊诧着,狐疑着,心仿佛在一点一点地下沉。
难道这又是一个骗局?
忽听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声音在身后道:“风四娘呀风四娘,两年不见,你可曾忘怀了我?”
风四娘霍然回头——
只见冷月下,秋风中,不知何时竟赫然站着一个人。
那人身形高大,瘦削,随随便便穿了一袭长袍,随随便便在腰间系着根布带,腰带上随随便便地插着把短刀。
他看起来比两年前消瘦了许多,但眼睛却还是很黑很亮,目光还是很深邃,很咄咄逼人,充满了懒散、俏皮而又机智的笑意,他的眉毛还是很浓,他的胡子也还是很硬,仿佛可以扎破人的脸。
他仿佛比以前更沉静了些,更凝重了些,仿佛少了一点点狂气,却多了一点点沧桑,但他身上那种固有的,说不出的野性吸引力非但未曾有半分减损,反而升华成了一种静谧如处子,狂野如风暴般的神奇魅力。
这种魅力能掀起人生命中最古老、最猛烈的激情火焰,让人疯狂,让人毁灭,让人恨不得拼命,拼命去死,死在他怀里,跟他同归于尽。
风四娘呆呆地望着,连呼吸都似已停顿。
她心里不由自主升起一种说不出的疲倦和悲伤,只恨不得扑到他怀里,狠狠抱住他,痛痛快快大哭一场。
在经历了那么多默默的思念和盼望后,陡然见到他,她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却听萧十一郎懒洋洋叹了口气,道:“你为什么这样子看着我?我鼻子上难道长了一朵喇叭花?”
风四娘在心里失望地叹了口气,淡淡道:“你鼻子上没有喇叭花,只不过有一只臭虫而已。”
萧十一郎居然摸了摸鼻子,皱皱眉道:“我怎么摸不到?”
风四娘又气又笑又恨,故意板起脸,道:“你已摸到了,因为你就是一只不折不扣活脱脱的天下第一特大号超级大臭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