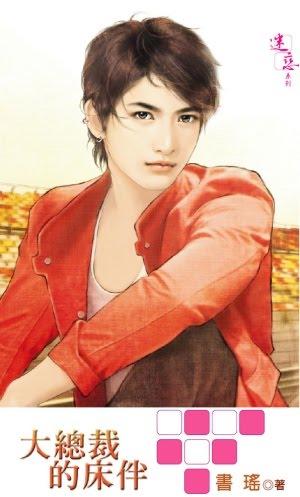ħ�����Ŵ�-��39����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ӿ��Ļ����Ͳ��������ˡ���
��Ц�����ԣ�����֮��ȡ�˺��ӡ�����ȴȡ��һö�Ӻ�һö��Բ���������ģ�����˵������ҹ���������������һ�����Ե�����Ҵ���������ȡ���ӣ����������Ц���������Ҷ���Ե����
����������Ц���������ұ�����һ�ε������ѹ����˶�˵�ٺϹ���϶����ۡ���ڽ��ġ���˲ŵ£�����ǰ;��δ����������
��Ц������ū��ۣ���������֮��һ��Ը������֮�̻塣������һ���Ҷ�ͷ��Ц���������˵����������������Σ������Ƕ���һ�߳��Ų裬һ��Ʒ�Ź���һ�������ӡ�
�嵽��;���ҵ��ӽ���������Χ������������ͣ���֣�̾��������������������һ����֣������ݺύ������ʵ�ڰ��������ʱ�����ȼ��ӣ�������ʧ���������겻ʶ����ζ��Ϊ���´�ǿ˵�����ɳ�����������֣�һʱ�ݺ�۳ң�һʱ�ᢳ������εȵĿ������ǡ��׳������ɽ�ӣ��ֿ����£�һ������ɽС���嵽�о֣�Ӣ�����̣���Ů�鳤�������ϣ������ң������˵����꣬���������վ�����������Σ����һ���ߴ�������������һ�䵽�ף��嵽β���������ˡ������ˡ�����ˣ������˵���ĺ���Ʋ����ᣬ����������ż��ն����ө��֮�⣬����֮Ϧ��������ӣ���������
������һƬ��ƪ���ۣ�ֱ˵����Ŀ�ɿڴ�����ִ��Ц������ū澶����²��ܶ��죬�����鲻���������������֮����Կɼ����壬���ֿɺ����꣬������Ե����ҹ���ң�������һϯ�Ӷ�֮�ԣ�ʤ��ʮ��ʥ��֮�顣��
�嵽���Ȼ�������ˡ���Ц�����������������������������ߣ�����Ҳ����Ͷ֮���ң���֮�������������ȡ��һö���ӣ�����ָ�⣬Ц�������ٺ��ߣ�����Ҳ���й���֮�ġ���ʩ֯�塢�Ѿ�֮��������֮�ᡣһҹ����ǧ�ţ�����һЦ��¥���ӹ������ټѻ������ɴ˴����������ࡢ����ʦʦ�����ԲԲ��Ī����ˡ���
��Ц������ū��ǵ�֮�⣬������������ԣ������ѳ˺�ȥ��ǧ��һ�ޣ�����ͬ�����鲻����������֮������ū澸ж�����������ˣ��������������������Թ�ˡ���
�����ڰ��֣�����Ц����������ͬ����ǧ�깲�����й��������֪���������䣬��������Ҳ����˵�꣬���Ƕ��ˣ����Ӷ�Ц����ʰ���̣��������ӡ�
���ֹ���ҹ�����죬�����罥�������������£����о��⡣�������Ҹ���ʲô�ˣ�Я����֮�֣���˵��Ц��˫˫�ص����Է���
���ϣ�����ѷź���������ԡ�ĺϻ������ú�Ҷ���ţ�ɢ���ŵ��������㡣�ÿ���Ҷ�������������̣�ȽȽ������������Ƣ����ԡ����ſź��ģ�ɢ��ˮ�ף������岼��ˮ��֮�ϣ�Ʈ�Ű��������������Ŀ���������㣬ӯӯ�������������ӣ�����֥��֮�ҡ�
�ź��������������������Ϊ�������½Ӵ����ø���������Σ���������������磬�治�������еķˮ�������
���ھ�ǰ��˫�����룬�һ�����ȥ���������Ʋ��ң�һ�����������DZ��������������ǰ�������������֣��������������ڴ��ϣ��������Ҵ�ͷ���Ŵ�����һ����̾�������������գ��������ʣ���ؾ�����������һ���˸�ռȫ�ˡ���������ˣ�������������ܣ���������������
�Һ��������뿪˫�ۣ���˫����һ��������������⡣
�����ˣ�����������˹�ģ�һ��ץס�ң�����һ��������ѹ�������£������Щ�Q��������������֣���ʼ���������Ĵ��ҿ��桡^��*~����&*��*������@�����Ĵ�������Ū���Һ�����ʹ���ұ����۾���������һ�е���ĥ�����裬������һ����ſ���ҵ����ϣ����Ŵ�������������һ���ĺ��У�����ķ�й�š������ף������ķ��³����֣�������ս���ǵ����Ҿ���һ����������������������
���μ���֮�ø������������һ������Ƥ��һ��������ȥ��
������꣬�һ��ñ�ס��������ĸ������������壬�������ܵ�����һ����ĸ�����ø������ĵ�����������һ���İ�ͷ�����ҵ���ǰ�����ã��㷢������һ����������
������ƣ��µ�һ�ˣ���������Ϸ���ƺ�Ӧ�ý����ˡ����⣬�����𨣬��ˮ���ᣬ�������룬һ�ж��������ҵġ�
���������ÿ���˶�֪����Щ��ϲ��ʲô������Ҫ���Ǵ��ϵ�ħ�������µ���ʹ��
���ġ��ּ�35����һ·����
�������������������Ҳ�쵽�ˡ�
����ʱ����ֻ��è��������Ķ���˵����Сɵ�ϣ����ʲô���׳�ȥ�����ø����������������Ц�������������İɣ��õĶ����������ء������̰������ļһ��������������ˡ�
������������һ������ҹ�����ϣ�����һ�����ӣ�ֻ�м�˿�ҵ���������һ���Ĵ�Ʈɢ������ȴ�ǻ����������ƺ���̣���û����Ϊ���²������������˴�ҵ����¡�
��ɫһ�ƻ裬��Է���Ѱ����˹�Ʒ���㡣���������һһ�������������ã������������Χ��һ�𣬳Բ�̸�죬
����ֻ��ǰ�����������Ǹ�����ѧ���ķ��ˡ��������ô�ã��һ���Եһ�����˵����ݣ���֪����һ��ʲô���Ŀ��˶���
СС��Է����dz�ҹ����Щ�������ߵ�������ڸ������ţ��������š���Щ��֪�������������ܳ������ĵ�������
�Ǹ���֪��ߵغ��ɵ��㣬������֦����һ�����ӣ���һ�����ӣ���һֻֻ���Ū����ë���𣬼�����������ֻ��˵Ц��û���˹�������������������ȥ��
һ���������ǰ����������˵������ү���ŷ�����Щ���ԣ��������ܣ�����Ͽ��ȥ����
����Ц����������С�Ŷ������Ǹ��ֱ�������ӣ�����������ӣ�������ʡ�ġ���˵�꣬���Ҵҵ����ˡ�
ɵ���ĵ����ˣ�������֦��Ҳ������ȥ�ˡ�
�ۿ�������ȥ��ÿһ�������ﶼ֪�����ܰ�����������ȥ�ģ�����£���û�м�������˿���������ŷ��ˣ�һ������һ������֮�������ϻ���Ȼ�������������ϻ����ϵ��ˣ��Dz�����Ӣ�ۡ�����ܡ�
��Է�ֻʣ�������ã���Ѿͷ���ھ���δ���������������ԡ�
ƽ��������������ʱ�࣬��۵����Ӹ��٣�ͬ��һ�������£�ȴ�������������������ˣ����������ģ����ң����ĵ��䣬ĵ�����ȣ��ҵIJ�����������ʹ����˱����ᣬ���Լ��Ŀռ�����ɵĿޣ����ɵ�Ц���ֵô��ͼ��������
�������һ������ۿ�����˵�����ĴDZ����ˣ�ĵ���������ģ������ң�ЦЦ�������������ã����Ҳȥ�ˡ����������ɢȥ�ˡ�
�ۿ�����һ����ɢȥ������һ�磬���滨֦�����������죬��֪���룬�����Ĵ���ʱ�⡣
ĩ�ˣ����������˵������С�㣬��������������Ҳ��ȥ�ɡ���
�ص����ӣ��������������ϴ�������ϴ�˯�ˡ�
����������ô������Ҵ�ææ���������εĹ��ˡ�
ҹ�������һ���Σ����μ����ҵ����裬�ҵĽ�㣬���Ƕ��������ҵ�������ҵ�����������������ʻ������Ϊ���˿�����ı��˳��ԣ�����Խ��Խ��ǿ��Ϊ��һ���˵��ž۶�����ϣ����
������ǣ�������������ڶ��죬�Ҷ�����˵��Ҫ���ϼ�ȥ����������ͬ���ˣ�˵�������ŷ���Ҳ�����ţ�ֻҪ������ˣ�ȥ�Ķ����С������ÿ�����ﶼ�����ɵġ�ƽ�ȵġ���
�ǰ������������ʲô�أ���������̫�������϶���������������⣬����ˮɫ����ǰ�������̣�����ƺ���̣���������أ��������ɾ���Ҳ��������ˡ�
���ǣ�Ҳ����������ʱ�̣�һ����ƶ����֣��ǿ����������ģ����������ؾ�����Щ�����İ��������һЩ�����Ѿõ�ʹ�¡�
�ҵ��װְ֡��ְ̰֡�����ˡ����£���Щ�������ˣ��������ϵ�һ���̣�һ�����������������ʹ��
�ҵĽ�㡢���衢��������Щ��ȥ���ˣ����������һ��ʯ��һ��������Ͷµûš�
ÿÿ�뵽��������������ϵIJ������ӣ��������ᣬ��ȴ�Ѿ���ʼ��Ѫ�ˡ�������ӣ������ҵ������������Ȼ��������ôһ�ݲ�Ⱦ�糾����У�Ϊ�Ǹ���ȥ������һ���غ�
������ݣ�̤�Ͼ�;����Ѱ��һ����ʵ����Ļư�����ȥ���Ǹ����Ұٰ����ġ�ǧ������ȴ�����ǣ�ҵ�С�ǡ�
һ·�ϣ��ﻹ��������������������ľ������˵ģ�����ΪūΪ澵����ģ���������е��˶�������С�ձ������������ơ����������ˣ����ǿ��ѵ����ϴ���Ц���·���һ���µ�ϣ����һ��������̫���ͳ����ˣ��ʻ���ʢ���ˡ�
���ڵ��ˣ�������ҵļҡ������˳�����������ڵ��ϣ���ͷ�����ĺ���ȥ�ˡ�
��ǰ��С�ݣ������˵����Ӱ�ӣ��类����ݲ��ˣ����������ߣ��������������Ŀȫ�ǡ�������Щ�����ҵ����û��̫��ظ�̾��̫����ź����ﲻ�ǣ�����ǣ�һ�ж������ˣ��һ����������뿴��С�ݣ�����һ�µ���ľ��ζ��ѣ��������Ʋ��ơ��ò��ã����˶��ٷ硢���˶����꣬���Ҷ��ԣ������Ѳ�����Ҫ��
������ǰ��һ�����������ش���ȴ�տա�����һ���¶������ߣ�û�������ң���û�������ҡ�
�����˳���ȥ���Ǹ��������Ĵ�լԺ��������һ������֮�أ��ǽ����з�֮ʹ���Һ�������г�֮�ޣ��Ƕ�ʱ�⣬������һ���˵�ج�Ρ�
�Ǹ���լԺ��������ȥ¥�գ�������Ϣ����Ӱ�Ӷ�����һ�������ڴ���ǰ������ʨ��ͷ���ҳ�̾һ�����������м��ֽ�ޣ��뵱�꣬�������֣����լ�ӣ����ջ�����˭֪��ͷ����������ø��������ơ�
�����˳�����ȥ�˳������Ϸ��ӡ����ӻ���ԭ�������ӣ���Ϊ����ס��ȥ�ˡ�һ��Ů�ˣ����ź��ӣ�����������Ų�Ь������������ǰ��̧��ͷ����������һ�ۣ�������ͷȥ�����������Ļ����
�����������ϣ���õ�������߽�����Ϣ�������Ů�˵�����������������ס������ˣ���
��û��̧ͷ�������������ˡ���
��˵�������м���һ������Ů�˻�������������Ѱ�����𣿡�
��˵��������ǰ����һ�����������������ã�ûѰ�ţ���֪���Ķ�ȥ�ˡ���
��֪������һ�����ҵĽ�㣬�ҿ����Ľ�㣬����Ļ����ţ�
��ʱ����Ů�˱��ϵĺ��ӿ�����������û����ˮ���߽�����˳�һ��С�߹���������һ����¯�ϣ���ֽ����ľм������ϡ�������ҿ�Ц���������õ���Щ����ֽ�������°ְֵ��顣������ô���꣬�����Ѿ����չ��ˡ���������˵����������֪ʶ��������ѧ�ʣ�����������ģ���ƨ�ɵġ�
�Ҳ�Թ���ǣ�Ϊ��������Dz��ò����������Ҷ��˼����飬��ͷ����ȴ��ø������Ǹ������Ľ�֡�
�����Ǹ��ư�����������������������ȥ�˱���˵����ݡ�
�����Ƕ������ְ���һ�������Ǹ�������һ���ܣ�һ�߿��ź�����������Զ�ò���ľ����������ڶ�ij����У�ı������������⣬����ʱ��ʱ���ֳ������������Ժ���
���ݵ��ˡ�
��С���С�ӡ���С�š��ǽ����������·�һ���ǰ���������������ϰ��գ�����������һ����ʮ����һ�յ��ظ�����ͬ��������
�ҽй�������Ҫ�������ӿڵ��ҡ���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