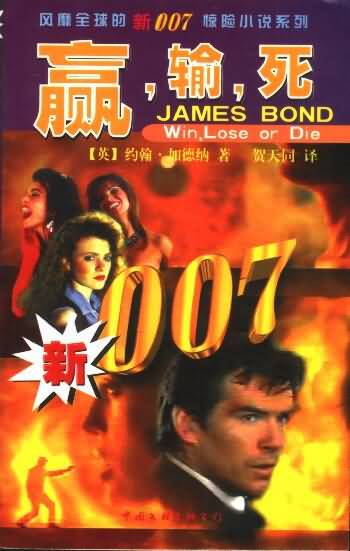赢,输,死-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使人感到痛快淋漓。
这是一座被岁月遗忘了的城市,当邦德将他租来的菲亚特车在一辆满载着瓶装水的大卡车后面刹住时,他沉思着。那不勒斯已不再是旅游胜地。它成了一个中转站。人们来到机场,也许逗留一两天,“游游”火山灰中的庞贝城,然后要么就去索伦托,要么就乘渡船到卡普里或伊斯基亚这两个作为那不勒斯海湾门户的岛屿。
人们时常说这两个岛屿已经不时兴旅游了,然而旅游者和社会名流还是乐意到那儿去。留在那儿的只有那不勒斯人,或是守卫那不勒斯湾的北约组织的各海军舰只上的水兵。对水兵来说,艳俗的红灯区以及沿山脚从圣埃尔玛城堡到市政大楼之间那一片区域使那不勒斯成了一座极不像样的城市。那片区域挤满了酒吧、专门敲竹杠的场所以及那些华而不实的取乐之处。犹如往昔马尔他时代的乔治五世街一样被称为下九流的地方。下九流的地方存在各种可能的堕落和邪恶。邦德心想,这里和被维苏威火山的熔岩毁灭前的庞贝城并无二致。 堵塞的车流朝前移动了6英尺,又停住了,驾驶员和警察的吼叫声透过紧闭的布满水汽的车窗传进车来。
夏天,那不勒斯的土红色的宅子和屋顶吸满了阳光,使街道布满尘土;冬天,这些屋子的墙壁又像是吸满了雨水,更给人一种凋零破败的感觉,仿佛它们随时会土崩瓦解,滑入大海似的。维苏威高入云端的火山口在对这城市怒目而视。
在伊斯基亚和卡普里的渡船码头上,小汽车和摇摇晃晃的卡车排成了长蛇阵,将有限的地方阻塞得水泄不通。邦德注视着一辆大客车企图朝前超车,看见一个警官将身子探进车里,给了那个穿制服的司机一巴掌。在伦敦,这样的警察会遇到大麻烦。可这儿,那司机可能知道如果他发牢骚,从此就不能在那不勒斯干活了。
经过从机场进城的缓慢旅程的挫折之后,等得不耐烦的汽车和货车终于一个接一个登上了渡船,可是吼叫声仍不绝于耳,司机挥舞着手臂,以上帝和圣母的名义彼此诅咒责骂。
邦德下车,来到汽车渡船的甲板上,穿过拥挤的人群,在渡船上寻找一个稍稍安静一点的去处。他用肩把人群推挤开,来到一个小酒吧跟前,很不情愿地买了一杯用塑料大口杯装着的所谓咖啡。这东西的味道就像是加了色素的糖水,但至少可以润润那发干的喉咙。只要到了卡普里西阿尼别墅,他就能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了。
当渡船开始朝海湾驶去时,邦德回首凝视着那黑油油的污水,心里琢磨那不勒斯在它辉煌的日子里是个什么样子。它的美丽曾一度给人以灵感。赛伦因爱上了尤利西斯,投海殉情而死。她的尸体被海浪冲到了黄金海岸,这里便成了那不勒斯海湾。“见那不勒斯而死”,邦德暗自笑了。这古老的意大利成语有着双重的涵义:见到那不勒斯后为她的美丽而死;另一层涵义是这个海港曾一度是台风和霍乱盛行之地。而现在呢,哎,数十年来这里充斥着贫穷和邪恶,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更是越来越糟。他断定既然艾滋病像新的黑死病一样在全球蔓延,这古老的成语现在可以有三重涵义了。不过,所有的古老港市都是如此。
当海岸线在渡船的尾迹中渐渐远去时,也许正是对岁月和衰败、对过去的辉煌和当今世界的紧张的思索,使邦德陷入了关注和忧虑的心境。又一次到这里从事秘密活动,他深知风险所在,因为他已多次到这里用生命作冒险了。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遇到极其不利的形势。上一次他到这里来是进行疗养的。而这一次——见到那不勒斯而……怎样呢?是死还是活?是赢还是输?
就这样,在略微有些忧郁的心情中过了一个小时,越过大海他看到了高耸的古代阿拉贡王国的城堡。不到10分钟,船便靠上了伊斯基亚港的码头,喊叫和推挤又开始了。汽车和卡车驶上码头周围拥挤不堪的街道,喇叭声和叫骂声震耳欲聋。垫上了厚木板以帮助较重的卡车,但码头周围和斜坡因下雨而路滑,使得这样做更加危险,而蜂拥的步行者似乎因走得比车辆快而十分高兴。
他在上车前仔细检查了他的车,因为这些BAST的家伙是不会把无辜的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的。然后,过了几乎是无穷的时间,他才把菲亚特开下了渡船,绕过几个临时胡乱搭建起来的摊点,这些摊点是向容易上当的度假者兜售劣质的旅游纪念品的,他们离开家和灶台在节日时分到这里来是为了一睹美丽的伊斯基亚废墟,饱受历史沧桑、曾目睹过惨烈的死亡也享受过欢乐的和平的岛屿。
他朝西驶去,随时准备应付不测。他已经谨慎地向任何可能向BAST提供情报的人放出风声,在尤维尔顿皇家海军空军基地军官室里里外外向许多人说明,他要到那不勒斯海湾去独自度过一个宁静的圣诞节。
他们知道BAST是从尤维尔顿窃取情报的;正如他们知道那满脸油腻的巴拉基已经向他伸出了魔掌,并让“野猫”莎菲·勃黛负责下手。他们手头没有莎菲·勃黛的照像材料。充其量只有一些匆匆瞥见这四位一体的BAST头目的人所抓拍到的模糊的照片。邦德确切知道的只有一点,那就是“野猫”是个女人,有人报告说她是高个儿,有人报告说她是矮个儿,有人说她胖,有人说她瘦,有人说她美丽,有人说她讨厌。唯一一致的说法是她有一头深黑色的头发。
他用租来的车旅行,这是个很不安全的开头,而且,在他抵达卡普里西阿尼别墅前, 他是赤手空拳的。直到M下达了最后的指令之后,邦德才意识到别墅本身就是一个极不安全的因素。当他在狭窄危险的道路上驱车行驶时,他不断地看后视镜;注意从渡船上下来的车辆——一辆沃尔沃,一辆VW。但是没有一辆车看上去像是在盯他的梢,没有谁对他发生兴趣。
在分别位于伊斯基亚岛西北和西面的拉科和弗雷欧之间的道路上,他改变了方向,驶上通往别墅的非常狭窄的碎石路。岛上的一切似乎没有改变,从毁灭性的,几乎是自杀性的驾车到出乎意料地在道路的拐弯处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美丽景色,一切都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还有其他一些景观:墙灰脱落的楼房,一间敞着大门的杂乱的车间,一家寒酸的加油站。在夏天,这地方也许还会有一些生气,可是在冬天,只使人感到空旷和压抑。现在,他准备将车驶进灰色石头高墙的大门,暗自希望别墅里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大门是开着的,他将菲亚特朝右拐进围墙,熄掉发动机,下了车。在他面前是一个很大的美丽的百合花池,池的右边是另一扇门,通向垂满蔓藤和绿叶的台阶。他能看到上面别墅的白色圆顶,当他在台阶上拾级而上时,一个声音叫道——
“是邦德先生吗?”
他应声称是,当他走到台阶顶上时,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他面前。她上穿一件无袖汗衫,下着牛仔裤,衣服不合身,像是偷来的,使她看上去仿佛那两条美腿是嫁接到她那小巧玲珑的躯体上的。对她的脸只能用厚颜来描叙。短而扁的鼻子和一张笑吟吟的大嘴巴上面闪动着一对深色的眼睛,上面是一头黑色的细卷发。
她是从别墅的大玻璃推拉门里出来的,现在就站在水池边,微笑着。她右边的棕榈树和热带植物丛中有一尊嘴里含着大拇指的森林女神的雕像,其神态和这女子惟妙惟肖。
“邦德先生,”她又说道,她的声音欢快开朗。“欢迎你到卡普里西阿尼别墅来。我是比阿特丽斯。”她的发音意大利味儿极浓,“贝…阿特雷…切”。“我在这儿迎候你。同时也要照顾你。我是女仆。”
邦德心想他不愿为她打赌,大步走上宽大的阳台,阳台上铺着一层绿色的地毯,在炎热的季节,当你从这儿走向游泳池时就不会烫着脚底,可是现在,那游泳池是空的而且是盖着的。 别墅在冬季是从不开放的,所以他不知道M这次是如何为他租下这里的。 答案也许就在他可能和这里的业主共同做出某种秘密的安排。M在世界各地都有地位高的朋友,所以,邦德猜测,由于当前形势需要,他会对他们施加压力。
仿佛是知道他的想法,比阿特丽斯伸出一只手,出乎意料地紧紧抓住他的一只手。“太太不在,她到米兰过圣诞节去了。我留在这儿守卫这里的房子和整个别墅。”
不知你是不是还为BAST守卫它们呢?邦德暗想。
“来,我带你看看。”比阿特丽斯轻轻拉了一下他的手,像个孩子似的领他进入别墅,然后站住了。“啊,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这地方,你以前到这儿来过,是吗?”
他微笑着点点头,跟随她走进建有拱顶的白色大厅,厅内有配套的铺着乳白色罩布的沙发和椅子。厅内有三张玻璃面的桌子,四盏形同盛开的百合花的白色玻璃灯和四幅油画——其中一幅是霍克尼的风格,一个欠身站在水池边花丛中的不知名的男子;其余三幅是邦德熟悉的各种花园景致。
尽管比阿特丽斯知道他了解这个地方,她还是用令人上气不接下气的速度带他四处转转,让他看三间大卧室——“你会很难拿定主意睡哪一间,是吧?或许你可以每天晚上换一间卧室,嗯?真可惜。夜夜不同才是一种享受哪。”说完是一阵大笑。
别墅处在一层上面:一间大厅,有门通向三间卧室,通往厨房的狭窄的过道整齐地放置着两台冰箱、瓷器、壶、碟子和刀叉。大厅的后面是拱形的,过去便是餐厅:整个地方都摆设着美丽的家具,老式和新式的巧妙结合,每一间房间有自己的风格。走到餐厅的后面,经过几扇玻璃门,便来到第二个阳台上了,在第二个阳台的左边,有阶梯通到由平屋顶布置成的四周开敞的房间,顶棚是由木头和灯芯草搭起来的,顶上还有一个风向标,顶棚由粗重的木梁支撑,里面放置着一张长餐桌,是夏天用餐的绝好地方。放眼远望是弗雷欧的灰白色的小镇,重新粉刷过的,用简洁的建筑线条筑成的雪白的救难女神庙,高踞在向海中延伸的古老的灰色石岩上。
雨停了,冬日的太阳照在远处显得小小的教堂上,将光芒反射到水面上。邦德回首看着那群山起伏的小镇,然后又回过头来凝视着那海岬和教堂。
“真美,嗯?”比阿特丽斯站在他身旁。“那是救助渔民的;对所有出海的人。救难女神保护他们。”
“有一首赞美诗,”邦德突然说道。“那是一句祷文。哦,当我们向你哭泣时你可曾听见,为的是那些在海上遇难的人。”
“真好。”
她站得离他很近,即使在这寒气逼人的冬天他也能闻到她身上阳光的气味。仿佛是炎热的夏日滞留在她身上的甜蜜气味,期间还混杂着一种他无法辨别的香味。
他转身走开,在台阶上停了下来,凝视着隐藏在别墅后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观。
有一阵,本地的人们认为夫人——正如比阿特丽斯所说,她现在在米兰——疯了。一个大艺术家的寡妇,她买下了这个地方,将这里炸平,把它建成一个像圆形剧场的样子。在岩石旁,她又建了一座看上去就像是个灰色拱壁的要塞似的大别墅。她在夏季出租的四个小别墅是由原来的牧羊人茅舍和谷仓之类的老房子改建的。但她最大的成就是花园,在卡普里西阿尼别墅里所挂的油画就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