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容依旧-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非浅一路送他到楼下。他上了车,她就一直定定的隔了玻璃看着他。
他放下车窗不怀好意的说:“我发现你有点依依不舍。”
她笑:“我是担心你半途折返,这样才放心。”
他也笑,简单说:“那我走了。”
非浅就冲他挥手。
他才把车窗升上,就开了门跳下车,紧紧抱着她说:“非浅,我有点想你了。”
她仰头看着他,眸如点漆,闪闪涌着不舍,一时不晓得该说什么好,又低下头在他怀里,也伸了手揽着他的腰。
他说:“要不你跟我走吧。”
车已经上了高速,非浅还不能确信自己竟然跟他私奔了,而心情却那样愉快,愉快得生了轻松。可是哪里能轻松得了,怎么跟妈妈解释呢,所以愁眉不展。
她问:“你还记得你妈妈最生气的一次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吗。”
仲微专心开车,一脸的镇定,“就是那次抢银行吧。”
非浅噗哧笑出来,他说:“可是有了笑模样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被绑架了。”
她说:“你说我怎么跟我妈妈说啊。”
他说:“用电话说。”
她说:“我手机没带,你的借我。”
他腾出手来给她拿手机,稍有愤愤的说:“你那手机本来就是个摆设,有和没有一样。”
非浅接过来,握在手里,低着头想心事。
他问:“怎么不打了。”
她平静的说:“仲微,你还记得中午那个时候跟我一起走出小区大门的那个人吧。他是我妈妈的朋友伍阿姨的二儿子,我们从小就是邻居,他比我大六岁。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放学回家,看见他在墙角蹲着,我就叫他‘二哥’,可是他不理我,我又叫了一声,他还是不理,我以为他没有听见,于是又很大声的叫了一声‘杨均哥哥’,接着我就傻了眼,一群大孩子冲到他面前开始打他,对方人太多,他跑不脱,就在我的面前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还听说断了肋骨。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我每晚都做恶梦,不主动叫人,爸爸妈妈都不叫。看过很多的医生,慢慢长大了才好的。可是我一直很后悔当时不懂事,如果我不叫他的话,他也许就躲过去了。初晓说我是钻牛角尖。”
仲微一直静静的听完,才讲:“非浅,你爸妈很担心你,怕你遇到事情还是会钻牛角尖。”
她说:“我知道。你跟我爸下棋的时候他给你讲过一遍吧。”
他点头,伸右手握住她,“非浅,对不起。其实之前听初晓也讲过,那时候不是很信。”
非浅拍他:“所以就大老远的跑过来干巴巴的在楼下等啊,就那么想我给你打电话。”
仲微坏坏的笑起来:“伯父说,你越是在乎的人越不肯主动打电话。”
非浅哎呀一声,举起手机说:“我妈该急疯了。”
仲微说:“你妈才没着急呢,我跟她说要带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她早同意了。”
非浅吃惊的问:“什么时候。”
他云淡风轻的说:“就是你洗碗的时候啊。”
第二十章
非浅吃惊的问:“什么时候。”
他云淡风轻的说:“就是你洗碗的时候啊。”
她盯着他,一下一下眨着眼睛,像是难以置信,过了好久才爆发出来,“周仲微,你耍我。”
他转头看了她一眼,继续直视前方认真看路,不为所动的口气:“那不是应该的么。”
非浅顿时觉得刚才的那些甜蜜顷刻化为灰烬,他那张英俊的侧脸也生出了邪恶,她犯傻还以为是私奔了,原来不过是被拐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心里的气来得莫名,却大得自己镇压不住,固执的偏头去看窗外,抿着嘴一语不发。
车里统共就两个人,又谁都不再说话,空气就一点点的冷下去,气氛沉着得诡异了。沉默了好久,他渐渐忍不住,问:“真生气啦。”她不理。他好声好气的哄:“别气啦,送你新年礼物好不好。”她还是不理,他没了办法,和气的商量:“非浅,你也说句话。”
她侧过身绷着脸像个受了欺负的孩子,指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昏暗中好像看到她眼里盈盈水光,他的心跟着一紧,减速把车停在紧急停车道上,车里更是静默了。他低低的唤她,“非浅。”似是有些为难的缓声开口,“我只是舍不得你。”
夜色早就黑得浓重,只有路上车灯通明,一辆辆车从旁边飞驰而过,她的眼睛便一闪一闪。看不清楚他脸上的表情,只是知道他那么认真,认真得教她没了脾气。“以后不许耍我。”
她的声音很软,听着生了淡香,心也是飘来荡去的软,他笑着点头,像是总结发言:“合理要求。”非浅便彻底没了脾气。
车又上了路,他不知从哪里变出了个玲珑的小盒子递给她。她接过来,问:“是什么。”
他微微笑着,“打开看看啊。”
是一对kaloo的香水小熊,蓝色的那只带着睡帽懒懒的闭着眼睛,粉色的那只睁着一双善良的眼睛可爱异常,这么可爱的两只东西,非浅简直爱不释手,捧在怀里像是得了稀世珍宝。
他问:“喜欢么。”
她不假思索,“喜欢啊。”
他问:“喜欢送礼物的人么。”
她想了想说:“还是更喜欢礼物。”说完开心的冲着他笑,一双眼如明珠出洛神,一直照亮到他的心底。他喜欢看她笑,或者说渐生迷恋,那样柔暖的笑容,焕可和风日,明可烛天南。他不自禁恍了神。
钥匙,手机,钱包,惯常的三大件非浅一样都没有带着,到B市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又不好去吵初晓,只得投奔他的住处。
来过三次竟都是三更半夜,她始终觉得这件房子又大又冷清,开玩笑说:“你一个人住这里不怕么。”
仲微将灯打开,橙色灯光像是烛火照耀处即刻温和了起来。他翻了半天才找出拖鞋递给她,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偏着眉眼说:“怕啊,要不你搬过来给我壮胆。”
非浅才忽然想起来,吸气“啊”了一声,“我穿成这样明天怎么陪你去参加婚礼啊。”
仲微好笑起来,她身上穿的是中学时的运动服,头发束成马尾,如果再来个双肩包说她是高中生恐怕都会有人信。端起下巴,摆了一副为难的样子说:“那就,别去了。”
她将信将疑的问:“真的不去啦?”
他敲她脑袋,“只是你不去,我还是要去。”
她一脸鄙夷,“那还把我拐过来做什么。”
他表情严肃的说:“拐都拐了。”
非浅只想笑,他恐怕打死也不会再说“舍不得你”这样的台词了,虽然她很想再听。“那我做什么啊。”
他一脸得逞的兴奋,像是在说就等你这句话了,拉起她直奔衣帽间。非浅暗讶,竟然比她的卧室还要大,满目琳琅,摆满了他的衣服鞋子。惊叹间模仿他的遣词造句:“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比女人的衣服还多。”
他揽着她浅笑:“所以我整理困难啊,你明天就帮我整理整理吧。”
非浅吃惊的瞪着他:“这还用整理?完全是纤尘不染,有条不紊,难道还需要整理么。”
他正经的说:“家政整理的方式我不喜欢。”
她仍是一脸无知,满脸堆着问号:“还有比按照颜色分类更合理的方式么。”
他说:“你知道我有时候很懒,你就帮我按照搭配摆放吧。”不容她答话就半推半抱的推她到客房,“今晚你就睡这。”
然后又手把手的将盥洗室,厨房,洗衣机烘干机一一交代了一遍,上楼前不忘嘱咐说:“明天记得帮我整理衣服。”
她笑着点头:“好啦好啦,晚安啦。”
他也笑,自己几时这样罗嗦过,清了清喉咙道:“晚安。”上了几层楼梯,又俯下身来说,“有事叫我。”
她郑重的点头。
非浅其实一直都认床,加上床也软她睡得极不习惯,一会觉得被子厚了,一会又觉得枕头高了,折腾了半天,起初的那点困意全然不剩。屋里的暖气蒸得她口干舌燥,反正也是睡不着了,只好起身去倒水。厨房和屋子里的任意一处一样,也是纤尘不染,大概除了烧水也没有过别的用途了。她也很纳闷,像仲微这种看起来四体不勤的人怎么会执着的喝烧开的水,就算是再挑剔的舌头加上柠檬片也是觉不出原味的,她猜想也许是饮水机触过他霉头。
她端着水杯一点一点去打量客厅,沙发很大或者该说很宽广,坐在上面便不想动了,她对沙发有偏执的喜爱,所以是真心的喜欢这只沙发,喜欢到把自己藏在里面都甘愿的地步。茶几上整齐的摆着报纸杂志,她随手拿起来翻看,红色喜帖就在隐藏之下见了光亮。她从没见过那么精致的喜帖,红得自然而喜庆,边角细细的烫着金边,上面的剪纸双喜因灵巧而熠熠生辉。只是端看着喜帖就觉得婚礼必定也是不凡的。她一向好奇心不胜,却也是想要看看是何许人物。如果她能够知道里面端正的写着主角“余清修”的话,她一定不会把它打开,在碰到它之前就躺在床上安安静静的睡觉了。那只是如果,非浅像是忽然结成了冰,眨不了眼睛,也不知道该怎样挪动手脚,只是一颗心抖得她惶惶不安。薄薄的请帖生了千金之重,拿在手里如何也承受不起,铅直落地,原来真的那样沉,不似平常纸张的轻飘。她缓缓复苏过来嘲笑自己,落荒而逃也不过如此罢。
仲微也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忽然想起请帖好像没有放好,出了卧室看到楼下的灯亮着,便疾步过来,还是晚了一步。走到她身边,步子并没有刻意放轻,却没有将发呆的她惊醒,想要伸手探她的肩,非浅才惊慌抬眸不可思议的望着他。
他淡淡的说:“我看见客厅灯亮着……”吞下去要说的话,转了轻松的口气,“想找你说话的,原来你真的没睡着。”
非浅微微点头。
他弯腰把喜帖捡起来放到桌上,语气谨温:“明天我做伴郎,伴娘不是你,怕你吃醋所以不想让你去。”
她的眼泪忍得太坚强,忽然间破了极限一般,扑簌簌的往下掉。那句台词的原址不该是明天他做新郎么。仲微缓缓的把她揽在怀里,团着她的耳朵轻轻安抚,安安静静的听她的哭泣。他身上那样暖,而她身上那样凉。他一下一下的摩娑她的脊背,一下一下,耐心得像是没了边界。
非浅并没有哭很久,觉得眼泪干涸了,抬起头说:“我只是想妈妈了。现在我去睡觉。”
他不置可否,不拆穿也不点头,抱起她进了客房,轻轻放到床上,仔细给她盖好被子掖好被角。她问:“这是做什么。”
他一副我也不情愿的表情说:“你不是想妈妈了吗。”
很好笑,可是她笑不出来。
他心疼,俯下身抱住她,非浅一动不动的任他越抱越紧,她喜欢他身上的暖,喜欢他身上淡淡清爽的味道。可是不是现在,现在的她思绪混乱。他的唇也是暖的,有些发烫,烫得她被吻过的地方一阵灼热,可是她仍是冷。他吻着她的眉眼唇鼻,还有曾令他心动不已的脖颈曲线,她的头发还没有完全晾干,潮湿着散发诱惑。她知道他的暖里有情欲在蔓延,可是没有念头去回应,也没有力气去叫停。
他动情的吻着她的长发,一寸一寸下滑最终定在发稍,他的双手已经抚在她胸前柔软也是忽然没了动作。终于还是叹息,隔了半晌,起身帮她把被子理好,走到门口轻声问:“需要关灯吗。”却不看她。
满室漆黑,她茫然中记得自己好像是说了“关吧”,可是她后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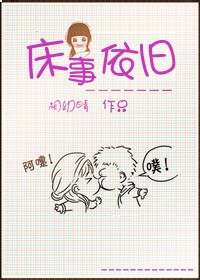

![[网王]星光依旧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46/46933.jpg)